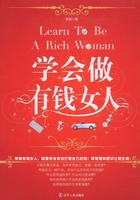天地良心,是谁先忍不住主动吻我的?
大概走了半个时辰,我们终于又重新迎来了月光的光辉,可是我却依然欣喜不起来,还再一次感到深深的挫败!
这……这究竟是有完没完了?千辛万苦走出一片森林,我又迎来了另一片森林!
望着这无边无际与夜色融为一体的密林,我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做在地上,再也走不动半步!
慕容北珩也坐了下来,问我,“夏姑娘知道这是哪里吗?”
一听他的话,我心中更凄凉,他是祁人都不知道这是哪里?我一个初来乍到的夏国人就更是摸不到边了。
死定了,这次真是死定了。
他不动神色的看我一眼,一句话石破天惊,“这里是西郊群鹤山。”
“啥?”我惊叫出声,敢情他已经摸清了这里的地理位置?
慕容北珩目光如水,嘴角泛起的浅笑犹如此时柔美的月光,“这里是西郊群鹤山,从这里一直往东走不出三个时辰,我们就能到京都了。”
我愣在那里,心中一悲一喜,已分不清自己究竟应该是高兴还是难过了,总之,情绪很复杂。
喜的是,我们终于逃出了那个阴冷的地狱,悲的是,竟然还要走上三个时辰才能回到京都,三个时辰,那可是六个小时啊!
估计到的那会儿我也已经半死不活了。
可事实证明,现实比我的担忧更悲壮。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仁兄说的三个时辰,完全是指骑着千里良驹奔驰而行用的时间,而我们徒步,又是两个伤残,我看不走个两天三天的,根本不可能!
一想到还有两三日跋涉的路程,我就开始头痛。
由于体力透支得厉害,我和慕容北珩没有再急着赶路,一直倚在树下休息到天亮。
夜里风大,荒郊野外的又透着一丝瑟缩的凉意,我被冷风无情的吹醒了几次,睁开朦胧的睡眼四处望了望,发现慕容北珩如寒松一样坐在我身旁,毫无睡意。
我这个位置恰好能看见他半边侧脸,完美的弧度,高鼻、薄唇、长睫毛,一张清清淡淡的脸,在月下飘渺得不似真人,他静静凝望着那漫无边际的密林,脸上写满了寂寥。
他望着远方,我望着他,仿佛时间也静止了。他在想什么我自然不知道,可是诡异的是我在想什么我居然也不知道,就那么忘情忘我的看着他,一直看着……
不知不觉中,一件外衫落到我的肩上,我诧异抬头,他眸子晶莹,脸上的落寞一扫而光,整个人温暖得如同三月春水,漾人心扉。
是我错觉了吗?眼前这张出尘的脸明明如此清朗,我却真实的感受到他眼底压住的一丝寒光。
此时的情景实在不对头,我连忙干咳了两声,问道,“你睡不着吗?”
慕容北珩双目微垂,不冷不热的回答,“本王夜里一向睡得少。”
“夜里睡得少?”我纳闷,“那你晚上不睡觉一般做些什么?”
“不知道,发呆吧。”
“为什么会睡不着?有看过大夫吗?听说失眠也是一种病,你得赶紧治。”我今夜实在啰嗦。
他明显愣了一下,抬起眼皮看过来,半信半疑,“是一种病?”
我急忙点头,“对呀,失眠到了一种很严重的地步,就会夜不能寐,长年累月下去轻则神经衰弱,重则痴痴呆呆。”
慕容北珩笑了笑,用指尖轻轻拨了拨额前的碎发,“本王是心病。”
“心病?”难不成他也是个心理变态?
慕容北珩点点头,望了一眼远处的密林,又转过头来问我,“你说心病,是不是只能心药医?”
我迷茫的点点头,又听他幽幽道,“日子就快到了,本王也就再无须夜不能寐了。”
“是吗?可是听说有心病的人往往自身的心理感知也会有一些残缺,不知道襄王可把自己的心境调整好了?若是根基不固,恐怕其他也是惘然。”
慕容北珩淡漠的双眸中闪过一丝阴戾,片刻消失不见,“那依夏姑娘之见?”
“先找到你失眠的原因再对症下药,方可事半功倍。”我淡淡道。
“失眠的原因?”慕容北珩沉吟半晌,“本王似乎自记事起就从未好好睡过一觉。”
他的声音缓慢,如清平的琴音一泄而出,隐着有一丝淡淡的忧伤,很容易挑拨人的心扉。我不知道是怎样的忧虑令一个孩子从记事起就睡不好觉,但也不想去知道。
这个男人太危险,你知道越多,就越难全身而退。
“夏姑娘有害怕过失去什么吗?”他突然问我。
“以前有,但现在没有了。”自夏国亡了以后,我最珍视的人和物都在同一天离我而去,细细想来,我现在还真可谓是孑然一身了。
“本王从未有过。”
他说这句话时神情冷漠,语气冷淡,一身白衣在月色下宛若开在湖中寂寞摇曳的白莲,但字里行间,我却听出了另一种情绪……渴望。渴望爱与被爱,渴望在乎与被在乎。
慕容北珩淡漠冰冷的性格,多半与他从小生长的坏境有关。他自小丧母,亲情疏远,虽然少年封王,外祖父又是祁国鼎鼎大名的楚丞相,可自小便缺少了母爱的孩子性格上多少有些残缺。难以自爱,更无法爱人,他扭曲的人生,可能是也是在那时便已经注定。
清晨,林中飘荡的朝雾散去,金色的阳光从枝叶的缝隙里照进来,万丈金光流霞,整个群鹤山上充满了蓬勃朝气,没有了昨夜的阴森冷郁,目光所及之处,无不是金灿灿的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