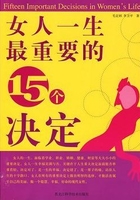他受了很重的内伤,而我又连续两日滴水未进身体虚弱得厉害,从独立独行到两个人互相搀扶,在这片荆棘林里兜兜转转的走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出路。
迷雾中,冷风阵阵盘旋,到处都充斥着阴森森的味道。冷风灌入耳,又渐渐入了心,将我整个心绪都染上了悲凉的味道。
慕容北珩突然侧过脸来看着我,问,“累了吗?”
我摇头,“还好。”累到不累,他应该问我,死了吗?我想我会果断的说,快死了。
我叹了一口气,“不知道我们究竟何时才能找到出路。”
“不急。”他淡淡的开口,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淡定,“天无绝人之路,既然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再说本王也不会允许自己死在这荒郊野外。”
我点了点头,他那么铸锭,我也不好打击他,又好奇的问,“子午沁兰金针是什么暗器?为何那个女人会如此恐惧?”
慕容北珩黑眸微微一闪,压住了一丝异样的情绪,口中温温问道,“天绝兰你可知道?”
我点头,“听说过。”
大哥精通医理,曾无意听他说起过,那是一种十分烈性的奇毒,生长在终年积雪而又险峻的高山上,极难采摘。它无色无味,遇血即融,并且第一次毒发极快,以后每日发作两次,每次发作时都如万只蚂蚁噬骨啃心,寸寸割肉,这种生不如死的痛苦一直持续到第四九天才会血管爆裂而亡,死状惨目忍睹。
我望着他,“莫非,这金针里就藏有天绝兰的剧毒?”
慕容北珩点头,“这沁兰金针里不仅带有天绝兰的毒,还加了一味五星子午草。”
五星子午草?
这味药我好像有些熟悉,似在那里听过,但又一时之间着实想不起来了。
慕容北珩指了指前面那片藤蔓横绕的地方,叉开话题,“我们去那边看看。”
见他不愿再说,我也不再追问,穿过层层枝密横生的树枝,绕过一片被烧得漆黑的枯木,一阵夜风袭来,我不由得打了个冷颤,慕容北珩转过来看安慰我,“别怕。”
我点点头,与他并肩一步一步往前走,穿过枝条密生的灌木丛,借着朦胧的月色看过去,前面的路已被墙堵死了。
我心下一沉,皱起眉头去看慕容北珩,什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福我是看不到了,不过死路倒是有一条。
慕容北珩略微沉吟,走上过去用手在墙壁四处敲打,“这扇石壁后面好像是空的。”
我闻言,赶紧奔上去一边敲一边贴着耳朵听,声音空空缓缓的,好像的确是空的。
我顺着墙壁一点一点的摩挲,不敢遗落任何一个细小的地方,也不知道最后究竟是我还是他触碰到了机关,只听见‘轰轰’几声,那堵墙中间裂开了一条通道。
我和慕容北珩对望了几秒,他率先迈开步子,向里面走去,我紧随其后。
通道狭窄,四面都是石壁,黑沉沉的,空气流动性差,令人说不出的压抑。顺着通道往里走了没一会儿,依稀看见一扇满是铁锈的门横在我们面前,慕容北珩踱步上去轻轻一推,门‘吱呀’一声开了,眼前立刻出现一条长而深的隧道。
隧道里黑漆漆的没有一丝光源,我跟着他向前走了两步,黑暗中只有我们彼此微重的呼吸声,不知道前面究竟有多长,也不知道下一步会不会踏空,便掉进无底深渊。
气氛冷沉沉,逼得人险些透不过气来,我寒意陡升,想起自己被关两日的那个黑屋子,心中越来越凉,生怕黑暗中再杀出一个什么梅花、菊花来,我想我铁定就一命呜呼了。
慕容北珩似感觉到了我的惧意,他慢慢将手伸过来圈我进怀里,一只手紧紧握着我,“本王在这儿,别怕。”
“我不怕。”我死鸭子嘴硬。
“不怕吗?”慕容北珩语气极轻,温暖的呼吸喷在我耳廓,分散了我的畏惧感,我抬起头,他却又刚好底下头,这一来二去间,两片唇就如此不期而遇了。
他的唇很凉,温度堪比炎炎夏日里解暑的冰淇淋,却柔软得如同上好丝锦,带着一丝清新的甜腻,宛若吻上了一朵午夜露水染湿的花芮。
本以为黑暗中看不见的双眸,此刻却尤为明亮,他的眼睛就像一朵澄明而渴爱的花,就是满天雨落下都盛不满。
我沉迷其中,他已加深了这个吻,唇齿相依的感觉,让我的身体在惊愕中变得柔软。
那一刻,我仿佛被鬼上身,对眼前这个男子无法抗拒,并且还如此沉迷……
在一轮又一轮的细细啃噬后,慕容北珩终于意犹未尽的放开我,纤长的手指在我脸颊抚过,仿若抚着什么珍贵的宝贝。
他冰冷的指尖带着微微的湿意,一触到我的肌肤便立刻带起了一层沁凉的冷意,我一个激灵,这才从刚才的心神恍惚中走出来,暗自唾骂拙劣的自己。
也许人在脆弱的时候总是渴望有人亲近,触碰、轻吻甚至一个拥抱都能恰到好处的安抚心中的惧意,可是那一瞬间的沉迷却令我无法解释。
难道真如泾朔所言,我是个色女?只要是个美男我就会被其美色所迷?只是我一直没发现自己这方面的癖好?就好比我变态却没发现自己是个变态?
我心虚的瞄了一眼慕容北珩,他仍旧拉着我的手默默前行,却是死了心的不再与我攀谈。以至于有两次我主动找他说话,他都很不给面子的将我视为空气,好像……好像刚刚吃了多么大的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