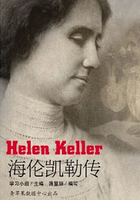他很沉得住气,没有继续逼问,而是换了一种问法,“你刚刚打算跑到哪儿去?”
我继续装傻,“我害怕,吓到了,所以没目的的瞎撞。”
慕容孤赫的脸靠近了三分,“吓到了?”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我脸上,我看到他深邃的黑瞳里分明印着‘不信’两个字。
我鼓起勇气,硬着头皮,装傻到底,“对,我吓到了,我一紧张就喜欢乱窜,我十分没有安全感,从小就这样,记得小时候……”我一一列举了多个事例,反复论证我的观点,最后总结,“你不了解我,所以你不知道我的习惯。”
他没有再问,陷入沉思。口中呢喃道,“本王也许真的不了解你,若了解你……”后面他越说越小声,音弱似蚊,本着天生的八卦心态,我张着耳朵努力想多听两句,却全然听不清楚半分。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蒙混过关,惊疑不定中,腰被猛地一抬,炽热的吻覆了上来。
我吃痛,狠狠一咬,咬破了他的舌头。哪知他迅速反击,一下咬破了我的唇,血交融,甜甜的、咸咸的,充斥着口腔。
这突如其来的狂吻让我手足无措,这魔鬼似的交缠也令我感到害怕,试图推了他几次,根本动摇不了分毫,他似乎深深沉迷在这个吻中,吻得忘情忘我。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才依依不舍的放开唇。一边舔着上面沁出来的血珠,一边温柔的说,“不管那个男人是谁,他都绝无可能将你从本王身边抢走。”
他指腹在我下巴上轻柔摩挲,又温柔的亲了亲我的脸颊,“你会跟本王在一起的吧?”
“我……”我浑身发麻,寒毛倒竖,喉咙似被什么卡住了一般,说不出话。
他不在意的笑了笑,“以后陪着本王,爱上本王,永远都不要离开本王,好不好?”他的声音低哑,像靡靡之乐,可是今天又格外温柔,像低吟浅拨的瑶琴,划过湖心,荡开一圈又一圈的水波。
“好……”我知道现在惹怒他绝然不是明智之举,只得硬着头皮应下,心想逃过一劫算一劫。
他目前表面上看着还算亲切友善,可从相处这段日子以来的了解,想必他已怒到了极点,不然不会连连做出如此反常之举。
“你在撒谎。”他一语道破我的谎言,指腹在我唇上反复柔腻,带来丝丝疼意,“不过也没关系,不能爱本王,那就让本王来爱你,疼你一辈子你说好不好?”
我震惊得说不出话,瞪大眼睛盯着他。
他又笑着摇了摇头,‘恍然大悟’道,“本王差点忘了,你已经没有选择的机会了。”
他的意思我的人生就在他这几段言辞间,已经被主宰了?
一路无话,他也没再阴森森的说些奇奇怪怪的话,我麻木的任他按在怀里,作无害的小猫咪状,心思飘忽忽的飞了老远。
刚才混乱的场面中,那立于桃花树下的白影,我几乎可以铸锭就是燕北,却打心底里不愿相信。若真是燕北,他一介布衣,为何手下会有那么多死士效命?
印象中,他除了骑射了得以外,便是个温润如玉之人,跟打呀杀呀的血腥事件是半点关系都沾不上的。
如今突然冒出那么多死士,若领头之人真是燕北,那他的性质与慕容孤赫又有什么差别?还不是双手占腥,嗜血伤命的狂人。
想到这里,我心凉了半截,越渐反感这个推论。就像你一直信仰的某件事物,心中留恋的某种温暖,转眼间全变成了另外一番模样,以一种你不熟悉,不认知的面孔重新站在你的面前,是多迷茫,多无奈?
我努力催眠自己,这归结与我性格上某部分的逃避心理,我只愿相信燕北是一个普通少年,董太傅的远方侄子,年少时一起长大的玩伴,会永远在蒲公英下对我笑的人……
胡思乱想中,马车已在皇宫的正门前停了下来。
我思绪恍惚的沿着大理石铺成的小径一路往前走,被这里喜庆的气氛感染了心绪。
祁国的皇宫,到处是一片张灯结彩的繁荣之景。
耸立的红墙,墙上飞檐卷翘,矗立的宫殿气势恢弘,殿顶的琉璃玉瓦闪耀争晖,瑞光流彩。
慕容孤赫毫不避嫌的一路拉着我,接受众人跪拜,踏入正殿,人们和谐的交谈声骤然停止,数百双目光齐刷刷的射过来,有好奇、有震惊、有艳羡、有轻藐,有不屑,各种眼神,目不暇接,看得我头皮发麻。
我微微低头,避开各种稀奇古怪的神色,掌心,密出微微细汗。
我最怕这种场合,以前在夏国的时候,各种宫宴也都是能省则省,能不出席坚决不出席。
我不是个爱凑热闹的性子,特别是这女子多男子少的宫里,简直是盛产易妒爱宫斗的心机女,我怕这个,玩儿不起。
前方,一个惊咋咋的声响起,在沉闷的大殿里显得格外刺耳,“三哥!”那人笑嘻嘻的踱过来,凤眼却是一脉的盯着我,惊呼道,“夏姑娘!本王莫不是眼花了?夏姑娘,这一别多日,可让本王好想啊!”
不用看,只听这声音,就是知道是那惟恐天下不乱的寰王,慕容先绪。
我本想冷着脸瞪他,却被他那幅流浪已久的小狗找到主人的欣喜模样给逗乐了,噗嗤一下,就笑出了声,引得在场众人一阵唏嘘。
慕容先绪嘿嘿一笑,挠头很是自豪的说,“本王就是知道你没有忘了我。”他忘了身份忘了场合的竭力与我套近乎,“夏姑娘,本王可跟你说,那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