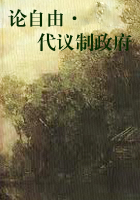他是最应该被信任的人;父亲的慈爱使儿女的财产和利益在他的照料下得到保障;他们在幼年时对他服从的习惯促使他们对他比对其他人更容易顺从。在群居的人们中间,政府是难以避免的,也就是说要有一个人来统治他们,除非疏忽、残忍或其他任何的身心缺陷使他不适合这个位置,那么还有谁能像他们的父亲那样合适呢?可是,如果父亲死了,但是留下的子嗣由于尚未成年,因缺乏智慧、勇气或任何其他品质而不适合统治,而几个家族集合在一处,同意继续聚居时,他们便行使他们的自然自由,选立那些他们认为最能干和可能最善于统治他们的人为统治者,这是必然的。同理,我们看到的那些美洲人,在还没有受到秘鲁和墨西哥两大帝国的武力征服和扩张统治的影响时依然享有他们自己的自然自由,尽管从另一方面讲,他们通常拥戴他们的已故国王的子嗣;但是,当他们发现他软弱无能时,就会另立最坚毅和最勇敢的人做他们的统治者。
106.由此可见,虽然我们查考最早的有关聚居的材料和各民族的历史的记载,通常会发现政府是在一个人的支配之下的;但是这仍不能推翻我所支持的观点,即:政治社会的形成是以那些要加入和建立一个社会的个人的同意为基础的;当他们这样组成一个整体时,他们可以建立自己认为合适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但是,既然这种情况会引起一些人误解,以为政府本来就是君主制的和属于父亲的,我们就不妨在这里研究一下,为什么在最初人们一般采用了这种政府形式。这是因为在有些国家最初建立时,或许父亲的优势地位会促使他在最初阶段把权力交给某一个人;但很明显的是,这种集权于一人的政府形式能够继续下去,并不是由于对父权有任何敬意或尊重,而是因为一切小的君主国,即几乎所有的君主国,在接近它们的起源时,通常都是——至少有时是选任的。
107.第一,最初,父亲对其子女在幼年时期的统治,已经使子女习惯于受一个人的支配,并且他们知道只要这种统治是在关怀、循循善诱、和蔼和慈爱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支配就足以取得和保护人们想在社会中寻求的一切政治幸福。这样看来,他们要选择采用哪种政府形式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因为他们从小对它已经习惯,而且经验告诉他们,它是既便利又安全的。此外,我们还可以说对于人们来说最简单明了的是君主制,因为当时的经验既没有给他们关于政府的种种形式的启示,他们也尚未受到帝国暴政的迫害,不懂得提防特权的侵害或专制权力的骚扰。这些特权和专制权力都是君主政体沿袭下来并施加于人民的。所以当时他们并没有费心去想办法来限制那些对他们赋予权力并支配他们的人的任何专横,也不懂得想办法靠分权来制衡君主的权力,这是很平常的。
他们既没有经受过暴君的压迫,而社会风俗以及财产数量和生活方式都不足以让人产生贪念和野心,这使得他们没有任何可以忧虑或防范的理由,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置身于这种最为简单明了而且又最适合他们当时状况的政体,因为他们当时的情况更需要防御外侮而不是需要法律的多样性。既然一种简单而贫乏的生活方式下的平等把他们的欲望局限在各人的少量财产范围内,很少能造成纠纷,因而不需要用很多的法律来加以裁决。同时又由于侵害行为和犯罪者都为数不多,也就不需要各种官吏来监督法律的程序及司法的执行。他们既然志同道合而加入了社会,就只能被认为彼此有一些交情和友谊,互相信赖,他们彼此间的猜疑必然没有像对外人那样大,所以他们首先要注意和考虑的,只能是怎样防御外侮来保障自己。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置身于一个政体下,推选最贤明和最勇敢的人在战争中指挥他们,领导他们去攻打敌人,并且在这方面做他们的统治者,这是很自然的事。
108.因此,我们看到美洲——它仍是原始时代的亚洲和欧洲的一种模型,那里地广人稀,人力和财力的缺乏使人们不会产生扩大土地的念头,也不致为了扩大土地的范围而引发斗争,印第安人的国王是他们军队的将帅,虽然他们在战争中享有绝对的指挥权,但是在境内和平时,他们却只能行使很小的统治权,只有十分有限的主权;决定是和还是战的通常是人民或议会,而战争本身因为不适合多人领导,指挥权自然会归于国王一人。
109.就以色列民族本身而论,他们的士师和初期国王的主要任务好像就是担任战时的将帅和军队的统率者(但从出入时身先民众,也就是出征和归来时都在队伍前面这一点除外),这在耶弗他的故事中说得很明白。亚扪人起兵攻打以色列,基列族害怕起来,于是派人去请耶弗他回来,耶弗他本是基列族被撵走的私生子。这时他们与他立约,只要他愿意帮助他们抵抗亚扪人,就立他做他们的统治者。这件事情在《圣经》中是这样记载的:“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做元帅。”(《旧约·士师记》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在我们看来,这就等于立他做士师。所以《圣经》又说:“他做以色列的士师。”(《旧约·士师记》第十二章第七节),也就是说,他做他们的将帅有六年之久。
又例如当示剑人对曾是他们的士师和统治者的基甸忘恩负义时,约坦责备他们说:“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争战,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旧约·士师记》第九章第十七节)只提到了他曾充当将帅。的确,这就是在他或其他任何士师的历史中所能看到的一切。亚比米勒虽然被称为国王,但顶多只是示剑人的将帅。以色列的百姓之所以需要立一个国王是因为厌弃撒母耳的儿子的恶行,“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统领他们,并为他们争战”(《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二十节)。这时上帝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对撒母耳说:“我必使一个人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前书第九章第十六节)这样看来好像国王的唯一任务就是率领他们的军队,为保卫他们而战。因此,在扫罗登位时,撒母耳把一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对他说:“耶和华膏他做他产业的君。
”(前书第十章第一节)所以以色列各族在米斯巴庄严地推选扫罗为国王并为此欢呼之后,那些不愿意立他为国王的人也只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反对:“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前书第十章第二十七节)好像他们的本意是要说:“这人不适于做我们的王,他在战争中并没有足够高明的策略和才干来保卫我们。”及至上帝决定把统治权移交给大卫时,说了这样的话:“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前书第十三章第十四节)似乎国王的全部王权就是做他们的将帅;因此,那些反对大卫登位和仍忠于扫罗家族的以色列各族带着顺服的条件来到希伯伦那里,除了别的理由之外,他们还告诉他,他们不得不像服从他们的国王一样服从他,因为事实上在扫罗在位的时候,他已经是他们的国王,所以他们现在没有理由不奉他做国王。他们说:“从前扫罗做我们的王的时候,是你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耶和华也曾答应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旧约·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二节)
110.因此,一个家族逐渐发展为一个国家,父亲的权威由长子承袭,在这个权威下长大的每个人默然地顺从他,而这种统治的顺利和平等对任何人都不妨害,每个人都老老实实地表示同意,直到后来借由时间的考验把它基本确立了,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承继的权利;或者是,因偶然的机缘、居地的接近或事务联系几个家族的后裔聚在一起,联合成为社会——不管是哪种情况,由于在战时人们需要一位能干的将军替他们抵御敌人,以及在那个艰苦而有道德的时代里天真和诚实使人们对他人有深厚的感情(世界上能够存在下来的政府在最初几乎都有这样的情况),这就使国家的最初创始者们通常把统治权交给一个人,除了事情的本质和政府的目的的需要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明确的限制或约束。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使当初的统治权属于一人,都可以肯定的是,它之所以被交付给某一个人,只是为了公众的福利和安全;而在国家建立初期,通常享有统治权的人都是为了这些目的而行使统治权的。除非他们这样做,否则年轻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如果没有这种保姆式的父亲的关爱和对待公共福利的审慎,一切政府都会因为它们幼年时代的孱弱而消亡,而不久,君主和人民就会同归于尽。
111.纵然这黄金时代(在虚荣的野心、恶劣的占有欲和歪风邪念腐蚀人心之前,在权力和荣誉的真正意义被曲解之时)具有更多的美德,因而有较好的统治者和不太恶劣的臣民;并且在当时一方面没有不断扩张的特权来压制人民,另一方面也不存在任何争执来削减或限制官长的权力,因而在统治者和人民之间不存在关于统治者或政府问题的斗争。可是到了后世,野心和奢侈怂恿统治者去维持和扩大权力,不去做人们当初授权给他时要他办的事情,加之谄媚逢迎使君主觉得自己应具有与其人民截然不同的利益,于是人们感觉有必要更加审慎地考察政权的起源和权利,并找出一些来限制专横和防止滥用权力的办法。他们原来为了替自己谋福利而把这个权力交托给另一个人,结果却发觉这一权力被用来损害他们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