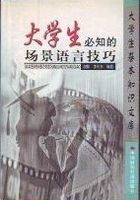70.为了尊敬长者或贤人、保护他的儿女或朋友、救济和扶助受苦受难之人和感谢给他好处之人,一个人承担着各种义务,即使尽其所有和尽其所能也不足以应付全部的这些义务;但是那些要求他克尽义务的人并不能因为这些就享有权威,享有对他制定法律的权利。很显然,这一切并非仅仅由于父亲的名义,也不是如前所说是由于也受恩于母亲的缘故,而是因为对父母承担的这些义务以及对儿女提出的要求的程度可以随着扶养、慈爱、操心和花费的不同而有所出入,这些照顾在两个孩子之间常有厚薄之分。
71.这即表明了为什么身处社会而本身作为社会成员的父母,对他们的儿女保持着一种权力,并享有与自然状态中的人们同样多的权利来要求儿女们服从他。假如一切政治权力都只是父权,两者其实是一回事,那就不可能是这样了。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既然一切父权都属于君主,臣民自然就不能享有。但政治权力和父权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权力,它们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又有各自不同的目标,因此每个作为父亲的臣民,对他的儿女享有同君主对他的儿女一样多的父权;而每个有父母的君主,应对他的父母尽到同他的最微贱的臣民对于他们的父母一样多的孝道和服从的义务;因此父权不能包括一个君主或官长对他的臣民的那种统辖权的任何部分,也不能达到这种统辖权的绝对程度。
72.虽然父母教养子女的义务和子女孝敬父母的义务意味着一方享有全部权利而另一方则必须服从,而且这对双方关系来说都是正常的,但是通常来说,父亲还有另外一种权利,令他的儿女不得不服从他;虽然他和别人都同样具有这种权利,但是由于实施这种权利的机会差不多总出现在家庭中,别处极少有这样的例子,也很少有人注意它,因此现在就把它当成父权的一部分。这就是人们通常将自己所拥有的财产给予他们最喜欢的人的权力。父亲的财产是子女们所期待继承的,通常根据每个国家的法律和习惯按一定比例分配,但是一般来说,父亲有权根据这个或那个儿女的行为是否迎合他的意志和脾气而决定多给或是少给。
73.这对儿女的服从有相当大的约束力。由于享用土地的总要对这块土地所属之国的政府表示服从,因此通常认为父亲能够强制他的后人服从他自己所服从的政府,使他的子女也被他的契约所约束。事实上,这仅仅是土地附带的一项必要条件,而只有那些愿意接受那种条件的人们才能够继承处在那个政府之下的地产,所以这并非什么自然的约束或者义务,而是自愿的顺从。这是因为,既然每个人的子女天生与他自己乃至他的祖先一样地自由,那么当他们处在这种自由状态之时就能选择自己愿意加入的社会、愿意隶属的国家。但是如果他们想享受自己祖先的遗产就必须接受他们祖先原来接受的条件,被这一家产所附带的一切条件所制约。诚然,父亲可以运用这种权利,迫使自己的子女即使已经成年却仍要服从他,并且通常使他们隶属于这个或那个政治权力之下。但是这种服从是用赏赐换来的,而非基于父亲的任何特殊权利;这并不比一个法国人对一个英国人享有的权利更大,如果后者想得到前者的一份财产,当然不肯放弃自由而对他服从。而当财产传给他之时,若要享受这份财产,他就必须接受该土地所在国关于土地占有的规定,不论是在法国还是在英国。
74.由此能得到这样的结论:纵然父亲的命令权只在儿女的未成年期间行使,并且只限于适合那个期间的管束教训;纵然儿女在自己的一生之中和在一切情况下,对其父母必须尽到尊敬、孝顺和拉丁人所谓的“孝道”以及对他们应尽的一切保护和赡养,而并不给父亲统治的权利——即制定规则和处罚他的子女——尽管这一切都不能使他对于自己儿子的财产或行动拥有支配权,但是很容易设想,在世界初期以及现在的一些地方,由于人口稀少而允许一些家庭分散到无主的地区,他们还可迁移或定居到尚无人烟之地,在那种情况下,一家的父亲很容易成为家庭中的君主。自儿女孩提时代起父亲就是一个统治者。由于进行共同生活却没有某种权力中枢是有困难的,于是很有可能当儿女长大之时,基于他们明白或默认的同意,把统治权归于父亲。
而实在地说,这个统治权仅仅是继续下去,并没有什么改变;事实上,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的仅仅是容许父亲一人在其家庭之中行使每个自由人自然享有的自然法的执行权,而当他们还留在这个范围之内时,由于这种容许,就会给予父亲一种君主的权力。然而显而易见,这并不是基于任何父权,而仅仅是基于他的子女的同意。因此不会有人怀疑,如果有一个外人偶然或因事到他家中,在那里杀死了他的一个儿女或者做了任何其他坏事,他可以定罪处死他,或者像处罚他的任何儿女那样去处罚他。当然他这样做,对于一个并非他的孩子的人,不可能是基于任何的父权,而应该是基于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然法的执行权。在他的家里只有他一人能够处罚他,因为由于他的子女的崇敬,他们愿意让他拥有高于其他家庭成员的威严和权威来行使这种权力。
75.因此,儿女们对父亲具有权威并进行统治是很容易的并且几乎是很自然的。在孩童期间,他们就习惯于服从他的管教,向他提出他们之间的小争执;而当他们成人之后,谁更适合统治他们呢?他们的微薄财产和不大的贪心很少会引起较大的争执。当争执发生之时,除了像父亲这样将他们抚养长大并对他们有爱心的人之外,还可以在哪里找到更合适的公正人呢?难怪他们并不对未成年和成年作出区别,而当他们自己无意摆脱被保护者的身份之时,也并不期待那能够使他们自由地处理自身和财产的二十一岁或者任何其他年龄。他们在未成年时所处的那种局面,对他们依然是保护多于限制;他们的安宁、自由和财产并没能得到比在父亲的统治下更可靠的保障。
76.因此,一些家庭中儿女的亲生父亲不知不觉地成为了政治上的君主。若是碰巧他们寿命长,留下了连续几代能干且适当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的继承人,他们就会由于机会、策划或某些情况的促成作用,奠定了各种组织形式和形态的世袭或者选举王国的基础。但是,如果认为君主以作为父亲的身份享有君权,并因此认为这就是足以证明父亲们享有政治权力的自然权利,因为事实上统治权的行使通常掌握在父亲手里——我要说,如果这个论证正确,那么它也将同样有力地证明,一切君主——并且只有君主——应当成为祭司,因为最初,一家的父亲担任祭司并同时担任统治者这个事实是可以同样予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