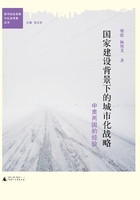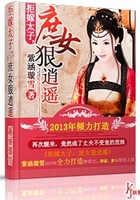150.我们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先祖政治继续存在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身上,直到历史上被埃及奴役的时代”之后,他接着又说:“我们可以依靠明显的足迹追踪这个父权政府一直到进入埃及人和以色列人那里。到埃及之后,这种最高父权统治的行使便中断了,因为他们已经被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征服。”我们的作者心目中的父权政府的足迹——即从亚当传下来并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基于父权的绝对君主权力的足迹——历经二千二百九十年——其实根本不存在,因为在所有那段时期之内他不能找到任何一个例子,证明有任何一个人是因为依据“父的身份”而得来的权利而要求或行使王权的,或是指出有任何一个做君主的人是亚当的嗣子。他能举出的所有证据能证明的仅仅是,在那个时代,世界上存在着父亲、祖先和王。但是父亲和祖先是否有绝对的独断的权力,以及那些王依据什么资格拥有他们的权力,这种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圣经》上完全没有提到。很显然,他们未曾也不能依据“父的身份”的权利要求享有统治权和取得帝位的资格。
151.说“最高的祖先统治权的行使之所以中断,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已服属于一个较强有力的君主”,这句话什么也不能证明,只能证明我之前所怀疑的,即“先祖统治权”这种说法比较荒谬,在我们的作者看来,它并不能够表示他用来暗示的“父”和“王”的权力的意思,因为他假设中的这种绝对统治权是属于亚当自己的。
152.而且,当埃及有一个君主时,又是以色列人在他的王权统治之下的时候,他怎么能够说“先祖统治权在埃及时期已经中断了”呢?除非“先祖权”就是“绝对的君主权”。如果又不是这个,而是别的什么东西,那他为什么要费那么多笔墨来论述一个既不成问题而又与他的目的没有关系的权力呢?如果“先祖权”就是“王权”,那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先祖的”统治权行使就未曾中断。确实,那时王权的行使资格不是在神选的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手中,但是在那之前,我知道它也没有存在过。
除非我们的作者觉得只有神选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宗系才有对亚当的统治权的继承权,可是这与他在上面所说的“传自亚当的王权”的中断有何关系呢?再说,他所举的七十二个统治者——在巴别城口音变乱时期保存了父的权力的人——还有以扫以及以东十二王的例子有何用处呢?为什么把他们与亚伯拉罕和犹大一起列举出来,将其看做是真正“父权政治”的行使的例证呢?如果他认为不论什么时候,只要雅各的后代没有最高权力,世间的“祖先统治权”的行使就中断了。按这种想法,我猜想君主的统治权归于埃及法老或者是别人掌握,倒是可以满足他的需要。但是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很难发现他想要讨论的目的是什么,尤其是在他说道“在埃及行使最高的父权……”时,他想达到什么目的,或者这话为什么就能证明亚当的统治权传给祖先们或其他的人,都含混得无法理解。
153.我原本觉得他是在从《圣经》中向我们举出一些有关从亚当传下来的以父权为基础的君主政府的证明和实例,而并非拿给我们一篇犹太人的历史,这些犹太人要在很多年以后,等他们变成一个民族时才能发现他有君主,而且历史中也从未提过这些君主们是亚当的后裔,或者他们是在具有父权之时,依据父权而成为君主的。我原本想,既然他讲了如此多关于《圣经》的故事,想必他会从那里罗列出一系列的君主:他们都明明白白地具备亚当父权所需的条件,他们作为他的后嗣,对他们的臣民享有并行使父权统治,因此这就是完全的父权政府。谁知他既没有论证先祖们是君主,也丝毫不提君主或先祖是亚当的继承人,哪怕是假冒的继承人也行。如此一来,倒不如说证实了先祖们都是绝对的君主,先祖和君主的权力仅仅是父权,而且这个权力是从亚当那传给他们的。我相信,一切这些命题均能够从菲迪南多·索托有关西印度的一群小王的杂乱记录中,或从任意一种北美洲的近代史中,或从我们的作者引用荷马的希腊七十个王的故事中得到印证。这效果跟我们的作者从《圣经》中拿出的那一大堆他详细罗列出来的君主们同样的好。
154.我认为他还是抛开不谈荷马与他的特洛伊战争为妙,由于他对于真理或君主政体的强烈热情已经令他对诗人们和哲学家们产生了如此激烈的愤懑,以致他在序言中向我们讲述道:“如今,喜欢紧跟诗人和哲学家们的脚步后面跑的人数不胜数。他们想从中寻找一种能够给他们带来些自由权利的政府起源学说,让基督教遭受耻辱,而且开始散播起无神论来。”但是,这些异教的诗人和哲学家们——比如荷马和亚里士多德——但凡可以提供一点似乎还能够满足他的需要的东西,就都没有被我们这位热忱的基督教政治家所反对过。
不过,让我们还是回到他所讲的《圣经》上的历史来吧。我们的作者随后向我们讲述:“当以色列人摆脱压迫回去以后,上帝就对他们十分关心,相继选出摩西和约书亚做君主来统治他们,代替最高的父亲的地位。”如果文中以色列人“摆脱埃及的压迫回去”这话是真的,他们一定会回到自由的状态,而且这话肯定包含着他们在受欺压之前和之后都是自由的含义,除非我们的作者认为,主人的改变就叫“摆脱压迫回去”,或者一个奴隶由一只奴隶船搬到另一只船上去就叫“摆脱压迫回去”。那么,假使说他们“摆脱压迫回去”了,显而易见的,在那个时代——即使我们的作者在序言中讲了些相反观点——一个儿子、一个臣民与一个奴隶之间是有差别的,不论是在遭到埃及欺压之前的先祖们或是之后的以色列统治者,都未曾“将他们的儿子或臣民看做他们的财物”,如同处理“别的财物”那样,用绝对的支配权来统治他们。
155.流便将他的两个儿子献给雅各做担保,犹大为了最终让便雅悯安全逃离埃及,担当了担保品,这是很清楚的实例。如果雅各拥有对他的家族所有人的支配权,就像支配他的牛或驴一般,或者像主人对于自己的财物一般,上述的事就全都是空谈、多余的,只不过是个笑料而已,而且流便或犹大出来当担保,确保便雅悯返回一事,就正如一个人从他的主人的羊群中牵走两只羊,取一只出来当担保,确保他能够完好地将第二只送还一般。
156.在以色列人逃离了这种压迫之后又如何呢?“上帝就对他们十分关心。”在他的书里竟然有一回让上帝开始关心起人民来,这可真是非常不错,因为他在其他地方谈到人类时,仿佛上帝丝毫不关心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而仅仅关心他们的君主,至于其他的人民,人类的社会,都被他看做是几群家畜,只供他们的君主奴役、差遣和享乐。
157.上帝相继选出摩西和约书亚当君主来进行统治,这是我们的作者想到的一个聪明的论据,用来证实上帝关注父的权力及亚当的继承人。在这里,为显示上帝对他自己人民的关怀,他精选出做他们的君主的人竟都丝毫不符合做君主的资格,因为摩西在利未族中,约书亚在以法莲族中,都不具备父的身份。不过我们的作者讲,他们是替代最高的父亲地位的。若是上帝曾在任何地方像他挑选摩西和约书亚这般明确地宣告过他将这样的父亲当统治者,我们就足以确定,摩西和约书亚是“替代他们的地位的”。可是,这是一个仍在争辩中的问题,在这个问题未能更好地被论证之前,摩西被上帝选为他的人民的君主,无法证实统治权是归亚当的后裔还是归“父的身份”所有,就像上帝选出利未族中的亚伦当祭司,无法证实祭司一职归亚当的继承人或归“最高的父亲”所有一般;因为,即使统治者和祭司两种职位都并非安排在亚当的继承人身上或父的身份之上,上帝依然能选择,亚伦当以色列的祭司,摩西当统治者。
158.接着,我们的作者说:“同理,在挑选了他们以后不久,上帝又设立了裁判官,以便发生危险的时候守护他的人民。”这证实父的权力是政府的渊源,与原来一样,是由亚当传给他的继承人的。不过在这里,我们的作者好像承认那些在当时都是人民的统治者的裁判官们仅仅是些勇猛的人们,在危险的关头,人民会推选他们当将军来守护他们。难道只能以父权为统治权力的依据,否则上帝就无法设置这些人员吗?
159.不过,我们的作者讲,在上帝为以色列选立君主的时候,他重新建立了父权政府世代传承制这一个原始和悠久的权利。
160.上帝是如何重新建立的呢?是用一种法律吗?或是一种成文的号令吗?我们无法找到这样的依据,于是,我们的作者要表达的就是,在上帝为他们立君主的时候,他就“重新建立了这权利”等。让一个人占有他的祖先曾经享有的而他自己根据世袭权也有资格享有的权利,这就是所谓在实质上重新建立对父权统治的世代承袭权。其原因是,第一,如果不是他的祖先原来有过的政府,而是其他政府,那就应当被称为开始一种新的权利,而不是继承一种“古老的权利”。如果一个君主,除了赐予一个人多年来他的家族早被掠走的早期遗产以外,还另外赐予以前未曾被他们先祖占有过的财物,在这种场合,只有对原来被他们的祖先占用过的产业,才能说是“重新建立世代承袭的权利”,至于别的产业,就不可以这样说。所以,如果以色列诸王的一切权力多于以撒或雅各所有,那就不叫在他们身上“重新建立”关于某种权力的继承权,而是赋予他们新的权力——无论你如何称呼这种权力,“父权”也罢,不是“父权”也罢。而以撒和雅各是否拥有跟以色列诸王同样的权力,请大家参照上文提到的话仔细考虑,我不认为他能找到亚伯拉罕以撒或雅各拥有任何一点王权的证据。
161.其次,这个获得此种权力的人,除非确实有继承之权,并是他所继承的人的真正下一代继承人,否则对一切东西都不能有所谓“古老的与原始的世袭权利之重新建立”。能说在一个新的家族中开始的事情是重新建立吗?把王位赋予一个无权继承它的人,而这个人在世代承袭没有中断过的情形下,又完全没有可能提出获得这种权利的托词,这能叫做一种古老的世袭权的重新建立吗?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扫罗是便雅悯族出身。那是不是“悠久的和原始的世代继承权”在他身上“重新建立”了呢?第二个王是耶西最幼的儿子大卫,而耶西是雅各的第三个儿子,犹大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