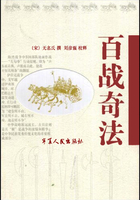他是谁
刘晓莹译
现在,我正记录的,是一件诡异而又恐怖的事情。
那是几个月前,我由于心脏病复发,住在医院里疗养。待病情有所好转,院方就把我从加护病房转到了一个普通的单人房,它处在心脏病房的最里头。
那是一个又长又窄的房间,灯光昏暗,照明不怎么好。附近还有十余间同样的单人病房。
刚开始的两天,我都紧闭房门以防其他房间的电视声或收音机声的打扰,我喜欢安静地看书。
有一天,当我正在阅读时,房门被轻轻打开了。我当时没有听到开门声,不过没等抬头,我就感觉到有人站在门边。
我希望来人是位访客,但我又失落又烦躁,因为来人居然是医院的理发师。他身穿一件薄料的、看上去有点儿褴褛的羊驼呢夹克,手里拎着一只难看的黑色袋子。
他没有开口说话,只是抬起浓密的眉毛,做无言的询问。
我摇摇头:“现在不理,晚些时候再说吧。”
他的失望显而易见,在门边逗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悄悄掩上了门。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再无法静下心来看书。我必须承认,他吓了我一跳,他的打扰惹怒了我。我知道,对一位心脏病患者来说,这种情况可不太妙。
我服下镇静剂,想休息一下——但没成功。虽然如此,那天晚上我睡得不坏(当然是在安眠药的帮助下)。第二天上午,在一连串诸如洗澡、换床单、量体温等各类事情之后,我坐下来准备再看书。
我发现我不能集中精力,尽管前一天那本书很吸引我。
最后,当我环顾四周时,我懊恼地皱起眉头,因为我明白烦恼是什么了。
在我的要求下,门再次被关上。可是现在,说不出为什么,我发觉自己竟然不想它关上。由于我仍不能下床行走,所以,我按响了护士的铃声。
一位活泼开朗、浅黄头发的瑞典籍女护士走了进来。她说:“这么快就厌倦隐士的生活啦?我以为你会改变主意的!”我笑笑,带着温驯的姿态。她说完,走出去,任房门开着。
我低下头看书,但潜意识里仍在思索着房门的事。好吧,我不得不承认一件事实:我阅读的时候,绝对不想要那个理发师再来开房门,打扰我、惊吓我。电视声和收音机声依然没完没了的传来,但我尽量充耳不闻,径自看书。就这点上,我算是部分成功。
午饭之前,我略有睡意,便搁下书,打了个盹。突然,一阵恐惧刺耳、令人发指的尖叫声将我从床上惊醒。我觉得那声音来自于附近的病房。
我的心脏怦怦地跳动,暗暗对自己说,那声音来自电视。我安慰自己,那一定是谁不小心把电视音量开到了最大。
几分钟之后,病房的走道上传来一阵骚动,人生嘈杂。只见护士和医院的工作人员匆匆而过,我之前竟然不知道这病房有这么多的人。
医生们行色匆匆,一阵低低的命令、谈话声过后,就是几近完全的沉默。渐渐地,护士和工作人员都回到病房的走道,没多久,一具从头到脚都裹着黑胶布的尸体被推了出来,从我的病房门口经过。
我静候了一会儿,然后按响了护士铃。黄发护士的助手急忙进来,我诧异她的反应如此之快,只见她的脸色有点儿苍白。我问:“发生了什么事?”
她犹豫片刻,然后耸耸肩说:“过道对面的艾克先生。”
“心脏病猝发?”
她点点头。
我注意看了看她的脸。“一位患有心脏病的人,那样叫是不是有点儿不正常?”
她再次犹豫了。
当她再开口,用字就变得小心至极,说道:“依一般的病情来看,是不大正常。不过,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呃,也许是他病情加剧,痛苦不堪。大多数的患者都是无力地倒下,但是他居然高声尖叫,是有点儿——不正常。”
她微微一笑,可那笑容看起来有些勉强。“不过,你不要去想它。你的病情正在逐渐恢复,安静读你的书,不要瞎想。”
我怎么可能不瞎想。我白天在想,夜晚也在想,最后他们没有办法,给了我一颗额外的药片,才使我安静下来。
日子平静地过了两天,又是一个下午,当我正在阅读时,门再次开了。那种被紧紧压迫、心烦意乱的不愉快感又窒息而来。
我一抬头,门边站的果然还是那位穿羊驼呢夹克,手提黑色破旧袋子的理发师。和上次一样,他微皱浓眉,做一种无言的询问。
我也和上次一样,气愤至极,因为他又吓了我一跳。我心想,这人真可恶!虽说门没关,但也应该有礼貌地轻敲两下啊?
“我不理发!”我强忍着怒气对他说,“我需要理发的时候自然会请护士小姐通知你!”
他依然逗留在门边,脸色柔和,但没有表情,就像戴着一副面具。他那黑而明亮的眼睛在闪动,失望地闪动。
那样子又不仅仅是失望,但我说不清是什么,我可以说是憎恨,但似乎太轻了些,那样子更像是深仇大恨。我觉得血液瞬间涌上了脸部和颈部。
“请离开好吗?”我暴躁地对他说,“你太无礼了!”
我可能是幻想,不过,我觉得他像是微微鞠躬,一分钟之后,离开了门口。
我才开始平复下心情,满心等候吃顿美味的晚饭时,从附近病房又传来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这回不是高而尖的嗓音,而是一种抑制的低泣。
我僵住了,心脏怦怦跳起来,接着我听见大叫声,然后是跑步声。那声音听起来很轻,像是惊慌地朝防火梯的方向跑过去。一分钟之后,伴着一阵沉重、有意的脚步声,三四阶并作一步地追了下去。
我看不大清楚走道,另外,这次发出叫声的病房在距我较远的地方。接下来和之前一样,我听见人们急速地过去,叫喊声、命令声、低喃声,然后复归平静。
在我的想象里,我仿佛看到担架再次沿过道推出,上面躺着一语不发、冷冰冰的尸体,一袭黑色的胶布盖在上面。
那天,我那位黄发护士的助手正好休假,新护士是位红发的娇俏女人,由她来为我端上晚餐。显然,她的愉悦表情同之前的助手护士一样,都是勉强装出来的。
我问她:“这回是谁?”
她沉默了一会儿,佯装安排我的餐盘,“梅先生,三七五病房的。”
我的病房是三七七,梅先生距我只有两屋之隔。
我想从新护士那儿多打听一些消息,但没有成功。她说她当时不在现场,听到梅先生不幸的消息,还只是几分钟前。
第二天,我试图从别的护士那儿打听出什么消息,但都以失败告终。她们若不是自己不想说,就是接到指示不让说。
她们向我保证说,梅先生是安静地去世,并没有呻吟或者低泣那回事。她们告诉我,梅先生在失去意识之前,曾按响了护士铃。她们坚称,如果我听到了什么哭声,那也是“不自主的”。
至于我所提的,有关脚步声奔向防火梯的事儿,她们不认同地耸耸肩,说或许是因为我打盹,幻想出的声音。
我试图忘记那段插曲,但心中却充满狐疑。那天下午,我正在阅读来信,听到有轻轻的敲门声,我抬起了头。
一位衣着整齐、头发光亮、蓄有八字胡的年轻人正站在门旁。他身上穿着洁白的夹克,手上拎着一个褐色的小箱子。
“先生,理发吗?”
我踌躇了一下,“呃——现在不理,或许一两天内吧。”
他和蔼地点点头:“遵命,先生,过一两天我再来。”
他一离开,我就后悔没有立刻要他理。一来,我需要理发;二来,我要向他询问医院里另一位理发师的事。我希望他永远滚蛋。
我的身体逐渐康复:在新理发师再来为我理发之前,有一天下午,我坚持要乘轮椅到日光浴室闲坐一小时。
当我无聊地坐在那儿的时候,医院的一位保安人员信步走来,我招呼他,他坐下陪我聊天。
在我个人的众多“职业”中,我曾干过许多不同的工作。比如,多年前,我就曾兼职过警卫的差事。因此,医院的保安人员与我一见如故,友善而亲切地聊了开来。
难免的,我们的谈话涉及到了心脏病房的两件死亡事件。我立刻注意到,这位新朋友的话变少了,甚至好几次不安地左顾右盼,仿佛怕有人听见。他像是在斟酌一个决定,最后终于耸耸肩。
“如果你能答应我不向任何人——特别是这儿的任何人说的话,我就告诉你一点儿故事。”他说。
我以人品对他起誓,不会说出去一个字。他皱了皱眉,不知该如何启齿。
“呃,那两个人的死亡相当离奇。首先,他们俩都面露惧象,死在床上的时候两眼睁开,像是看见了什么恐怖的东西死死地盯着,因惊奇过度而死亡!两次,在他们大叫或呻吟之后,都有人看见一个小矮个,手提一只黑色小袋子向通道尽头跑!事实上,第二次我也看到了,并且还追了上去。”
我觉得心脏怦怦跳,“你可以描述下那个人吗?”
“我看到的多半是他的背影——那人瘦瘦小小的,身穿一件薄薄的灰色夹克,手里拎着一只破旧的黑色小袋子。我还瞄到了他的侧面,他皮肤挺光滑的,脸上毫无表情,眉毛又浓又黑,就这些,再没有什么可描述的了。”
“那不是医院里的另一位理发师嘛!”我马上回答。
我的新朋友瞠目而视:“另一位理发师?别开玩笑了,医院里只有一个理发师——一个年轻人,穿白色外套,蓄着八字胡,他在这儿已经做了一年多了。”他犹豫了一会儿,“嘿,莫非你也见过这个人?”
我挥挥手:“现在不要管那些,你继续说下去。”
他搓搓下巴:“呃,第一次的时候我没看到这个家伙,但第二次我正好在一楼,就在梅先生呻吟,按响护士铃时,我看见这个矮子从他的房间跑出来,于是我立刻沿通道追了上去。他从防火梯跑下去了。”
“逮到他了吗?”
他摇摇头:“根本没机会,他像只兔子一样地逃,像只鹿一样,越过停车场的围篱。我花了两三分钟才爬过围篱,那时候,他已经无影无踪。”
“但是最疯狂的部分还没来呢,你知道他拎着的那只黑色小袋子吧?”他看着我说。
我点点头。
“呃,当他跳越围篱的时候,那袋子钩住了上面的铁丝,掉落在停车场。之后我捡起它,你猜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我急切地说,“别卖关子了!”
“泥土!”他回答,“一袋子的土!就是地上那种土!”
“我们在两位死者的床上也发现了同样的土!” 他继续说道。
他又看看四周,然后说:“也许我不应该把这个故事告诉你,但既然告诉你,我就把结局也告诉你吧。”
“呃,我把那黑袋子交给当局。不过,在警方没有接手之前,我偷偷用纸袋装了一点儿土,然后我把它交给一位在化验室工作的朋友,他有显微镜和各种化验所需的东西。你知道他检验出了什么?”
“我无法想像!”
他倚近:“那土,那些泥土——他发誓来自坟墓!”
我又觉得心脏怦怦地跳起来了,但我佯装怀疑的口吻:“噢,他怎么判断的?”
“从掺杂在其中的小东西:花岗岩和大理石的细碎片;花环和人造花的残渣。不只那些,我朋友还说,土里还有两小片碎骨,经过检验,那正是人类的骨头!所有的土豆混有青苔,就像是从坟墓一处潮湿、黑暗的角落里挖掘出来的!”
故事到此为止,但我永远无法获得合理的解释。那个面无表情、眉毛浓黑、眼睛闪烁的小矮人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一位自认聪明的朋友,说那故事的答案很明显。他告诉我,拎黑色袋子的男人是个典型的精神病患者,他或者是生下来五官就有问题,或者是某次车祸受了伤。他带着面具,潜入心脏病房,然后摘掉面具,吓死两位病人。我朋友说床上遗留下的泥土,只是一位心智不正的人所营造的一种恐怖的奇想。
这样的解释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可我人不相信那是对的:我个人觉得,由于某些模糊的超自然原因,那个我误认为是理发师的恐怖东西,根本无法进入一位病患的房间,除非他得到应允。我想,那两位惊恐叫喊而死的心脏病患,曾经允许他进入病房。当然,不会有人注意到他们是否需要理发!我无法说出我的观点,它只留存在我的心中,如此而已。
不过,有一点我敢确定,假如当时我答应那位要命的人给我理发,你就读不到这个神秘的故事——因为我相信,我不会活下来写这篇文章。
我的余生里,这个问题将永远挥之不去:他是谁?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