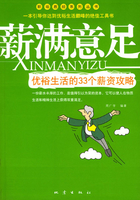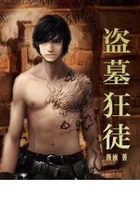傍晚,夕阳在疯狂的燃烧之后终于变成了天边一道灰白的颜色,就像小河里翻起的鱼肚那么苍白死寂,并被黑暗吞噬着不断缩小。又是一个一无所获的日子,其实已经成功了,当我和哥哥俯卧在草丛里,看着母亲踉跄着把一只羚羊扑倒时,我们激动得止不住的发抖,已经五天没吃任何东西了,别说我们受不了,就连母亲的脚步都有些虚浮不稳了。我们跳起来冲过去,这是一只刚刚成年的母羚羊,这个年纪的羚羊身体灵活敏捷、速度快,没有拖累,是比较难抓的,但它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大意。它可能已经凭着自己较好的条件摆脱了无数次的追杀,由此认定这世上没什么能够追得上它,所以它只顾低头吃草,昂首赶路,却没有注意到已经在草丛中潜伏了数小时之久的母亲,闲庭信步的走进了她的攻击范围。现在它无力地躺在地上,脖子上有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正往外喷涌着鲜血,它为它的大意付出了代价,正值盛年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它死于它的骄傲。
我们胡乱撕扯着羚羊,不得要领的结果就是费了半天劲也撕不开它的皮毛,母亲帮我们划开它的肚皮,我们立刻凑了上去,大口大口地喝着涌出的热血,滚烫的鲜血一咽下,腹中立刻升起一股暖流,舒服得我打了个哆嗦。我开始撕扯羚羊柔软且营养丰富的内脏,只是刚刚咬下第一口,就听到了一个让我万分厌恶的声音,尖锐的、凄厉如小鬼悲鸣,这是鬣狗的声音。一只鬣狗正在向我们靠近,它头顶上有一块平平的伤疤,像是被人连皮带毛掀去了一般,导致整个脸都扭曲的变了形,嘴歪向一边,牙齿横七竖八地露在外面,更显得丑陋不堪。怎么办?我看了看母亲,一只鬣狗可以抵挡一会儿,但鬣狗一般是成群行动,你看它现在呜呜叫着应该就是在向它的同伙通风报信吧,天知道一会儿会来多少只呢?母亲放低身子,用嘶吼和出击的动作威慑鬣狗,警告它不要靠近。
鬣狗哪会把一只带着孩子的雌狮放在眼里,它一边慢慢地逼近,一边继续招呼着它的同伙,虽然碍于母亲暂时无法冲过来,却也极大地威胁到了我们的安全,我们都明白,晚餐保不住了,真是可恶,这群无耻的强盗。我和哥哥急忙低头又咬了一口,旁边的草丛里就冒出了十几只鬣狗的脑袋,再不走的话连我们自己都会有危险,母亲只好放弃,带着我们退到了十米开外,鬣狗们怪叫着一涌而上,撕扯着我们的劳动成果,我远远地看着,愤怒却又无可奈何。激动之后的失落是一种折磨,腹中的饥饿感更强了。以前在狮群时,我哪会把它们放在眼里,我曾亲眼看见父亲咬断一只鬣狗的脖子,如果他还在的话,也不会让我们受这样的屈辱。我们带着疲惫和饥饿退到了一座小山旁,这是一座由石头组成的山,到处都是风化的沙石,风一吹哗哗作响,进入夜间后显得既冷清又诡异。
这里没有植被,非常贫瘠,食草动物一般是不会到这儿来的,当然掠食者也没有兴趣光临,我们找了个避风的地方躺下,准备在这里度过又一个草原之夜。非洲草原的夜晚依然是各色动物活动的舞台,永远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声音,有掠食者的争斗、咆哮、追击、杀戮,也有食草动物的反刍、逃窜、惨叫、哀号,夹杂在呜呜怪叫的风里,所有的高亢的、低沉的、激昂的、凄厉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像哭泣,轻轻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一种冰凉刺骨的液体,被传得很远很远,淹没整个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让你在高达四十度的高温里,依然冷的发抖。这就是草原的声音。趴在石头山旁,声音又多了一种,就是在风中乱滚的沙石的哗哗声,和我们肚子里咕咕声的合鸣。麻木的胃因为有了热血的刺激而苏醒,正在急切地盼望着一顿大餐,落空后失望又气愤,在腹中造起反来,折磨得我彻夜难眠。我转头看看母亲和哥哥,他们同样也没有入睡,哥哥烦躁地翻着身,母亲则面无表情地看着黑沉沉的天空。被饥饿折磨的睡不着觉的确是一件糟糕透顶的事,但今天饥饿却救了我们的命,因为没有入睡,我们及时地发现了鬼魅般潜到身边的杀手,并在最后时刻逃过了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