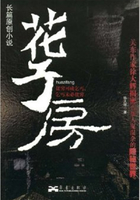因为被那只花豹发现,这里不能再住了,吃饱后,母亲盘算着搬家,我们在哪个地方都住不久,总是会因为安全或食物等原因搬家,对此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虽然没有狮群的保护,虽然终日生活在惊吓与颠沛流离之中,日子还是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们也在一天天地长大,我和哥哥就像春风吹过的青草,不经意间,就长高了很多,食量也开始大量的增加,母亲的乳汁已经不够我们裹腹了。有一天,母亲狩猎回来,带了半只蹬羚的残骸,啪的一声扔在地上,已经饥肠辘辘的我们欢呼一声围了上去,等着母亲趴下来好吃奶,但母亲一反常态地走到一边,并不理睬我们。我们有些疑惑地想跟上去,却被母亲大声地喝止住了,她挥舞着爪子阻止我们靠近,我愕然地看了看哥哥,他也很不解地看着我,我们都有些委屈,从来没见过母亲这样。我们就这样饿了一个晚上,不管怎么哀求,母亲就是不让我们靠近,到了天亮时,我有些饿得受不了了,扭头看到母亲扔在地上的半只蹬羚,犹豫地靠近嗅嗅,学着母亲的样子咬了一口,什么也没咬下来,我皱皱眉头。
哥哥也凑了过来,试着舔了舔,不好吃,他又跑过去想向母亲撒娇,结果被母亲一脚踢了出去。我开始明白母亲的想法了,她认为我们已经不用再靠她的乳汁生活了,我们需要独立,当然,最起码要先学会吃东西,不是吸吮乳汁,而是与别的狮子一样吃肉,这是独立的第一步。我低下头,开始用力撕扯蹬羚的肉,隔夜的尸体已经变的僵硬,对我们来说简直难以下咽,但我没有放弃,继续用力,终于撕下一块带着凝固血迹的肉块,没嚼几口就吞下肚去,差点噎死。但当肉块下肚的那一霎那,我忽然找到了感觉,这是一种说不出口的很奇妙的感觉,就像本来就应该如此一样,我们就是应该吃肉,这是我们的本能。我立刻开始咬第二口,哥哥也跑了过来,与我一起分食着做为狮子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餐,从小心翼翼到狼吞虎咽,蹬羚的残骸在我们的撕扯下一点儿一点儿地减少,最后只剩下一个没有多少肉的头颅。母亲在一边看着,开始微笑。
脸上沾满了暗红色的血迹,牙齿间残留着蹬羚的肉丝,我抬起头看着草原的天空,然后摸了摸鼓起的肚子,我喜欢这个味道,这个血腥的、粗糙的、残暴的、毁灭的味道。母亲开始带着我们一同出去狩猎,因为我们的脚力已经可以跟上她的速度了,虽然还不能参与狩猎,却也可以在旁边跟踪学习。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不用再像以前一样长时间离开母亲的保护了,虽然还是需要不断的流浪躲藏,却可以始终和母亲在一起,不需要在石缝、草丛等地方一窝就是两三天。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们也真正开始流浪了,走到哪儿算哪儿,没有固定的家。我们一般跟着猎物跑,食草动物跑到哪儿我们就到哪儿,但要小心不能踏进其他掠食动物的领地,不然就会遭到追杀。只是,只要是食物多,有水源的地方,又怎么会没有掠食动物呢?我们人单势孤,就算是遇到豹子、鬣狗等小型掠食者,也不是它们的对手,更不用说是我们的同类狮子了。
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别人不屑去的贫瘠地区游荡,看看有没有运气碰到一只兔子什么的,只有饿的受不了了,才会闯进水草肥美的地域狩猎,这种时候是非常危险的,母亲既要集中精力猎杀那些灵活擅跑的羚羊,还要小心提防隐在暗处的杀手,我们跟着在高过头顶的草丛中奔跑,几乎帮不上什么忙。这样的狩猎出击十次会有八次空手而归,剩下的几次就算得手也吃不了几口,还百分之百地会遭到鬣狗、秃鹫的抢劫骚扰,我们的肚子在饥一顿饱一顿中挣扎,我们的精神在这种看不到尽头的挣扎中一点儿一点儿地崩溃。在食物丰盛的雨季都吃不饱,旱季到来我们该怎么办呢?我看着母亲,疲惫和焦虑让她在飞快地消瘦和苍老。我们吃得太多却长得太慢,像寄生虫一样在一点儿一点儿地吸干她的血肉和精神,她一定也在烦恼这样的问题,其实解决的办法大家都知道,就是再找一个狮群。融入其他的狮群是缓和我们现在困境的唯一办法。但是……就算是一只健康独身的雌狮,被其他狮群接纳的可能也微乎其微,更不用说是带着拖油瓶的母亲了。如果母亲想改变她的命运,最好的办法就是抛弃我们,就算她曾经为了我们而离开家,现在也到了认清形势的时候了。
想要在草原上生存下去,就要看得清形势,要知道怎么用最小的牺牲来保全最大的利益,要知道在生命的交叉路口该如何抉择。这是我从出生就在学习的东西,母亲当然比我更清楚,不然我就不会有过被她抛弃的经历了。如果她抛弃了我们投入新的狮群,有可能很快就会有新的孩子,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这无疑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从我自身来讲,如果母亲做出这样的选择,我是不会怨恨她的,以前会,但经历了家族崩溃,亲人惨死,到现在过着颠沛流离日子的我不会,至少她曾为我们放弃过一切,对于我们,她已经仁至义尽了。如果她真的这么选择了,那也是我们的命。
母亲弯下身亲吻着我,我立刻投入她的怀中,讨好乖巧地亲吻她的脸庞,例行的亲热一番后,我向下找到她的乳头含在嘴里,她的乳汁已经很少了,而且淡如白水般无味,我才吸几口就吸不到了,于是我用尽全身力气猛得一吸,母亲触电般的抖了一下,一股血腥味在口中漫延开,是血吗?不会吧,乳汁怎么会有血的味道呢?一定是幻觉,我闭上眼睛,继续吸吮着。在母亲面前,我尽量让自己显得楚楚可怜,索命小鬼般紧紧抓住她的那颗舔犊之心不放,我是不会怨恨,但也不会轻易放弃生存的机会,母亲现在是我生存的唯一希望,所以我是不会放她自由的。看着她一天一天地衰弱、消瘦,我很心痛,但我不会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