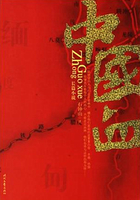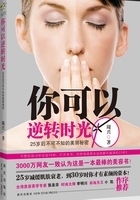张警官的办公室是一个很大的套间,靠西边的窗户旁边,放着几张背靠背的黑色办公桌,每一张桌子后边,都坐着一个穿警察制服的人。他们的身边都围着一些男人或女人,正埋头填写着什么东西,因而并没有注意到站在门口的丛苇。
让丛苇惊恐的是,靠近东边的墙根下,满满地蹲了一长溜人。他们的衣着打扮奇形怪状、五花八门,留着各式各样的头型,头发也染得五颜六色,耳朵上戴着乱七八糟的耳环。当其中几个闻声抬起头来的时候,丛苇看到,他们的鼻子上居然像耕牛一样被打了个洞,各种不同性质的金属玩意儿悬挂在那些小洞眼上,看上去十分怪异。
由于人多,房子里的气味非常浑浊,熏得丛苇差一点呕吐出来。她呆呆地站在房门口,恍如来到了另外的世界,那么陌生,那么怪异。
“请问您找谁?”
一个声音突兀地响了起来。丛苇恍然大悟,举目看去,见房门后边还有一张办公桌,桌子后边坐着一个面目清秀的小警官。虽然也穿着制服,可是丛苇觉得他也就只有十七八岁的样子,跟墙根下蹲着的那一溜人的年龄相差无几,似乎还没到成年,这让她情不自禁地想到她那些可爱的学生们。
丛苇不自然地笑了笑,恭恭敬敬地说:“我找张警官。”
想了想又加上一句,“是年龄比较大的那个张警官,是他打电话让我来的。”
那个小警官稚气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友好地指了指靠窗的那几张桌子:“张警官在那边。您是这些孩子中某个的家属吧?”
“哦……就算是吧。”
丛苇为难地笑了笑,向那个小警官点了点头,表示感谢。然后,走过那一长溜蹲在墙根下的人,慢慢向窗子边靠近。
人太多了,丛苇只得小心翼翼地挪动着,生怕碰到了哪个人的膝盖或脑袋。
一些胆子大的人趁机抬起头来,目光蔑视地打量着丛苇。
丛苇惊讶地发现,那些蹲着的人,大多数都很年轻,有的看上去甚至只有十五六岁的样子。
“看什么看?老实点儿!”
门背后那个小警官走了过来,见场面有些骚乱,厉声吼叫道。
那些极不友好的目光,瞬间充满了惊恐,那些抬起来的头,立刻齐刷刷地低伏了下去。
丛苇一边小心谨慎地通过那一长溜“人墙”,一边留心地注意着。但是,她没有在那些人中发现林黄鹂。
丛苇的心又开始狂跳,怎么没有黄鹂呢?她究竟怎么样了?
好不容易靠近了窗边的桌子,丛苇艰难地挤进人丛,她这才注意到,那些面孔阴沉的男人女人,应该都是跟她差不多的身份。因为他们拿笔的手,无一不是在表格上“家长”一栏里抖动着签下自己的名字。
“请问,哪位是张警官?”
丛苇平静了一下心绪,把装着两条中华烟的黑袋子放在身后。她发现那些家长没有人像她一样拎着东西,觉得自己太世俗了,有些不好意思。
“我就是。您是……”
一个约莫三十多岁将近四十岁的男人,从桌子后边抬起头来,审视地望着丛苇。
“哦,我是林黄鹂的……”
丛苇一时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定位自己跟黄鹂的关系了。说是她的阿姨吧,却跟她妈妈没有血缘上的姐妹关系,要说是黄鹂的妈妈,那显然更不合适。
迟疑了一下,丛苇只好很别扭地说:“我是林黄鹂妈妈的好朋友,黄鹂叫我阿姨的。”
“咦,林黄鹂的妈妈怎么不来?”张警官有些莫名惊诧了,询问地望着丛苇。
“黄鹂的妈妈……生病住院了,所以委托我……”
“那她的爸爸不会也生病住院了吧?”张警官似乎生气了,口气有些生硬起来。
“有些做家长的啊,真是太不负责任了,孩子不好好管教不说,出了问题倒知道丢人现眼了!这种事情,怎么可以委托别人呢?真是的!面子重要还是孩子重要?”
尽管张警官并不是在说丛苇,可她还是忽地涨红了脸。
“林黄鹂的爸爸……”想起正在监狱里改造的林启辉,丛苇觉得真是难以启齿了。
“你最好让她的直系亲属来!我们可是要备案的!”张警官板起面孔,语气有些严厉地说。
“自己的孩子出了事情,却委托别人来处理!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由别人代替的!”
丛苇觉得张警官的言外之意,是在责怪她不知轻重,胡乱蹚浑水,不由得浑身一阵燥热。是啊,她跟林黄鹂毕竟没有一点血缘关系,自己为了刘贝拉,硬着头皮答应来处理这件事,看来是不太理智,考虑也欠周到了。可是,贝拉那个样子,她又怎么忍心袖手旁观呢?
“哦,我的意思是说,孩子最好还是交给她的爸爸或妈妈来领合适,你不要误会啊。”
张警官可能发现了丛苇的窘迫,点点头,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儿笑纹。
丛苇想了想,无可奈何地咬着嘴唇,轻轻地说:“林黄鹂的爸爸,正在监狱里接受改造……”
张警官蓦地抬起头来,眼睛一下子睁大了,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样,疑惑地望着丛苇。
“是的,黄鹂的爸爸已经进去快两年了。”
话一说出口,丛苇发现自己从容了许多,强调一般重申道。
“是这样子啊?”
张警官垂下眼帘,无端地长叹了一口气。
“难怪林黄鹂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看来跟她的家庭环境不无关系啊。现在有些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犯事的时候,怎么就不为孩子想想呢?”
张警官这句无心的话,却让丛苇刚刚平静下来的心情又掀起滔天巨浪,许戈飞和莫怀卿的面孔,交替出现在她的眼前。她的心情异常沉重起来,两只手下意识地互相绞扭着,欲哭无泪地沮丧。
“既然这样,那就由你先代替林黄鹂的家长填一下表格吧。”
张警官板起的面孔有所缓和,甚至有些和颜悦色了。他把一张表格推到丛苇面前。
“姓名、籍贯、年龄、政治面貌……要详细填写清楚,要备案的。”
丛苇拿过桌子上的笔,开始按照张警官的吩咐,详细地填写起来。
“哦,您的字写得真漂亮!练过硬笔书法?”
张警官歪起脑袋,认真地打量着丛苇的字,欣赏着赞叹着。
“只是比较喜欢而已,没有专门练过,不靠体的。”
丛苇的脸一下子又红了。她的字虽然不靠体,但的确还算可以,学生们都戏称为“丛体”,好多学生还专门把她的讲义要了去,说是要练习她的字体呢。
“自成一体,不简单啊不简单!啊,您是蓝城大学的教授啊?怪不得能写这么一笔好字呢!”
张警官从表格上抬起头来,有些惊诧地盯着丛苇。仿佛蓝城大学的教授,就必须有一手好字一样。
丛苇有些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将填写完毕的表格交给张警官。
“我一直没看见林黄鹂,能告诉我,在哪里可以见到她吗?”
“没问题!”张警官的态度友好起来,他冲着旁边的一个女警察撮了个响指,“小王,麻烦你带丛教授去隔壁看看林黄鹂。”
“好嘞,张头儿。”
女警察调皮地一笑,露出两个好看的小酒窝。她收拾起面前的许多文件,起身向外走去。
丛苇感激地冲张警官点点头,又举起手轻轻摇晃两下,转身跟着那个女警察向外走去。
“呵呵,当教授的,就是跟一般家长不一样,人家的孩子,保准不会像这些小混混似的,有人养没人教,只能成为社会的包袱!”
背后传来张警官爽朗的声音。
听着张警官的赞叹,丛苇觉得五脏六腑像被什么揪扯着一样,猛地疼痛起来。托尔斯泰那句经典名言浮雕一般在她眼前闪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如若张警官知道她的婚姻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她的女儿澹澹,也许有一天会沦落到比林黄鹂更可怕的结局,又做何感想呢?他还会轻易地下这种结论吗?
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