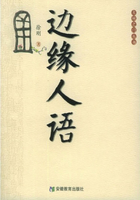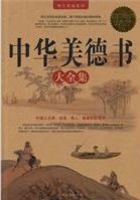朱向前是这种鉴赏审美式的批评的介导者和实践者。他特别推崇孙绍振的《文学创作论》,就因为“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切近创作,在理论和创作的森严壁垒之问戳了个大窟窿。”他由读法国法朗士的文学批评短论,而引发出一通“来一点鉴赏主义批评又何妨”的议论,认为我国文学批评的弊端乃在于:“国人着力译介、引进乃至模仿照搬的主要是西方的话言学、叙事学、阐释学、现象学、原型批评等形式批评和科学主义批评,而对主观鉴赏一派基本忽略不计。”他强调“批评家首先应该是一个鉴赏家”,对那些“缺少审美悟性和艺术感受力,更多的是靠批评‘方法’和理论‘框架’吃饭”的批评家很不以为然。
我对朱向前关于鉴赏审美式批评的介导和实践是亟表赞赏的,我也认为我们亟需提高和发展鉴赏审美式的批评。但我对朱向前关于科学主义批评的种种徽词,又不尽赞同。我宁愿对科学主义批评和鉴赏审美批评平分秋色,也不愿去贬抑其任何一方。原因已如上述:它们都是文学批评中的不可或缺的门类,谁也代替不了谁。在这方面,我基本上赞同前苏联美学家尤·鲍·鲍列夫的如下观点:“然而事实上,批评具有双重本质:从它的某些功能、特点和手段来看,它是文学;而从另一些功能、特点和手段来看,它又是科学。把批评与文学等同起来,否定批评中含有科学的(“理性的”)因素,会产生许多讼人因惑不解的问题。”不知向前以为然否?
三
现已可以断言,1993年是朱向前文学批评的又一个丰收年。这一年向前不仅发表了数量可观的批评文章,而且还投下了几枚颇具“杀伤力”的“重磅炸弹”——发表了凡篇颇有影响的重头文章。最重要的是两蔫;一篇是近四万字,写作时问前后迁延近一年的《新军旅作家“三剑客”》,一篇是一万二千余字的《我为什么反对“下海”》。这两篇文章中,朱向前对近年来困扰文坛的“下海”问题和军旅三位颇有实力的著名作家——莫言、周涛、朱苏进,发表了经过深思熟虑的认真研究的个人见解,旗帜鲜明,论证细密,见解独到,激情洋溢,文采斐然。可以说是朱向前近年来最有份量的两篇文章,从总体上显示了朱向前文学批评的实力和水平。
“下海”问题是商潮中困扰文坛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文人学士弃支从商或舍学就商者不过寥寥,但经过新闻媒体的鼓噪,“下海”一说却也被弄得沸沸扬扬,似乎全中国的文人学士都被商潮所裹挟了。事实却远非如此。我在今年夏天的一篇小文中曾说过,文人学士可不可或该不该“下海”,这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不值得大张其鼓地去讨论和鼓噪。古人早就说地:“学者所以饰百行也。”就是说读书人可以从事百行百业,这自然也包括经商。愿意和有能力经商的,就“下海”去;不愿意或没有能力经商的,兢依然以学业和文字为本。金钱固然是诱人的东西,但要文人学士完全放弃学业和文字的追求,而去追逛金钱,恐怕也是多数人所不能和不为的。我这里绝没有重文轻商的意思,我只是认为,社会有分工,从文和从商只是分工的不同,并无轻重贵贱之分。但倘若文人学士都去“下海”经商,那就是社会畴形的表现了,不值得提倡。以我个人来说,就不是经商的料,因此我绝没有弃文从商的妄想。——我的看法仅此而已。
然而向前却不然。在《我为什么反对“下海”》中,他高屋建瓴,首先从商品经济时代中国文人应当张扬自身的责任戎使命感出发,提出了历史和现实对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要求;“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地建构起一种富于当代意识和新的人文色彩的精神架构与文化体系,以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理论支撑的精神导引”,而“决不应去‘赶海’蹚浑水,推波助澜乃至混水摸鱼”。他又从文学的定位出发,认为文学虽然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商品,但它“首先是一种,心灵活动的记录,是精神追求的物化呈现。而商业效应则是它的副产品,是在它进入社会流通领域以后实现的,而此前在作家那里,它不应成为一个写作动机。以金钱的诱惑而不是以心灵的表达作为驱力的写作,按照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来看,也只能叫做‘异化写作’,一种‘心为物役’的写作。”向前对商品时代向文学提出的新的要求,商潮所引起的文坛的分化,以及商品经济对文学的发展所可能造成的正面影响,虽然缺少具体的分析,对一些文人“下海”也缺乏更冷静全面的评价,有些用词过于尖刻(如“为自己的彻底堕落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和恰如其时的机会”云云),但他以拳拳之心、殷殷之情对商海茫茫中的中国文坛发出了“我反对‘下海’”的断面,犹如空谷足音,一定会获得相当范围内的共鸣和回声的。
如果说《我为什么反对“下海”》是一篇充满着使命感责任感又不失学人见地的政论性文章的话,那么《新军旅作家“三剑客”》则是一篇有独出机抒的见解、冷静细密的分析,又飞扬着激情和文采的文学论文了。这篇文章发挥了向前历来切近作家本体和创作本体的优势,又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将鉴赏审美式的批评与对作家的传记批评和心理批评结合起来。其问既贯注着批评家的艺术直觉和主观感受,又不失细密的论证的科学的分析。就传记批评和心理批评来说,这篇论文显然还有不尽人意之处,还不是很周详,也许是有意隐匿避开了一些容易引起麻烦的东西,因此有不尽淋漓酣畅之感。奉来是一部书稿的框架击写成了一篇论文,自然有难以周详略嫌概略的问题,这是我们不应苛求的。尽管如此,读这篇论文仍然有如一阵清风拂面吹来,很新鲜,很明快,能够产生一种阅读的快感。一篇长篇论文能够产生这样的阅读效果,已然是难能可贵的了。
这是一篇完全个性化的研究成果,但又不是批评家的主观臆测妄断,它的每一个判断都建立在分析之上,而分析又都有根有据的,你可以不信服它,但却很难推倒它。最精采、最能体现批评家的个性化的研究见解的,我认为是下篇:“三剑客”现在行进中的困境与突围。作为一个批评家,最困难的不是表现在对研究对象的已获得成就的热情肯定上,而是表现在对他们的局限和困境的敏锐发现和切实分析上;在这方面,最容易引起作家的反感,尤其是对一个已经成名、自信而又富于抱负的作家来说。向前与莫言、周涛、朱苏进或是同学,或是朋友,或是同事,其关系可想而知。但他却不为亲者讳,根据个人的感受和研究,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些看法可以说是相当犀利和尖锐的,如对莫言。我不知识莫言在读到向前对他的批评时会是一种什么态度,如向前在文中说:“时至今日,当我试图对‘三剑客’作出一个阶段性‘总结’时,我再也不能保留我的看法了,我必须直率地说出我对近年莫言创作的批评意见:‘成也萧何,政也萧何’……成在以极端化的风格独标叛帜,败在在极端化的道路上过犹不及,因此,正处于创作状态巅峰的极地上和艺术风格的极限上颠复了自己,也迷失了自己,至今陷入一种失落了美学目标的躁动与徘徊之中。”当我读到这些批评的时候,一方面觉得痛快淋漓,一方面却又不无担心:会不会因此造成莫言的反感,甚至莫言与向前的反目呢?
朱向前以军旅文学批评起家,如今已越出军旅,而成为全国知名的年轻批评家了。在批评沉入低谷,批评队伍心态浮躁、心灵失衡的今天,向前却能理智地调整自身,以沉稳的姿态依然执着于批评的创造之中,为沟通理论与创作、文学与读者做了有益的工作,并获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这是令人欣喜的。向前的批评自然也有其弱点。五年前我们在太湖的对谈中曾涉及到这一问题。向前说自己“比较缺乏理论功底片”,“思维空间不够开展,参照系数比较局限,容易停留在印象和感情的层次上就事论事,难以把具体的作家作品置于更为宏阔和悠远的哲学、美学、历史的文化背学上进行考察,作出理论的升华与提炼”。虽然含有自谦的成份,说得重了一点,但也大体上符合实际。当时我提出了各个人都可以走自己的路,在发挥自己优势的同时,不断地克服自己的短处,力求将感悟鉴赏式的批评与科学的批评结合起来的问题。向前也表示同意。这五年来,向前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使他的批评有所提高和升华。但我想,这也应该是他较为长远的一个努力目标。
在当今一批富于实力和才智的批评家,包括束向前一辈的少壮批评家面前,我常有自叹弗如之感,但我还是不自量力,接受了向前的邀约革成此文,既表达我的欣喜之情,也寄托着我对向前的厚望,并亦借以抒发我的一些感慨!是为序。
1993、10、24写毕北京天命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