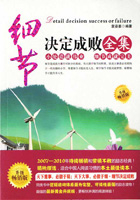血液里吹过定向的风
吹向山冈上那片成熟的寂寞
如果想要采摘晴朗的果实
那么,先品尝浓郁的苦涩
春寒是从哪里知道我来到珊瑚城的,这已经不需要考证了。
他在一路上又是转动怎样的心思找到彩虹姨妈的住处的,也已经没有考证的必要了。事实是:他终于站到了彩虹姨妈的门前,用他挥画笔的左手摁响了门铃。他是一个左撇子,不是遗传因素造成的,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人们说,这样的人聪明,经常运动左手能够强身益脑,对于达到思维的平衡有辅助的作用。这当然也不需要再加研究。事实是:正如彩虹姨妈所预料的,春寒像是接收到准确信号似的,准确无误地来到珊瑚城里这个唯一可供我休憩的地方。一个不希望别人来打扰的地方。一个需要安静再安静的地方。
这个无理的人,还是跨进门来。柔软的头发还是紧贴在耳根以下,白衬衣的袖子左右不对称地向上挽起,表情一派无辜。我的惊诧与厌烦适时地表露出来,我希望我能够表露出来。彩虹姨妈竟然一反常态地热情招呼他,像是他的到来为她的预测下了最好的注解。我感到好笑,原本来这里拜访彩虹姨妈的,应该是我的男朋友才对,而现如今出现这么一个文不对题的人,竟然在我的青春将灭时刻,公然又荒唐地亮相于我最尊重的亲人面前。
他为什么会拐进这条路上来?我为什么会在这条路上见到他?天知道。
我保持沉默,实在是因为不知道说什么,我们之间竟然也会有尴尬的局面产生,再次感到好笑。彩虹姨妈好像对他很有好感,他坐在那里,与彩虹姨妈一说一答的,很是融洽。他说呆会儿去找安顿下来的旅馆,姨妈告诉他边上有一家既便宜又干净的;姨妈问他会在这里呆多久?他说他请了一些日子的假,倒也不是很长;他向姨妈说自己的名字与职业,还说是我好朋友的朋友,当然也就是我的朋友,彩虹姨妈说她都知道了,也知道他会来。春寒惊讶地抬起头,注视着彩虹姨妈的眼睛,似乎在思量她是否在与他开玩笑,或者故意用这种方式使得他放下心来。彩虹姨妈慈祥地看着他,没有显示出可以捉住的破绽。
彩虹姨妈站起身来,说:“你们聊聊吧,我想去躺一会儿。”
我求救般地用眼神拉住她,她当做没看见,兀自进了卧室。
午后的光线跳跃着,像是乐器上的弦,拨弄一下就会发出声响。关键是看你拨哪一根弦,每一根弦发出的音色是不同的。桌上的野花,张阿姨总是经常更换,很少看到花朵腐烂的样子。我坐在较高的椅子上,春寒坐在较低的沙发上,我垂着眼看他,他仰起眼睛才能与我的眼光相连接。当然,我们只是各自垂着头,像是一对犯了错的孪生兄妹。他还是率先开了口,他与我一说话,我对他的抗拒就烟消云散了。我们毕竟在同一条船上,同一条船上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来这里,还是想找你谈谈。另外,我也想换一个环境,我也想离开那个熟悉得让人压抑的地方。”他说的话很实在。
“当时,我确实吓坏了,无法思想什么。现在,你来到这里,也许我们确实需要分析一下整件事情。”我说。
“我们,我们得给自己一个答案。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他说得很好,我赞同。
两个人像是签署了一份口头合同,甲方与乙方同意合作。甲方与乙方同时松了一口气,对于冤案的昭雪有了盼头。
甲方与乙方在第二天,就开始了工作。工作的地点既没有定在浪漫的海边,也没有选择安静的茶馆,而是找了一个还未有开发行动的荒芜的工地。这是一个空阔又偏僻的地方,破砖瓦与乱石子满地皆是,最靠边的角落里还有一间搭建的简易民工房,在那里坚守着阵地。如果夜空繁星密布的时候,民工房的主人可能也会做君临天下的梦,他也可以俨然是个大王似的在这个少有人问津的空旷土地上出没,他也可以傲视拥挤的楼群与喧嚣的人心。民工房主人的一条狗在乱瓦碎石间徘徊,偶尔低下脖子嗅嗅气味,它在寻找着线索,食物的线索,同伴的线索。
春寒蹲在石堆里,似乎这样弯曲着身体,更能蓄积分辨真相的能量。我找寻着一个可以下脚的地方,既不能离得他太远,又不能在一个无法固定的支点上摇摇晃晃,身体的不平衡会打乱我内心刚刚建筑起来的清晰平面。他给予我安定下来的时间。我终于站稳了脚跟。从远处看,我们就像是瓦砾中斜伸着的一棵柳树与一团仙人掌。柳树会与仙人掌说些什么?他们正在准备说什么?
我不想浪费时间,虽然我的空闲时间多得怕人。但我还是希望能够尽快地理清头绪,让那根细微的线绳尽早探头,以便于顺利地穿过等待中的某一个针孔。我向他开口,把昨晚想好的问题抛向他。
“我有三个问题要问你:一,你最后一次见海棠是在什么时候?二,海棠与你说了什么话?三,你又对海棠做了什么?”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场景里的三个问题,其实它也可算作一个连贯的长问题。这三个问题听在春寒的耳朵里,就是一个问题。一个渐次深入的问题。
他好像在回忆,好像在挣扎,好像在找可以首先出口的那句话。
他的声音像从地缝里钻出来,我使劲竖起耳朵,不想漏掉任何细节。
“我最后一次见到海棠,就是在她自杀的前一晚。那一天天气很闷热,这并不奇怪,桂花城的夏天总是闷热的。那一天的傍晚下了一场很大的雷阵雨,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约好是在晚饭后八点钟见面,为了那次见面,我省略了那顿晚餐。我下午开始就在房间里等她,心里从来没有这么不安静过,我对于她即将的到来,感到忧伤与落寞。”他叙述着,那一天好像就在他眼前。
我忍不住打断他:“你的心里为什么会不安静?还有你的忧伤,从何而起?你在害怕见到她吗?”我递进式的询问顺势而出,像一串鱼儿吐出的气泡,浮在水面。我的问句显得幼稚与激进。
他没有受到我的影响,继续着他的叙述,在大脑里存有的那盘录像带上按了继续播放。我似乎听见磁带转动时轻微的咔嚓声。
“我们将近有大半个月没有见过面了,也很少通电话。如果说这是一种僵持状态的话,我想是合适的。我不想去触动我们之间那根最敏感的线,那根线有时会很清晰,但大部分时间里,它有头无尾,抓不住主要的脉络。”他顿了顿,眼神看向前方的一个点,像是看到了什么。“她准时出现了。进来的时候,一脸的平静。我预感到她要与我说一些重要的话,是有关于我与她之间的。她说很热,径直走到我的那台老旧空调面前对着吹风,左手还拉起胸前的棉布衬衫来回扇动。我递给她饮料,她说不喝。然后就坐下来,轻笑了一下,说,很久没见了呢,没有想我吧?她半开着玩笑,有点拿我取乐的意思。我憋着气,感觉很不畅快,我想着是不是该由我来了结这个残局。最后,还是被她抢了先。她说完那句话,我们都像卸下了一个包袱,但又突然感到空荡荡的,好像彼此变成了陌生人。她说渴了,喝啤酒吧。我们默不作声地各自喝完了一罐纯生啤酒,她就挥挥手走了。”说到这里,他的痛苦开始狂烈地拍打他,他的身体不自觉地颤抖一下,他的眼圈抹上一层红晕,“现在想来,我很庆幸由她先说出那句话。”那句话是什么?他与她之间的,他好像不愿意说出。我不认为此刻我有权利逼供他,明显地,我感受到那不会是一句优美动听的话。
“她离开的时候,情绪还稳定吗?”我认为这样问话还是合适的。
“还算稳定。她挥手告别的样子,我永远都会记得。怎么说呢,既真诚又妩媚。是的,妩媚,这样的表情,我很少在她脸上看到。”他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