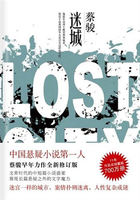小房间收拾停当以后,张阿姨帮我下了一碗面。当面端上来的时候,我知道我的胃确实是饿了。可我的意识一直在关注别的事,而且专心致志。我提起筷子,却没有吃的欲望。彩虹姨妈还是坐在沙发上,很关切地看着我。张阿姨卷起围裙,拢了拢头发,对我说:“你慢慢吃,我先回去了。明天我再过来。”我站起身送她到门口,还一个劲地与她说谢谢。她突然间握住我的手,有些哽咽,“你姨妈很可怜的,你来了,我也放心了。”我不知道说什么,有一团棉花类的东西迅速堵住了心口。她松开我的手,一面往前跨步,一面回望着我,嘴里念念有词,“真是像,真是像,简直是你姨妈的翻版。”
我关上门,走回去,在桌边重新坐下来。彩虹姨妈仍然陷在沙发里,如同陷在深潭里。一切终于安静下来,纷扰与喧嚣被关在了门外。蝉声虽然还在窗外嘶喊,倒像是另外世界的事情。彩虹姨妈与我,在这个小巢里,无声地坐着,温暖也罢,伤心也罢,只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感受。这让我定下心来。我开始吃那碗面,它已经坨了,我一口一口地吃,这么多天以来,它是我吃得最踏实的一顿饭,虽然还是没有恢复以前的好食欲,至少我不再与它对立,我已经卸下防备,顺从地接纳它了。安静,久违的安静。一束安静的目光。一份安静的安慰。
言语有时是可有可无的。在有些时间,有些状况里。
彩虹姨妈从深潭里挣扎着站起来,走到我的身边:“很高兴你能来,我知道你迟早会来的。”我看着她,她似乎看清了一切。她知道我会来,为什么而来,甚至比我自己还要明白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两个问题已经趴伏在我背上很多日子了,我反复地问自己,又反复地逃避。彩虹姨妈也许是一个占卜师,她的口气让我更加确信。希望她是,希望她是。她的理解力与判断力是超常的,我急需她的帮助。这个被我描摹的占卜师感觉到疲倦,与我道了晚安,进了卧房。失眠依然折磨着她,她睡觉的大部分时间只是思维活跃地躺着,闭上的眼睛还是能够看见想要看见的,甚至是不想要看见的也纷至沓来,而往往越不想看见的越是清晰地重复。这是我失眠的感悟,我知道彩虹姨妈也沉溺其中。
我独自坐在沙发里,坐在姨妈坐了很久的地方,很久是多久?
二小时?一天?三个月?十年?交替变化的无数人事中,留下什么是不变的?容颜褪去了光彩,形体失却了活力,意志在锤打中委顿,爱情在挣扎中消失。而蜜蜂还在嗡嗡地叫着,新的花朵还在绽放,道路增加了宽度与广度,有更多的方向可供选择。
我没有方向,我找不到方向。
困惑——层层叠叠。我陷在那个地方,如同每一个人,曾经陷入过一样。如同陷在泥潭里。神啊!请赐予我力量!让恐惧远离我,让我重新站起来。
瓶子里插着花。贝壳瓶子。野花。我才瞥见它,它在桌子的正中,花的颜色有好几种,白色的、紫色的、黄色的,零碎的绿叶子衬托着花朵,美丽又娇媚。还是倔强的。
清晨,我醒过来,听到窗外的雨声。我竟然没做恶梦,一觉睡到天明。这真是不可思议,真是难得!蜷曲的思想舒展开来,如同脸上平缓的阴影。我向床边的海螺与贝壳打招呼,它们洁净的脸一派单纯。红珊瑚如火如荼地倚在墙角,年月使它的鲜红沉淀得更加深沉,它的深沉是热烈的,也是含蓄的。我听着雨经过绿叶,经过窗棂,经过记忆的声音,直直地滴入无边的虚妄里。
外屋有声响。莫非是姨妈起来了?我跃下床,稍作整理,就跑出去,我想在早晨给彩虹姨妈一个拥抱。我就像一个快要溺水的人,突然面对拯救我的人,只想紧紧地抓住她,才感觉安全。有一个身影背对着我,张阿姨在晨光里摆弄早餐。她听见我的声音,并不回头,她不需要分辨就知道是谁起床了。
“你洗洗,来吃早饭。你姨妈是不吃早饭的,让她多睡一会。”我答应着,朝隔壁的关闭的房门看了一眼,那扇门很旧了,斑驳的油漆排列成有趣的图案,我是擅长此道的,我一边梳洗,一边给图案配上合适的名词,当然也不排除添加恰当的形容词。稀饭、咸鸭蛋、小碟子里的榨菜、还有油条,印象里完美的早餐。已经多久没有享用这样的早晨了?我在某一天丢失了它,现在也不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对待它,想到此,我的胃又一次抽痛,就是稀饭也无法下咽了。有些人的善解人意不是靠智慧,而是柔亮的天性所致。张阿姨是这样的人。她喜欢说话——在别人需要她说话的时候——带领着进入她的语境,而恰好忘记自己的纠缠。
“你姨妈刚发病的时候,吓死我了。我与你说说,真是要与你说说。那是几年前的事。有一天,她给我打电话,她说她要走了,再也不回来了,让我去见她最后一面。我吓坏了,她的口气完全不像开玩笑,再说她也不是会开玩笑的人。我停下手里的活,三步并作二步,冲到这里。就是这里,这个客厅。她站在窗前,窗子大开着,屋子里灌满了风。那是冬天,特别冷,海风能在脸上划出口子。
我走到她身边,她全身在哆嗦,头发很乱,像是好几天没梳了。我去拉她的手,冰凉冰凉的,她突然向我转过身来,定定地看着我,眼睛里的光啊,怎么说呢,好像带刺似的,能扎人。我有点害怕,摇着她的胳膊,问她发生了什么?她就哭了,一直哭,一直哭,然后自言自语:‘有人要害他,要害他,我不允许,他怎么不给我发电报呢?打电话也可以。他没有我的电话,他不认识我了,他说结束是好事。不行,我不允许。他不能走,不能走……他走了,你看,起风了,他跟着风在跑,他跑得多快,升上天空了。我也要去,为什么我不能去?有人要害他,有人要害我,真的。’她紧紧拉住我,让我相信她说的话。我一时缓不过神来,她却开始往窗台上爬,我明白了她的意图,就赶紧抱住她的腰,拼命地拽住她。别看她平时挺瘦弱的,可那一会儿,像一头蛮牛,力气大得惊人。我使出吃奶的力气,终于把她摁到了沙发上。她开始骂我,骂我是坏蛋,说我也要害她,害她不能死。然后,就不停地哭,不停地哭,我受不了了,也跟着哭起来。真是奇怪,好像受了她的感染,我也哭得不能停止了。”张阿姨沉浸在回忆里,眼眶又湿润了。
我禁不住地问她:“后来呢?”
“我带她去看医生,医生说她患了严重的忧郁症。开了很多药,说要有人照顾。”她的情绪稳定下来,这个好心的人,遵照姨妈的意愿,没有与我们联络,只是自愿承担了照顾彩虹姨妈的责任。
我很感激地看着张阿姨,她似乎轻松做着的事,实际上是多么繁复。友谊,看来还是有它结实的一面,这可能是爱情无法比拟的。我这时的心完全被彩虹姨妈的故事占据了,那可怕的一幕里,彩虹姨妈的神思走在哪座悬崖峭壁上,她自己难道已经无力摘下千年的灵芝,无力解脱了吗?于是,只能够漫无目的地乱飘,哪里都是地狱,哪里都是天堂。天堂与地狱混淆在一起。她没有了重量,没有了体积,如同一粒肉眼看不见的尘埃,飞旋舞蹈着,飘逸到不可知的地方。遥远的,一厢情愿的地方。修剪枝蔓重新编辑现实的地方。美丽滑翔的地方。冷酷埋藏的地方。刹那间禁闭的幽长的通道,纷乱的画面,打破的节奏,钥匙丢在无望里。
“那个他是谁?”我忍不住地发问。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姨妈是个古怪的人。听说原来有个很好的对象,可她并不喜欢他。后来,也有人陆续给她介绍过几回,她见一回,就向对方说一句话:我已经有了爱人。”张阿姨的困惑写在脸上,她摇着头,试图减弱它。
“可是,她没有爱人。”她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这句出口的话,有着她无法把控的神秘意味。神秘之花盛放开来,在我们面前。它无限度地扩展,扩展。
张阿姨继续与我说话,像是要把我们飞远的思维拉回到现实里,她告诉我她所经历的往事。
她的丈夫去世了,因为突如其来的一场病。她的女儿远嫁到别处,留下她一个人。她女儿是希望她跟着一起过的,可她与女婿合不来,又舍不得这个住惯了的城市,也舍不得住惯的家。尤其是那个家里有几十年来一直晃动在她面前的身影,这个身影,就算已经永远离去,对于她仍然是存在的。包括他的一些陋习,可恶又可恨的陋习,也陪伴了她那么多年,屡说不改,屡吵不改,现在想来,也变得亲切了。她叹了口气,上眼皮因为下垂,盖住了她三分之一的眼睛,面色还是少女般红润着,上面有几坨黄褐斑在渐亮的日光下加重了。
“绕了一圈,我也变成一个人。你姨妈也是。我们都是一样的,孤单对孤单。”
孤单对孤单。
我听见卧房里传来彩虹姨妈叫唤我的声音。在我分辨的几秒钟里,张阿姨已经在向我眨眼睛了,她说:“你姨妈在叫你呢,你的名字是灵香?真好听。”她摆摆手示意我快进去,我站起身,推开卧房的门。彩虹姨妈还躺在床上,她一个人躺在床上,那张床显得太大了。她用手揉着太阳穴,看来昨晚睡得并不好。她拍拍床,让我坐下来,关切地问我:“睡得好吗?”我告诉她很久没睡过这样的好觉了。她笑笑,传说中那双会说话的蓄满清泉的杏眼,如今并未干涸,反而由于增添了时光的痕迹而更加打动人心。
“我还是睡不好,没办法。”她说这句话时,显得无力。只有失眠的人才懂得什么是失眠。那就如同脑袋里扎了无数的小辫子,打开一条辫子,又长出一条新辫子,它们交缠在一起,越急于解开,缠绕得越紧。长期失眠的人,就算放弃了解辫子,可是由于长期的紧张,它们习惯性地交缠着,不需要触发,它们自己直挺挺地龇着。承受失眠的人,害怕夜晚的来临,也害怕白天的来临。夜晚的到来,意味着再次与失眠作艰苦的斗争;白天的到来,意味着又一次斗争的失败。治疗方法:心理与生理的双重调整。心理与生理的平衡一旦破坏,就像坐上了跷跷板,一起一伏的,很难快速回复到起始状态。就是重新恢复,也会因为不期而至的刺激,再度失去平衡。
“珊瑚城的夏天不热,夏天不热未必是好事。热烈的浓度是不同的,无法要求付出与得到的对等。有些是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只有忍受。这很不容易,因为真相隐藏得很深,恐惧的云朵会笼罩脆弱的心灵。灵香,我可怜的孩子,发生了什么?”彩虹姨妈用询问的目光打量着我,她的询问神情里有她自己意识不到的了解与明白。
“发生的事情,我宁愿忘记。”我轻声说着,“可是没有忘记的可能。”
彩虹姨妈不再说什么,她的思绪停顿在某个地方。似乎她被什么缠绊住,一时回不过神来。有一个红蝴蝶结系在一棵记忆之树上,任凭风吹雨打,任凭年月的腐蚀,它依旧鲜艳如初。这个恒久的蝴蝶结,因为痛苦,所以存在得更久,飞舞得更高。能够掌控它的那个人,永远骗不过自己。
如果失忆该多好!
“不好!我可怜的孩子。”彩虹姨妈竟然接上我心里默念的句子,我吓了一跳。她转正脸,认真地看着我说:
“火选择了炙烤我们的方位,我们只能接受它的熊熊燃烧。虽然最终只剩下灰烬,那也是属于我们的灰烬。”
彩虹姨妈的肯定语气是严肃的,甚至是坚定的。白天的太阳在夜晚不会出现,所有都遵循着自然的规律。我想:我是不需要刻意记忆与忘却的,记忆自行记忆,忘却自行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