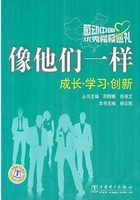对李逵,人们认为他身上有反抗的一面,不错,但他反抗的是赵官家,他想的是自己的哥哥去做皇帝,他所讲的是私义。他身上所谓的淳朴含有很大的奴性,他是最强烈地呐喊“哥哥做皇帝,教卢员外做丞相,我们都做大官,杀去东京(指北宋首都开封),夺了鸟位”的。
但革命成功后的李逵,是否还有强烈的造反性,那是值得怀疑的,我想他会乖乖伏地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他就会从对赵官家撕咬腾扑的宋江的功狗,变成一个对宋江大哥看家护院的狗,记得汉高祖论功行赏的时候,曾有功狗功人论:上(汉高祖)以何功最盛,先封为酂侯,食邑八千户。功臣皆曰:“臣等被坚执兵,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走得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
其实,李逵之类只能是功狗耳,恩格斯说:“狗认为它的主人是它的上帝,尽管这个主人可能是最大的无赖。”记得江青就曾放言:“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
在刘邦、朱元璋眼里,在黄巢、宋江眼里,狗始终是狗,再丰厚的赏赐与爱宠,不过视为奴才使唤。狗命好时得遇明主,或能凌烟阁上绘像留名,但十之八九都是遭遇狡兔死、走狗烹的无良主子,百般奴役凌辱之后,仍免不了当头一刀。
李逵的最后结局是这最好的注脚,宋江让他三更死,他就活不过四更天,所以宋江最后喝了毒酒快要死的时候,怕李逵在他死后造反,坏了名声,就捎带着把李逵也毒死,李逵毫无怨言,他临死前说:“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
从这点来说,宋江是赵官家的一条狗,是狗的队长和班头,李逵是这狗队里的一条健壮的功狗,但终究摆脱不了被宰的命运。
至死也不悟,这样的功狗命运悲也夫!
谁动了领导的奶酪——说插翅虎雷横
在坊间有顺口溜说在工作中有八大没眼色,也叫做八大不懂事,这是针对公务员阶层来说的:
领导敬酒你不喝,
领导小姐你先摸,
领导走路你坐车,
领导讲话你罗嗦,
领导私事你瞎说,
领导洗澡你先脱,
领导夹菜你转桌,
领导听牌你自摸。
官场上的小公务员总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否则就如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之死》写的那样,一个小公务员在剧院里看戏时打了个喷嚏,不慎将唾沫溅到了坐在前排的一位将军的秃头上。他惟恐将军会将此举视为自己的粗野冒犯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道歉,弄得那位将军哭笑不得,最后真的大发雷霆,而执著地申诉自己毫无冒犯之心实属清白无过的小公务员,在遭遇将军的不耐烦与呵斥后一命呜呼。
说郓城刑警队“黄金组合”的第二号人物,公务员插翅虎雷横,其人铁匠出身,但多有瑕疵。作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但这刀插的也不是多正,一是有自己的小九九,拿朋友的钱手软,再就是这刀插在政府的肋骨上,他不痛。晁盖被通缉后,雷横为什么抢着要去后门私放晁盖?还不是因为他在捉刘唐时收了晁盖的十两银子。为了这十两银子,雷横宁可与刘唐打五十多个回合,虽没头破血流,但一身臭汗是赚在了皮囊上,但就是不肯退还一毫一厘。作为都头,搞好郓城地界的治安,缉捕盗贼强人,是再也天经地义不过的了,但是正因为在大宋朝,谁也不把职业当回事,只要上面有蔡京、高俅,下面难免不出宋江、朱仝、雷横这样为晁盖通风报信者,即使像宋江杀了阎婆惜这样的命案,雷横们也敢上下其手,这些都头平时收点钱,听戏娱乐的时候摆谱不拿票,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但雷横这次却栽了,是枕边的风把他的腰和公务员的俸禄薪水一下子折断。插翅虎雷横从梁山回郓城以后,由李小二陪同到郓城县的剧院(勾栏)听首都东京行院的白秀英唱戏。进入勾栏,“便去青龙头上第一位坐了”。这天,白秀英唱的是《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这白秀英说了又唱,唱了又说,博得满座喝彩不绝。就在这节骨眼上,其父白玉乔停下板鼓要求女儿向听众收钱。雷横坐了头座,理所当然“先到雷横面前。雷横便去身边袋里摸时,不想并无一文”。这唱戏的白秀英主要是靠听众的赏钱生活的。雷横“坐当其位,可出个标首”,按说不但要给钱,而且要多出些银两。说自己忘带钱来,就有听白戏之嫌,这坐首座的不给钱,这后面的钱又怎么收?白秀英很没有面子。于是白秀英父女两个,你一言我一语地奚落雷横,不干不净的粗话也夹在其中。
白秀英是从东京来郓城捞银子的,她背靠着县长这棵大树乘凉。
一般郓城的各界都会给足面子的,想象比宋还久远的唐代,我们的老祖宗捧歌星,绝不让于今日追星族: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如果要知道白秀英是县长的二奶,想提拔的、托门子办事的,谁不借这个机会狠命地用银子砸。
我们刑警队长雷都头,坐在第一位却忘了带钱——在郓城地面上,我想都头是没有带碎银子习惯的。娱乐场合出现都头对场子来说是一种面子和抬举,但白秀英依仗自己抱着了大树,假如她说自己是县长的小姨子或者县长是自己的表哥,我想铁匠出身的雷横只要脑袋不长包自会明白,但都市的歌唱家都是惯出来的,作为走穴的大腕脾气也大,她根本没有把小小的刑警队长放在眼里。
当别人解围说忘带钱的爷是雷都头时,白秀英甩了一句“只怕是驴筋头”。驴筋头不是好话,把雷横比成了叫驴的生殖器官,这对在众人面前的雷横的伤害有多大可想而知,在郓城黑白两道跺一脚,地就晃动的雷横怎能受得了如此的羞辱,该出手时就出手,挥手一拳是自然的了。
下面的场景应该是《水浒传》中好汉们表演“孝”的经典镜头。白秀英这妮子也不是好惹的,在县令的身边一展哭闹和添油加醋的功夫,说些自己的身子只许大人动,别的人怎能动的话,自然县令的醋意、恨意顿生,于是县令就枷了雷横,而且枷在白秀英挂牌演出的勾栏前示众,这样示众丢人就丢人吧,白秀英还不依不饶,硬逼雷横的同事们将他摁在大街上捆作一团。正好雷横的母亲看见了,心疼得不得了,就边解绳子边和白秀英对骂。雷老太年纪虽大骂人却有一套,就单捡些乡土的东西,专拣痛处骂:“你这千人骑、万人压、乱人入的贱母狗。”白秀英敌不过乡土野骂,“大怒,抢向前,只一掌,把那婆婆打个踉跄。那婆婆却待挣扎,白秀英再赶入去,老大耳光子只顾打。”《水浒传》的好汉讲究的是孝义,看自己的母亲受辱被打,雷横“一时怒从心发,扯起枷来,望着白秀英脑盖上打将下去”。
金圣叹在点评此章节时,笔下动情,像一篇《陈情表》,每每读到此等文字,我就知道那些好汉在江湖立身的根本所在了。下面是老金的文字,节录存档:雷横母曰:“老身年纪六旬之上,眼睁睁地只看着这个孩儿!”
此一语,字字自说母之爱儿,却字字说出儿之事母。何也?夫人老至六十之际,大都百无一能,惟知仰食其子。子与之食,则得食;子不与之食,则不得食者也。
子与之衣服钱物,则可以至人之前;子不与之衣服钱物,则不敢以至人之前者也。其眼睁睁地只看孩儿,正如初生小儿眼睁睁地只看母乳,岂曰求报,亦其势则然矣。乃天下之老人,吾每见其垂首向壁,不来眼睁睁地看其孩儿者,无他,眼睁睁看一日,而不应,是其心悲可知也。明日又眼睁睁看一日,而又不应,是其心疑可知也。又明日又眼睁睁看一日,而终又不应,是其心夫而后永自决绝,誓于此生不复来看,何者?为其无益也!今雷横独令其母眼睁睁地无日不看,然则其日日之承伺颜色、奉接意思为何如哉!《陈情表》曰:“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雷横之母亦曰:“若是这个孩儿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悲哉!仁孝之声,请之如闻夜猿矣!
作为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太太,最疼爱自己的儿子,只有做妈的才会嘘寒问暖,知痛知痒。但雷老娘心疼儿子的同时居然也看出了郓城县的司法不公,当看到儿子在示众,老人家说:“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道理。”是啊,犯罪有政府处置,但县令与白秀英穿一条裤子,盖一床被子,白秀英就是政府的委派机构,但执法权放给了原告,这玩笑开得也实在太大了,暮年的母亲为儿挨打,只要心存良善的儿女决不会无动于衷。可恶的歌星打了雷老娘,这标准的孝子雷横怎能忍得下这鸟气,用枷打死了白秀英,送她到月亮之上牧马放羊,把地狱的热辣情歌给县令就唱到了天亮也无妨。
插翅虎,犹如成语如虎添翼,好像老虎长上了翅膀,出处是在三国诸葛亮《心书·兵机》:“将能执兵之权,操兵之势,而临群下,臂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
雷横,铁匠出身的他,白有个绰号插翅虎,他能飞到哪里?在权力的罗网下,有翅膀也白搭,因为他脑子不灵光,领导的奶酪动不得,如果他像李逵负荆,一下子拜到在白秀英的水红裙子下,说不定级别还能升半格,与朱仝平起平坐呢。
太岁头上的石榴花——说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
文革中评《水浒》,把阮氏三兄弟当成造反的核心,可依靠的力量,亲不亲,阶级分,连八百年前的打渔的都是我们一根藤上的瓜,是我们阶级的一奶同胞,就有评论说“阮氏三雄”的绰号都有鬼气,这是统治者污蔑底层劳动者,真是孰(叔)可忍,婶子不可忍,我在小学就亲眼看到农村的大娘、大婶两眼冒火,批判黑宋江兼金圣叹,但批判后,这些淳朴的女人们关注的是开批判会的工分。但就在那会上,我知道了太岁在底层劳动者神秘的位置。
民间有句俗语叫“太岁头上动土”,那是不吉利的举止。在中国民间,“太岁”向来被看作是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具有能在冥冥之中支配和影响人们命运的力量。古书云:“太岁如君,为众神之首,众煞之主,有如君临天下,不可冒犯。”由于“太岁”位高权重,古人对他都非常敬畏,惟恐触怒了它而于己不利,小则头疼发热,大则要了吃饭的家什。为避免得罪“太岁”神,在冲犯“太岁”之年必须在新年开春期间拜祭它,以祈求新的一年平安顺利、逢凶化吉。
史料有载,“太岁”是古人假定的一个天体,和岁星(木星)运动速度相同而方向相反。“太岁”到了哪个区域,就在相应的方位地下有一块肉状的东西,这就是“太岁”的化身,在这个方位动土就会惊动“太岁”。这就是“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俗语的神秘所在。
阮小二的绰号立地太岁,就是活在人间的怪物,谁要碰见,可是一件丧门而不值得庆贺的事。其实《水浒》里很多的人物绰号,都是凶神恶煞,就是去掉绰号,还原成本人,那一般的百姓见了也是毛骨悚然。
这些好汉虽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但打打杀杀的过程里,小老百姓也难免不皮肤受损心里受伤。
其实,阮小二的绰号原本并非立地太岁,在《宋江三十六人赞》中,阮小二的赞词是:“灌口少年,短命何益?曷不监之,清源庙食。”“灌口”是指四川灌县的都江堰,余秋雨曾有一副对联写“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这阮小二与都江堰离得山高路远又有什么关系呢?
传说李冰的二儿子名叫二郎,早年吃喝嫖赌。一次李冰命他治理岷江,当时正赶上洪水猛涨,堤坝上出现了一道决口,洪水势不可挡。
李冰便命令二郎用身体堵住决口,只见他跳入滔滔洪水,将洪水吸入自己身体之中。洪水退下,可二郎却以身殉职。李冰说:“二郎宜其短命。”意思是说他这样一个浪荡公子,能够死在治水当中,尽管短命,却是死得其所。“短命乎?永生乎!”二郎的物理生命虽然结束了,但他的灵魂却永远活在都江堰人民心中。于是当地的清源庙为二郎设了神位来纪念这位英雄,清源山也被百姓命名为“二郎山”。龚圣与用这个典故来赞美阮小二,这说明阮小二也先是浪子,后是金子。
阮小二的“短命二郎”的绰号怎么又跑到阮小五脑瓜子上?
清代曾庆笃在《水浒撷萃》另有解释,他认为这个绰号中“短命”的不是“二郎”自己,而是“二郎”专使别人“短命”。“短命二郎”就是能使别人丧命的杀人二郎、要命二郎,以此来形容阮小二的厉害和勇武。哥哥的绰号与弟弟的绰号对调,曾庆笃认为这是刻书人的失误。
“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明人刻书,往往粗制滥造,错讹百出,将阮小二的绰号安到了阮小五的头上。这和现代的盗版的张冠李戴如出一辙,是美丽的误读。
说到阮小五,最惹人注目的是他的出场,他虽是好赌的穷光蛋,但却讲究一个“酷”字。第一次与大家见面,阮小五斜戴着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披着一领旧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郁郁一个豹子来,形象像是现在的街舞少年。
阮小五应该说是个比较难写的人物,郓城有俗话“头生希罕,老生娇,最苦就是丫巴腰。”说的是孩子在家里,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受大人疼爱,中间的往往没戏,三兄弟,阮小五排在中间,没有阮小二的威风,也没有阮小七的伶俐,对他的描写也是最少的。吴用到石碣村劝说三阮入伙,阮小五的话最少,有一句最显示三阮的豪气:“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一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们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
“论秤分金银,一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
这话成为描写梁山好汉的经典,也是后代好汉的人生目标。
但我感到《水浒传》写男人有张力的地方,是用写女子的妩媚笔法写男子,用“一枝花”来写刽子手蔡庆,用柔韧的笔墨写鲁智深和林冲,真叫人感慨万端。而写阮小五偏偏头上插的是石榴花,花在女性头上出现没什么希奇,不是三条腿的蛤蟆。女子头簪时令鲜花的习俗在汉代就已出现。汉代以后,簪花之俗在妇女中历久不衰。
宋代是比较女性化的,男子簪戴鲜花的风俗在宋代成为一些典礼的礼仪,由皇帝给群臣赐花,由中使为之插戴。
虽然唐代的男人也有插花的,但范围有限。王维有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古代重阳节,人们要插戴茱萸避邪,插戴菊花祈求长寿。
然而在《水浒传》中,男子簪花则是另一番风味。阮小五出场“斜戴着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披着一领旧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郁郁的一个豹子来”。小霸王周通到刘太公庄上抢亲,“小喽罗头巾边乱插着野花。”病关索杨雄在蓟州做两院押狱,兼充市曹行刑刽子手,“有一首临江仙词,单道着杨雄好处:两臂雕青镌嫩玉,头巾环眼嵌玲珑。鬓边爱插翠芙蓉。背心书刽字,衫串染猩红。问事厅前逞手段,行刑刀利如风。微黄面色细眉浓。人称病关索,好汉是杨雄。”“人都羡英雄领袖”的浪子燕青“腰间斜插名人扇,鬓边常簪四季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