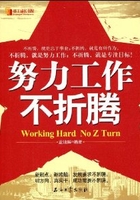我们爱武松,还有就是那骨子里的快意恩仇,我们都是俗人,学不会武松的那种洒脱,也许在武松身上,有我们的幻想,我们不敢也无法快意恩仇。在武松那里,没有像我们的斤斤计较,掂三掂四,前怕狼后怕虎,在武松那里,就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只管快意,不计其他,什么法律、伦理、道德,统统是抹布,丢在一边。
先说报仇,哥哥无辜被害死,作为在江湖行走的武松绝不会善罢甘休,于是痛下辣手诛杀潘金莲、西门庆。再说报恩,在武松被押往东平府申请发落之前,取了十二三两银子送给郓哥的老爹,因为此前他叫郓哥帮助打官司时,曾许下给郓哥十几两银子做本钱,但此时武松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在他投案前,曾委托四邻变卖家中一应物件(武大郎的炊饼炉子一类)作随衙用度之资,现在要上府城听候最终发落,更是处处需要用钱,在这种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武二郎还能不忘对一个小孩子的承诺,这点连宋江都做不到。
但武松的快意,有时像个没脑子的孩子,像是给一块糖吃,叫干啥就干啥,不问青红,何管皂白,肠子饱了,何问脑子。比如发配到孟州城安平寨,吃了施恩几顿酒肉,就去替他平了蒋门神,其实施恩父子也不算什么好鸟。武松只管眼前,不问是非,说明我们的武松二郎,还处在被蒙骗的阶段,如果蒋门神先厚待了武松,那武松的拳头就会砸向施恩。
《水浒传》里说施恩他爹乃孟州城监狱的管营,武松作为犯人初来乍到,因为没有“孝敬”,管营大人差点照常规赏给武松一顿“杀威棒”,好歹在旁边的儿子施恩另有谋算,才免却皮肉之苦。大宋的牢狱之黑不独孟州,江州也复如是,宋江刚见戴宗的时候,如不是递上话也差点挨揍。而施恩呢,也是孟州地面的坐地虎,在孟州的黄金地段开的快活林酒店,他向武松是如此介绍:“但有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他去趁食。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二三百两银子寻觅,如此赚钱。”说白了,就是黑道保护费。施恩靠的是他老子与自己“学得些小枪棒在手”,并且还有他老子管的八九十个拼命囚徒护场子,但“如此赚钱”的买卖却活生生被蒋门神夺了。这其实是黑吃黑,但武松全没有虑此,就被施恩父子的天天好酒好肉,几顶“大丈夫”、“义士”、“神人”的高帽,弄得迷迷糊糊,心甘情愿为施恩父子做牛马使。
而二郎武松在张都监几声“大丈夫”、“男子汉”、“英雄无敌”的哄骗下,知其要自己做亲随体己人时,也跪下称谢道:“小人是个牢城营内囚徒,若蒙恩相抬举,小人当以随鞭执镫,伏侍恩相。”武松是真心感激张都监的“抬举”的,张都监设下圈套,使人诈喊“有贼”时,武松立即做出反应:“都监相公如此爱我,他后堂内里有贼,我如何不去救护?”于是武松栽进圈套,我们为没有脑子的二郎一哭,但武松岂是随便侮辱和欺骗的?
于是武松一旦出手也就血腥四布:大闹飞云浦,一举诛杀两个公人、两个杀手,而后折返鸳鸯楼,杀马夫、杀丫鬟、杀张都监、杀张团练、杀蒋门神、杀亲随、杀张都监夫人、杀张都监儿女、杀张都监媳……月光里,烛影中,刀光霍霍,腰刀砍缺了口,再换朴刀,杀、杀、杀,走出中堂,拴了前门,折返回来,再寻着了——不是撞着了——两三个妇女,都搠死在房中。
在杀、杀、杀中,武松的杀戮美学体系建立了,金圣叹说:“武松者,天人也。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也。”
即使在最后,武松还天真地不忘为自己做广告,在白粉墙上用血写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这也是快意的表现,就像诗人登高必赋,这时如果不表现就心里痒痒。
但这种快意很少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心理的痉挛,有时我们也感到解气,这说明我们中《水浒》的毒也太深,到了不自觉的地步,金圣叹在批点血溅鸳鸯楼时,在旁一再批上“杀第一个”、“杀第二个”、“杀第三个”、“杀第七个”、“杀第八个”、“杀第十一、十二个”、“杀十三个、十四个、十五个”,通过这些批语,似乎可以看到他好像一直在得意洋洋地替武松掰着手指头数着,直到最后,在“武松道:‘我方才心满意足,走了罢休’”句中“我方心满意足”旁,又批上:“六字绝妙好辞!”
看到如此批语,有时静下来,我就倒抽一口冷气,我们的社会和民族的“戾气”,有着多么广泛的基础,这也许是鲁迅批评《水浒》和“水浒气”的根苗吧。
武松是个匆匆的赶路者,但行者的名号,出自孙二娘的杰作,第三十一回以前,与张青夫妻相会之前,他完全没有绰号。当时在外面混的人,哪怕是初级泼皮,谁没有个把绰号呢?武松少年时就吃酒惹事,横行街市,竟然没有。母夜叉孙二娘因考虑到武松投奔二龙山路上的安全,才建议:“叔叔既要逃难,只除非把头发剪了,做个行者”。于是替他打扮成戴发修行的行者模样,喝声彩,“果然好个行者”。
后来,武松真正成为一名“行者”,不愿随宋江进京受封,在杭州六合寺里出家,经历了繁华,也经历了荒凉,在路上什么样的景致没有见过?但武松没有留恋,最后真的回归了佛性,绰号成了真的身份,但依然是行者,走在正道的路上,一个伏虎的罗汉,是否能忘情于人间,我想世间如果有西门庆,如果哥哥还在受欺辱,武松还是不能忘情吧。
板斧砍向谁——说黑旋风李逵
在现在梁山山顶一处要道黑风口,矗有一尊雕塑,是李逵手执板斧,黑凛凛地戳在那里,让游人毛骨悚然。说不定什么时候,这黑家伙阴魂不死跳将下来,手起斧落,不是砍断腿,就是砍掉胳膊。掉胳膊掉腿这在现代社会还好说,医疗条件具备,接上缝上,伤筋动骨一百天就可,如果从脖子那里砍掉,把头颅当做足球,在高俅的足下滚来滚去,那却是麻烦。有个朋友说,李逵站在这里,替梁山守家护院,如狗耳。
我闻后,大喜。说白了,李逵就是宋江的家奴,或者说是宋江喂熟的一条狗,让咬谁就咬谁。宋江带着李逵去走李师师的后门,在东京拜会李师师时,宋江曾介绍李逵:“这是家生的孩儿小李。”“家生的孩儿”是最能深刻地表明李逵与宋江关系的,而这时李师师幽了一默立马接口说:“我倒不打紧,辱莫了太白学士。”三个姓李的并列,不知道李白是做何感想,不意李家还有如此儿郎,真乃家门不幸。
李逵的星号为天杀星,绰号黑旋风。他一出场,就是一个不良的社会分子,行凶杀人流落在外,如丧家狗被戴宗收留,当时宋江与戴宗在江州的酒楼上喝酒,李逵来了,戴宗向宋江介绍说:“这个是小弟身边牢里一个小牢子,姓李,名逵,祖贯是沂州沂水县百丈村人氏。本身一个异名,唤做黑旋风李逵。他乡中都叫他做李铁牛。因为打死了人,逃走出来,虽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曾还乡。为他酒性不好,人多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及会拳棍,现今在此牢里勾当。”
先前人们多以为其善良,我以为不可,李逵浑身散发的是流氓气、无赖气,多吃多沾,吃拿卡要,一句不合就来粗的。当宋江给了李逵十两银子,李逵拿了去赌,结果输了个精光就耍起无赖,硬要取回又引得一场打架。李逵为了报答宋江,去江边讨鱼,但他不是好好的要,而是大声喝道:“你们船上活鱼,把两尾与我。”渔民们告诉他,得等到渔牙主人来了才可以,但是李逵便自己去抢,结果胡七八搞,把他们的鱼全给放跑了,双方因此打起架来,这时张顺(即渔牙主人)赶来,两人又打起来。最后,李逵经不起激将,被张顺诱到水里喝了一肚子水。打完架以后,他们接着喝酒,这时卖唱的宋玉莲来卖唱,李逵因被搅了豪情,“李逵怒从心起,跳起身来,把两个指头去那女娘子额上一点,那女子大叫一声,蓦然倒地。”对一个小女子动粗,不是好汉作派,更有意思的是李逵还欺辱老人。《水浒传》第五十三回,李逵和戴宗在饭店里吃饭,李逵拍桌子把一个老人的面条打翻,老人揪住他说理,李逵就要打他,幸好被戴宗劝住,否则,说不定那老人又要被李逵打死。第六十七回,李逵想立功,暗中出走,路经韩伯龙的饭店,吃了饭不给钱,被韩伯龙揪住,李逵索性将他一斧砍了。
梁山郓城有句话评价不良分子、地痞流氓:“敲个寡妇门,挖个绝户坟,打个老头欺负个小孩,这不是真汉子。”但这些李逵大都具备,有一二缺项,也和被杨志一刀劈死的牛二差不多。其实李逵身上还有无赖气,当戴宗批评教育他因为抢鱼而跟别人打架,李逵却说:“你怕我连累你,我自打死了一个,我自去承当。”这好像是豪言壮语,男子汉敢作敢当,但细细分析这句话是靠不住的,是谎言。当年在家乡打死了人,为何又要撒丫子逃跑?《水浒传》第五十二回,李逵为柴进事打死殷天锡,李逵说:“我便走了,须连累你。”柴进告诉他自己有办法,于是李逵也就顺水推舟,打死人有主家扛着,孩子哭了给他娘,一推六二五,让别人替自己擦腚。
李逵的杀戮,只由性子,李逵为救宋江在江州劫法场,书中写道:“只见他第一个出力,杀人最多。”晁盖喊他他也不听,“那汉哪里肯应,火杂杂地抡着大斧,只顾砍人”,“当下去十字街口,不问官军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推倒倾翻的,不计其数”。后来,晁盖阻止李逵滥杀百姓,可是,“那汉(即李逵)那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也许,你说周围多的是无聊的看客,但这些人也到不了罪不可赎的地步,这里多的是无辜百姓,李逵却是嗜血成性,如狗儿见了骨头。
在梁山好汉第三次打祝家庄时,李逵的斧子更是派上了用场。后来李逵到宋江面前请功:“祝龙是兄弟杀了,祝彪也是兄弟砍了,扈成那厮走了,扈太公一家,都杀得干干净净,兄弟特来请功。”他又说:“我砍得手顺,望扈家庄赶去……他家庄上,被我杀得一个也没了。”宋江嫌恶他杀戮过分,问他抓了几个活的,李逵说:“谁鸟耐烦,见着活的便砍了。”宋江因此抹去了他的功劳,可是,“黑旋风笑道:‘虽然没了功劳,也吃我杀得快活。’”杀人只是杀人,不问青红皂白,不问功劳苦劳就一味杀,连宋朝的花朵也不放过,而且李逵杀人的变态心理令人吃惊。
他杀四岁儿童是从孩子的头劈成两半;杀了李鬼后,割他腿肉下饭;捉奸时将两个人杀死,砍做十来段;宋江捉了黄文炳,要将他凌迟处死,是李逵自告奋勇动的手,书中写道:“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黄文炳笑道:‘你这厮在蔡九知府后堂,且会说黄道黑,拨置害人,无中生有撺掇他。今日你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慢死。爷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捡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
鲁迅说在史书里歪歪斜斜看到的是吃人,李逵们的所作所为正是游民里暴民的天性,对生命全无怜悯,杀得快乐,杀出了游戏性。但有时这些举动连宋江也看不过,就喊李逵为“黑禽兽”。要说李逵的没心没肺莫如他力杀四虎后,当时母亲刚被老虎吃掉,李逵在荒山野岭的大哭却也撼动我们的心,但后来就在众人的簇拥下,喝得酩酊大醉,这又让我们感到老娘不如一杯酒,李逵是怎么快乐怎么来,不管是杀人还是喝酒。
人们常说李逵天真烂漫,我觉得这是施耐庵用漫画和反讽的笔法,为我们这个世界塑造一个乐子,里面不乏戏弄的成分。如第七十四回寿张县坐衙、闯学堂诸事,充满喜剧色彩,但李卓吾所说就有点过,也许这和他王学左派不要束缚,鼓吹的“童心说”相近:“李大哥做知县,闹学堂,都是逢场作戏,真个神通自在,未至不迎,既去不恋,活佛!活佛!”书中写到:李逵起身,把绿袍抓扎起,槐简揣在腰里,掣出大斧,直看著枷了那个原告人,号令在县门前,方才大踏步去了,也不脱那衣靴。县门前看的百姓,那里忍得住笑。正在寿张县前走过东,走过西,忽听得一处学堂读书之声,李逵揭起帘子,走将入去,吓得那先生跳窗走了,众学生们哭的哭,叫的叫,跑的跑,躲的躲,李逵大笑。
但我们读到此处,心里是如何嘀咕?怕没有一个愿意在神圣安宁的教室看到李逵这厮肆意张狂吧。其实李逵的天真是在损害别人,无论生命还是财产,他没有理性,不拿脑子思考,只是从快乐出发。他在寿张县做县令,李逵让人扮成打官司的,然后自己来断案,他是怎么断案的呢?他说:“这个打了人的是好汉,先放了他去。这个不长进的,怎地吃人打了?与我枷号在衙门前示众!”这里有什么公理可言,一切从李老爷的好恶出发,这样的县令不要最好。李逵在四柳村捉鬼时,发现主人的女儿与人偷情,便将两人都杀死,致使主人悲恸欲绝,李逵居然还要人家谢他!如此颠倒世界,如此的连做人的基本道德都不遵循的人,对人间来说是恶魔。孔子说:“勇而无礼则乱。”李逵这样的孔武是非常不可爱的,鲁迅是厌恶李逵的一员,在《掖集外集业序》中说道:“我却又憎恶张翼德型不问青红皂白、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中去,淹得他两眼翻白。”
李逵在这个世界上,只认宋江,这点也是鲁迅说得对,终究是奴才。
李逵对宋江的驯顺、忠心与依赖正可看作狗与主子的关系。宋江是枭雄,他看李逵可造就,就舍得在李逵身上投资,既花银子,也花时间和感情。李逵初见宋江,宋江又是送银子,又是带李逵喝酒,对他那卤莽的行事一味微笑着任从。你说需要银子还债,便给你银子还债,你说小盏吃酒不过瘾,便吩咐酒保专给你换大碗,看你吃鱼吃不饱,又专为你要了两斤肉,临别还送了五十两一锭大银。宋江这样的感情投资就如驯熟一条狗,养狗还要骨头,还要耐心,等养熟了,那狗就忠心在骨。宋江因题反诗入狱,戴宗因受知府差遣进京需离开一段时日,李逵怕贪酒误了宋江饭食便“真个不吃酒,早晚只在牢里伏侍,寸步不离”,这样的形态与忠实的狗子何其相似。狗是主人的宠物,主人对狗难免也产生感情,宋江说:“他与我身上情分最重”,而狗呢,主人是有生杀大权的,于是李逵说“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吧。”
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宋江带数人元夜上东京时,曾对李师师戏称李逵是“家生的孩儿小李”,难道这种戏称可移用到武松、鲁智深身上乎?李逵在宋江眼里不是家奴不是狗子又是什么?
李逵绰号黑旋风,文革中有文章妙解:“李逵,叫黑旋风。风,有好坏之分。旋风,从来就被封建统治者视为邪风、恶风、鬼风,李逵最敢造反,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爷,对地主阶级有如凌厉的旋风。再加上一个“黑”字,就成了要‘撼地天爷的恶煞风了。因此,作者便把他的造反精神诬蔑为野性不改,惹事生非,莽撞、愚蠢,极尽了诋毁、丑化之能事。”风在这里也有了阶级性。
黑,在中国人心里的本意并没有贬义。黑包公、黑钟馗,他们都是正义的化身,在时装界,黑是高贵;在丧礼上,黑是敬重。其实李逵黑旋风绰号里的“旋风”是一种火炮。李逵面黑如铁,性烈如火,“黑旋风”名副其实,有如现代人的绰号“大炮筒子”直来直去,当然黑旋风也可理解为龙卷风,风来是昏天黑地,樯倾楫摧,一片瓦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