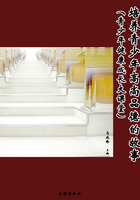在我的印象里,熊是一种很笨的动物,我们平常骂人,你怎么笨得像狗熊!事实上,熊的智商不比其他哺乳类动物低。这头母熊知道把小熊崽拴在木桩上是个引诱它上钩的圈套,也知道狗是站在人一边的,是它的敌人,如果它会应用成语的话,肯定会说狗和人是一丘之貉。它还知道它一旦走进没有树丛可以隐藏的开阔地,可怕的猎枪就会朝它射击,可出于一种母爱本能,它又必须穿过开阔地给小熊崽喂奶,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把小熊崽救出囹圄。它是被逼急了,灵机一动,想出个抱着大黑狗走进开阔地来的绝招。
母熊大白掌很快走到木桩跟前,小熊崽呜噜呜噜发出亲昵的叫声,朝母熊的怀里钻来。木桩四周无遮无拦,月光如昼,离我们埋伏的石窝仅有二十来米远,一举一动都躲不过我们的眼睛。大黑狗还在挣扎,狗嘴咬不到,就用爪子在母熊身上拼命撕扯,但犬科动物的爪子比起猫科动物来,要逊色得多,既不够长,也不够锋利,熊皮厚韧,熊平时又喜欢在树干上蹭痒,遍体涂着一层树脂,狗爪抓上去,等于一把老头乐在搔痒。母熊大白掌大概急着要喂奶,把大黑狗塞到自己的屁股底下,像坐板凳似的坐着;然后,它把小熊崽搂进怀里,小熊崽咂巴着母熊的奶头,吃得又香又甜;大黑狗在母熊的屁股底下哀哀叫着。
狗熊遇敌有三招:一是用熊掌掴,二是用大嘴咬,三是用屁股碾。三招中,数屁股碾最厉害,熊身体重如磐石,熊屁股大如磨盘,包括人在内的中等兽类,一旦不幸被熊坐到屁股底下,就像一把不结实的板凳,哗啦就会散了骨架,再被熊屁股像石磨似的一碾,便会碾成块薄薄的肉饼。
大黑狗虽然被闷在母熊大白掌的屁股底下,却还在叫唤,显然,母熊还舍不得它死,没用力往下坐。
大黑狗的叫声,搅得亢浪隆心烦意乱,几次举枪欲射,都害怕误伤自己宠爱的猎狗,叹一口气又把枪放下了。
过了一会儿,母熊大白掌喂完了奶,重新像抱婴儿似的把大黑狗抱进怀里,腾出那只白色的右掌,去扯小熊崽脖子上的细铁链,哗啦哗啦,铁链抖动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响亮。熊虽然力大无穷,但要拉断铁链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扯了几下,没能扯断;又改用牙咬,铁链可不像松脆的炒豆那么容易嚼烂,咯嘣咯嘣,听得出来,它咬得很起劲,说不定牙齿也崩碎几颗了,还是没能把铁链咬断。倒是小熊崽脖子被细铁链勒疼了,呵吭呵吭咳嗽起来。
母熊大白掌在木桩前呆呆地坐了几分钟,突然抱着大黑狗走过去,先用那只大白掌推了推木桩,然后用身体猛烈冲撞树桩,咚咚咚,声音恐怖得就像在撞地狱的门。木桩虽然埋得很深,但小石山下的土质有点松软,木桩毕竟不是树桩,没有根扎在土里,被母熊大白掌庞大的身体连撞了几下,就开始松动,像醉汉似的歪过来歪过去;它又用那只大白掌搂着碗口粗的木桩,像拔萝卜似的要把木桩从土里拔出来。
假如再不设法制止的话,母熊大白掌很快就会如愿以偿,把木桩推倒拔起,然后把木桩连同小熊崽和大黑狗一起带进树林。
亢浪隆忍无可忍,举起枪来扣动了扳机。一团橘红色的火焰划破夜空,蹿向木桩。正在拔木桩的母熊大白掌像当胸被一只巨手推了一把,搂在怀里的大黑狗掉落下来,踉踉跄跄后退了好几步,一屁股坐在地上。它艰难地翻转身来,发出可怕的怒吼声,离开木桩,朝树林退去。
亢浪隆急急忙忙装好火药铁砂,想再次朝母熊大白掌射击,但来不及了,母熊大白掌已穿过开阔地,隐没在黑黢黢的树林里。
我和亢浪隆跃出石窝,奔到木桩下一看,大黑狗身体被铁砂马蜂窝似的钻了十几个洞,倒在血泊里,已经咽气了。小熊崽离得远,没受什么伤。再看地上,有一块块颜色很深的斑点,一直向树林延伸,用手一摸,湿漉漉黏糊糊的,凑到鼻子前一看,颜色很红,哦,是熊血。看来,母熊大白掌受的伤也不轻,亢浪隆的那支猎枪虽然老式,杀伤力却很大,要不是大黑狗替它挡住了大部分铁砂,它此刻一定是躺在木桩前动弹不了了。
亢浪隆小心翼翼地从地上抱起大黑狗,轻轻地捋平它背上凌乱的狗毛,用颤抖的声音说:“今天不把那只大白掌砍下来,我就不是人!”我看见他在说这句话时,眼睛里泛着一层晶莹。一个猎人,失去了一条好猎狗,当然是很伤心的,再说又是被挟制着用自己的猎枪误杀了自己的猎狗,除了伤心之外,更添了一层愤慨。
“等到天亮,我们可以顺着血迹去找大白掌。”我说。
“林子这么密,没有狗带路,你怎么找呀?它要是过一条河,你就是浑身长满眼睛也看不到血迹了!”亢浪隆断然否决了我的提议,“我要把它再叫回来。”
“它受了伤,吃了亏,怕不会再来了。”
“我亢浪隆打了那么多年的猎,我有办法叫它回来的。”他说着,取出我们随身带着的一只小塑料桶,到旁边一条涓涓小溪里接了半盆水,又取出我们准备野炊用的一坨盐巴,用石头捣碎了,撒进盆里,用一根小树枝不停地搅拌。
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像被装进了闷葫芦,站着发呆。
“你是来跟我一起打猎的,不是来看热闹的。”
“我……我不知道该干啥。”
“来,拿着。”亢浪隆解下腰上的皮带塞在我手里,“给我往小熊崽身上抽!”
“这……你这是要干吗呀?”
“让它哭,让它叫,让它嚎,把母熊引出来。”
我机械地举起皮带,往小熊崽身上抽去。小熊崽哇哇乱叫,绕着木桩躲避,但铁链子的长度有限,绕了两三圈,便被固定在木桩上不能动弹了。我一皮带抽过去,它竟用两条前肢抱着头,靠在木桩上,咿咿呜呜发抖。那副模样,极像一个被冤枉的孩子在遭受后娘的毒打。我实在有点不忍心再打下去,可又不敢违背亢浪隆的意志,便将皮带慢举轻抽,并尽量往小熊崽的屁股上打,敷衍亢浪隆。
“你是在给它拍灰还是在给它搔痒?”亢浪隆将调好的盐水搁在一旁,一把夺过我手中的皮带,劈头盖脸朝小熊崽抽过去,如狂风暴雨,如霹雳闪电,直抽得小熊崽喊爹哭娘,发出尖厉的嚎叫。
不一会儿,小熊崽身上便遍体鳞伤,鲜血淋漓。
亢浪隆收起皮带,扎在腰上,端起那盆盐水,像过泼水节似的,一抖手腕,哗的一声,一股脑儿泼到小熊崽身上。就像冷水滴进沸腾的油锅,小熊崽立刻爆响起撕心裂肺的长嚎。
我上下牙齿咯咯咯开始打仗,浑身打哆嗦。不难想象,还在滴血的伤口被盐水一浇是什么滋味,我觉得用万箭钻心火烧火燎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这种残忍的刑罚比起坐老虎凳、灌辣椒水、钉竹签子和搔脚底板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小熊崽凄厉的长嚎划破夜空,在寂静的山野传得很远很远。那恐怖的哀嚎声把附近一棵古榕上一树的乌鸦都惊醒了,在夜空乱飞乱撞,有好几只在摸黑飞行中被树枝割断了翅膀,垂直跌落下来。
“快,我们回石窝去,大白掌很快就会出现的。”亢浪隆一手提枪一手拉着我跑回石窝。
我卧在冰凉的石窝里,颤抖得更厉害。
“又不是打你的娃儿,你心疼个屁!”亢浪隆显然是发现我身体在抖,就用讥诮的口吻说。
“我……我觉得它那么小,这……这实在有点太过分了。”
“你是说我很残酷,对吗?”
“……”
“大白掌把我的大黑狗弄死了,就不残酷了吗?”
是你先放狗咬伤并捉住了小熊崽,是你把小熊崽拴在木桩上试图让母熊大白掌钻进你的圈套,是你朝母熊大白掌开枪误杀了阿黑,是你挑起了事端,是你制造了血案,你还好意思说母熊大白掌残酷?!
当然,这番话我只是在心里说说而已,我是人,我不能站在动物的立场上说话,好像也不应该用对待人的平等态度来对待动物。亢浪隆的话虽然违背事物的发展逻辑,但大家都习惯了这样的事实:人有权随心所欲地猎杀动物,而动物是不能用同样的手段来报复人的,不然的话,动物就是残酷,就犯了死罪。
“打猎嘛,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亢浪隆见我保持沉默,便用委婉的口气继续说,“你拿着刀拿着枪,不就是要杀戮要见血吗?我看你长着一副婆娘心肠,你不该来学打猎的。”
“我……我……我觉得小熊崽还太小,再说……再说母熊大白掌未必会上当。”
“它会来的。”亢浪隆说得异常肯定,“好比有个娃儿快死了,拍加急电报给阿妈,阿妈会不来吗?”
小熊崽一声比一声嚎得凶嚎得急嚎得凄惨,那叫声钻进母熊大白掌的耳朵,确实就像收到了爱子垂危的加急电报。它只要还有一口气,它就一定会来的,我想,亢浪隆不愧是位狩猎的高手,熟识母性的弱点。
我睁大眼睛,注意观察开阔地外树林里的动静。
左等右等,月亮沉下山峰,启明星升起来了,母熊大白掌还没出现。
小熊崽的嗓子叫哑了,但哀嚎声仍绵绵不绝。
天边出现了一抹玫瑰色的朝霞,金色的阳光从树冠漏下来,驱散了残夜。
“母熊大白掌肯定已经死了,害我们白等了一夜。”亢浪隆懊恼地说。
我想也是,不然的话,这里不可能那么太平。
我在小小的石窝待了大半夜,四肢发麻,脖颈酸疼,眼睛发涩,难受极了,便翻爬起来,跳出石窝,到开阔地活动活动身体。
亢浪隆长时间躺卧着也不舒服了,把猎枪搁在石窝里,跑向小溪,想掬把清凉凉的山泉水洗个脸。
小熊崽仍然用嘶哑的嗓子高一声低一声叫唤着。
晨鸟啁啾,雾岚缥缈,景色怡人。
我们刚刚离开石窝,突然,“——”山谷爆响起一声低沉的熊吼。这叫声一听就知道不是平面扩散开来的,也就是说不是从开阔地外的树林里传来的,而是自上而下传播开来的,也就是说从天空罩落下来的。我和亢浪隆赶紧抬头去看,只见一个黑色的物体已从小石山顶上坠落下来,像只巨大的黑色的怪鸟,在向大地俯冲。一眨眼的工夫,黑色的物体就准准地落在我们躺卧了整整一夜的石窝里,轰的一声巨响,我感觉到大地都微微颤抖了。
躺在我们石窝里的是母熊大白掌!
它的下半截身体已被砸得稀烂,血肉横飞,岩壁和四周的地上,都溅满了碎肉和污血。它砸落在石窝的一瞬间就气绝身亡了,但那只圆圆的脑袋和那张尖尖的嘴还完好无损,两只褐黄色的眼珠还瞪得贼圆,凝望着石窝下绑在木桩上的小熊崽,一副死不瞑目的神态。它的那只粗壮的右前肢,大约是肱骨折断了,从背后往上翘起,那只十分罕见的白爪子,掌面向上摊开,像是在向苍天乞讨着什么;(不会是在向苍天乞讨生命的公正吧?)有正常人两倍大的那只白熊掌中间,凸隆起一只紫色的肉垫,像握着一只用血蒸出来的馒头。
它生了一只奇异的白熊掌,那只白熊掌却要了它的命。
亢浪隆脸上像刷了一层石灰似的发白,头上沁出一层豆大的冷汗,呆呆地站在石窝边,望着母熊大白掌,嘴唇翕动着,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也背脊冷飕飕的,头皮发麻,手心冒汗。
我搁在石窝里的长刀,亢浪隆的猎枪,还有我们的背囊,全被母熊大白掌砸得粉碎。好险哪,只要再迟几秒钟离开石窝,亢浪隆和我就被从天而降的母熊大白掌压成肉饼了。
“它……它怎么可能爬到山顶上去?”亢浪隆搔着后脑勺,困惑地说。
我抬头望望一百多米高的小石山顶,也有同感。小石山孤零零地耸立在平地上,不可能绕道上去;狗熊不长翅膀,也不可能飞上去;狗熊虽说是爬树的高手,但小石山山势如此陡峭,连岩羊都望而生畏,它又负着伤,怎么可能上得去呢?
我和亢浪隆绕到小石山背后,青灰色的岩壁上,从山脚到山顶,涂着一条血痕,宽约两尺,在阳光的照耀下,就像一条红绸带,披挂在岩壁上。特别陡峭的地方,血迹也特别浓,特别大,仿佛是长长的红绸带中间打了几个漂亮的花结。
恍然间,我仿佛看到了这样一组镜头:
——小熊崽遭到鞭笞的声音,小熊崽身上的伤口被盐水泼湿后发出的凄厉的哀嚎声,传到了母熊大白掌的耳朵里,好似一把尖刀在剜它的心;
——它晓得,它若从树林跑进无遮无拦的开阔地,立刻就会成为猎枪的活靶子,不但救不了小熊崽,自己也会白白送掉性命;
——它是母亲,它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囚禁遭毒打受残害而无动于衷,它急得在树林里团团转,寻找可以解救自己宝贝的途径;
——它绕到小石山的背后,那儿的山坡虽然也十分险峻,但不是笔直的悬崖,要是在平时,它想都不敢想要从这么陡的山坡爬上去,但现在,除了这条险象环生的路,它找不到第二条可以向万恶的猎人报仇并救出小熊崽的路来;
——只要有一线希望能救出小熊崽,哪怕是刀山火海,它也要闯一闯;
——它用尖利的熊爪抠住粗糙的岩石,一点一点往上爬,胸部和腹部的伤口本来已凝结了,这样一运动,血痂重新被撕开,渗出殷殷血水,染红了它爬过的石头和野草;
——爬到半山腰,一段两丈高的山坡突然找不到斜面了,陡得连山鹰都无法在上面栖息,是名副其实的绝壁,它连爬几次,都无可奈何地滑落到原来位置;它已精疲力竭,差不多要绝望了;
——它一停下来,小熊崽撕心裂肺的嚎叫声就像针一样扎进它的心,像火一样炙烤它的灵魂,它的心坎里又蓬蓬勃勃燃起复仇的火焰,身上平添了一股力量;
——它又失败了几次,伤口流出来的血一遍一遍涂抹在绝壁上,血泡醒了山神,连绝壁也受了感动,终于,让它越过了险关;
——它的血流得太多,它爬得比蜗牛还慢,它咬紧牙关,一寸一寸地向山顶攀登;
——太阳从青翠的山峰背后伸出头来,太阳用自己的光和热孕育了这个世界,太阳在制造生命的过程中最得意的杰作就是用两足直立行走的人,但此时此刻,太阳为自己的杰作——人而羞红了脸;
——母熊大白掌的血快流尽了,力气也快耗尽了,终于,它创造了奇迹,登上了山顶;
——它在陡峭的山坡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血痕,这是一条用生命开辟出来的辉煌的血路;
——它站在山顶上,望见悬崖下自己的小宝贝浑身是血,流血的伤口上又结了一层白白的盐霜,哀嚎声时断时续,已奄奄一息了;它还看见有两个野蛮的猎人正卧在悬崖底下的石窝里,那支会喷火闪电的猎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开阔地外的树林;
——它跨到悬崖边缘,用最后一点力气站直起来,金色的阳光洒在它身上,黑色的体毛上像披了件金斗篷,小石山温柔地托举着它,白色的山岚温柔地缠绕着它,像是在为它缠绵地送行,晨鸟的鸣叫,仿佛是在为它轻轻吟唱一曲断肠的挽歌;
——它像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一样,留恋自己的生命,它不愿意死,它多么想能继续活下去,把可爱的小熊崽抚养长大;
——就在这时,悬崖下的两个猎人从石窝里站了起来;
——它照准底下的石窝,跳了下去,在身体腾空的一瞬间,它发出一声悲愤的吼叫……
我久久凝望着挂在岩壁上犹如红绸带似的长长的血痕,思绪万端,感情十分复杂,既钦佩母性的坚毅勇敢,又庆幸自己能死里逃生。要是我们晚几秒钟离开石窝,我肯定已经死了,而且死得不干不净。
打猎,真是一项用生命做赌注充满血腥味的世界上最残忍的游戏。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上山打过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