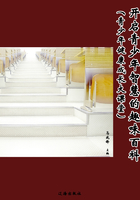老猎人亢浪隆在山林里闯荡了几十年,和飞禽走兽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经验丰富,枪法又准,再加上他养的那条大黑狗机灵凶猛,所以只要进得山去,极少有空手回来的时候。当地猎人有个习惯,凡打了飞禽,就拔下一根最鲜亮的羽毛,粘在枪把上;凡猎到走兽,就剁下头颅风干后挂在墙壁上。他的那支老式火药枪上密密麻麻粘满了各种色彩的羽毛,活像一只怪鸟;他竹楼的四面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野兽的脑袋,好像在开兽头博览会。
亢浪隆长着一张国字型的脸,浓眉大眼,微微上翘的下巴衬托着一只挺拔的鼻子,显得刚毅剽悍,气宇轩昂。但人不可貌相,这家伙虽然长得威武,心眼和他高大的身体却形成强烈反差,气量小得让人无法忍受,是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除了寨子里组织的集体狩猎外,他从不肯带人一起进山打猎,因为按照当地的习俗,只要是一起出去打猎的,无论是谁发现和打死了猎物,见者有份,他生怕别人占了他的便宜。
可这天黄昏,亢浪隆却肩着五彩缤纷怪鸟似的火药枪,牵着他的大黑狗,带着我这个猎场上的新兵,涉过湍急的流沙河,走进了密不透风的原始森林。
他是被我逼得没办法才带我一起去打猎的。
一个小时前,我和亢浪隆泡在流沙河的浅水湾里洗澡。当地的风俗,男的在上游洗,女的在下游洗,相隔约二十多米。恰好有几个姑娘也在河里洗澡,皮肤白得耀眼,嘻嘻哈哈的笑声直往我耳朵里灌。我的眼睛无法老实,但害怕亢浪隆笑话我,只好朝姑娘们瞥一眼,立刻又把眼光跳开,跳到对岸的香蕉林,装着在观赏风景的样子。
突然,我看见青翠的香蕉树丛里钻出一个黑糊糊的大家伙来,粗壮的身体,直立的姿势,乍一看,像个黑皮肤的相扑运动员,我赶紧用手背抹去挂在眼睫毛上的水珠,这回看仔细了,圆得像大南瓜似的脑袋,尖尖的嘴吻,一双小眼珠子,哦,是头狗熊!这时,从大狗熊的背后又吱溜钻出一只毛茸茸的小狗熊来,只有半米来高,蹒跚着朝河边走去,大概是口渴了,想喝水呢。大母熊急忙伸出右爪,做了个类似招手的姿势,小熊崽马上回到母熊身边。母熊立刻将几片宽大的香蕉叶拉扯下来,遮住它和小熊的身体,我便什么也看不见了。显然,母熊发现有人在对岸洗澡,退回到密林里去了。可我已经看见它了,更重要的是,我看见母熊伸出来的那只右爪和身上其他地方的毛色截然不同,是白色的,十分醒目。
熊掌本来就是名贵的山珍,在熊的四只爪掌里,又是右掌最值钱;熊习惯用右掌掏蜂蜜采蘑菇掘竹笋,还习惯用黏糊糊的唾液舔右掌,右掌等于长期浸泡在营养液里,肉垫厚实,肥嘟嘟的像握着一只大馒头。在所有的熊掌里,又数白掌最为珍奇,被视为稀世珍宝。当地猎人中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黑狗熊,白右掌,金子落在鼻梁上。一百只狗熊里,也找不出一只白右掌来,物以稀为贵,所以显得特别金贵,一只白右掌可以换两头三岁牙口的牯子牛。
我很兴奋,我想,和我一起洗澡的亢浪隆也一定看见母熊大白掌了,他是个老猎人,比我更懂得白右掌的价值,肯定像看见路上有只大钱包似的满脸喜色。可我偏过脸一看,出乎我的意料,亢浪隆脸平静得没有任何波澜,微闭着眼,哼哼唧唧,好像洗澡洗得挺忘情的。我不是傻瓜,我立刻明白这个老家伙肚子里在打小九九,以为我没发现母熊大白掌,不动声色,瞒天过海,想甩开我,独吞那只大白掌。果然,他连肥皂也忘了擦,泡了几分钟后,就上岸穿衣服了。
我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我微笑着来了一句:“我也看见白的东西了,别忘了见者有份哦。”
“姑娘的大腿很白,”他揶揄道,“我也不要见者有份了,让你独自看个饱吧。”
“那白的东西,不是大腿,是右前掌。”
“你的眼睛像蚂蟥一样叮在姑娘身上,一座山掉在你面前,怕你也看不见。”
“那好,我告诉村长去,让他赶快派人到对岸去搜索。”
亢浪隆用狐疑的眼光在我脸上审视了半晌,见我腰杆挺得像槟榔树一样直,不像说谎的样子,只好无奈地叹了口气说:“算你运气,跟我回家拿枪去吧。记住,白右掌归我,黑左掌归你,其余的平分。你连枪都不会打,已经够便宜你了。”
虽说是个不平等条约,但总比一点好处也捞不到要强;我是个刚从上海到云南来插队落户的知青,一个最蹩脚的猎人,既没有猎狗,也没有猎枪,只有一把长刀,若让我单独进山,别说猎熊,恐怕连只麻雀也打不到的。没办法,我只好屈服于亢浪隆的强权霸道。
我们一到对岸的香蕉林,就看见湿软的泥地里嵌着两行大脚印,有脚趾也有脚掌,极像人的脚印,当然要比人的脚印大得多,穿鞋的话,大概要穿六十码的特大号鞋。有脚印指引,又有大黑狗带路,我们很快在山脚下追到母熊大白掌和那只小熊崽。
大黑狗吠叫着,闪电般追了上去。母熊大白掌沿着一条被泥石流冲出来的山沟向山丫逃去,很明显,是想翻过山丫逃进密不透风的大黑山热带雨林去。母熊大白掌和人差不多高,胖得像只柏油桶,怕有一吨重了,但爬起山来却异常灵巧;小熊崽年幼力弱,稍陡一点的地段,就爬不上去,叫着,母熊大白掌只得回转身来,站在上面叼住小熊崽的后脖颈,像起重机一样把小熊崽提上去。这当然严重影响了它们的奔逃速度。几分钟后,大黑狗就叼住了小熊崽的一条后腿,小熊崽喊爹哭娘地叫起来。母熊大白掌吼叫着,转身来救小熊崽,撩起那只大白掌,就朝大黑狗掴去。别说猎狗了,就是孟加拉虎,被狗熊用力掴一掌,掴在嘴上,就会变成歪嘴虎,掴在脖子上,就会变成歪脖子虎;假如大黑狗被母熊大白掌掴着,亢浪隆就准备吃清炖狗肉吧。
亢浪隆不愧是个经验丰富的老猎人,立刻端起枪来,朝母熊大白掌开了一枪。他是在奔跑途中突然停下来开枪的,气喘心跳,很难打准;再说这种老式火药枪灌的是铁砂,学名叫霰弹,也就是说从枪管里射出去的不是一颗子弹,而是一群子弹,呈锥形朝猎物罩过去的;母熊大白掌和大黑狗一上一下离得很近,他也怕误伤了自己的大黑狗,所以枪口抬高了几寸。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一团灼热的火焰飞出去。我看见,母熊大白掌像被一把无形的理发剪快速理了个发,头顶竖直的毛刷的一下没有了,仿佛是理了半个奇形怪状的光头,露出烧焦的毛茬和发青的头皮,可能还有一两粒小铁砂钻进了它的耳朵,流出两条红丝线般的血。
母熊被巨响声震住了,愣了愣,那只极厉害的大白掌停在半空,没能按原计划掴下去。大黑狗趁机用力一扯,把小熊崽从山坡上拉下十几米来。
母熊大白掌低沉地吼叫着,望望坡下被大黑狗缠住的小熊崽,又望望还差几米就可到达的山丫,犹豫着,踯躇着,看得出来,它心里矛盾极了,想从坡上冲下来救小熊崽,又怕会闪电喷火的猎枪再次朝它射击,非但救不出小熊崽,还会把自己的性命也搭进去。
其实,这时候母熊大白掌要是不顾一切地冲下坡来,不但能救出小熊崽,还能把亢浪隆和我吓得屁滚尿流。亢浪隆用的是每次只能打一枪的单筒猎枪,且不是使用那种现存的子弹,而是往枪管里装填火药,还必须填一层火药盖一层铁砂,要重叠好几层,才有威力;火药装在葫芦里,挂在后腰带上,铁砂放在麂皮小口袋里,挂在前腰带上,装填一次火药工序繁杂,要一长套组合动作,最快也要三五分钟。这点时间,足够大白掌掴断大黑狗的脊梁,救出小熊崽,然后领着小熊崽翻过山丫扬长而去了。
亢浪隆一面手忙脚乱地往枪管里塞火药铅巴,一面啊嗬啊嗬伸直脖子叫嚷。他叫得很用力,脖子上青筋爆胀,像爬着好几条大蚯蚓。
我第一次经历如此怪异的狩猎场面,看得目瞪口呆。亢浪隆抽了我一个脖儿拐,骂道:“发酒瘟的,你是根木头呀?别傻站着了,快,用力跳,用力叫!”
我惊醒过来,也顾不得姿势是丑是美,拔出明晃晃的猎刀,高举双手,像蛤蟆似的一个劲蹦跶,啊啊叫起来。亢浪隆又在我屁股上赏了一脚:“发情的蚂蚱都比你跳得高,叫春的猫都比你叫得响,你是三天没吃饭了还是怎么着?”我只好由蛤蟆变成袋鼠,张牙舞爪,鬼哭狼嚎起来。这有点像动物与动物在对决前向对方炫耀自己的威武,一种纯粹的恐吓战术。别说,还真灵呢,母熊大白掌胆怯地望望我,一转身往坡上窜去,很快就翻过山丫,消失在一片葱绿的树林里。
我们生擒了小熊崽,用一根细铁链拴住脖子,牵着走。小家伙出生才两三个月,还没断奶,小鼻子小眼睛小耳朵,像只玩具熊,蛮可爱的。它一条后腿被狗牙咬破了,但伤得并不厉害。它很害怕,人一走近,便浑身觳觫,缩成一团。我掘了一支竹笋喂它,它也不吃,一个劲地呦呦呜咽,大概是在叫唤它的妈妈吧。
“可惜,让母熊大白掌跑掉了。”我说,“今天怕是逮不着它了。”
“你懂个屁,小熊崽在我们手里,就等于捏住了母熊大白掌的半条性命。唔,我教你怎么才能猎到母熊大白掌。”
亢浪隆带着我来到一座陡峭的小山前,围着小山踏勘了一圈,很满意地咂咂嘴说:“这地方不错,嘿,母熊大白掌逃不脱喽。”
这是一座高约一百多米的孤零零的小石山,四面都是半风化的花岗岩,山上没有树,石缝间偶尔长着一两丛荆棘。与四周郁郁葱葱连绵起伏的大山相比,这座小石山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孤儿。山势极陡,有一面是垂直的绝壁,其余三面也都是七十五度以上的陡坡,别说人了,就是善于在悬崖峭壁上攀缘的岩羊,也休想爬得上去。小石山四周约一百米范围里,几乎没有树,只有一些低矮的灌木和荒草。
亢浪隆走到绝壁下,站定了,吩咐我把前面的几丛灌木和荒草都砍倒,这样,从绝壁到树林间便形成了百米长的开阔地。然后,亢浪隆砍了一棵碗口粗的小树,削去枝桠,在绝壁前栽了一棵结实的木桩,把小熊崽用铁链子拴牢在木桩上。
这时,太阳落下山峰,暮霭沉沉,归鸟在林中聒噪,天快黑下来了。亢浪隆在绝壁下找了个石窝,在石窝里垫了一层树叶,让我和他一起躺在石窝里,把灌满火药和铁砂的猎枪搁在石头上。
我不得不佩服亢浪隆善于利用地形,这是狙击猎物最理想的位置,居高临下,视界开阔,无论母熊大白掌从左中右哪一侧出现,都逃不脱黑森森的枪口。更重要的是,我们背靠着陡峭的小石山,不用担心大白掌会绕到背后来袭击我们,而前面那片百米长的开阔地,也保证我们能及时发现任何动静,再说,还有大黑狗在开阔地里会随时为我们报警呢。
天还没有黑透,银盘似的月亮就挂上了树梢,能见度很高,别说一头大狗熊了,即使一只松鼠跳到开阔地来,我们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我想,这片开阔地就是母熊大白掌的葬身之地,当然,首先得有个前提,就是母熊大白掌要进入这片开阔地。它真能来吗?它要不来的话,我们就成了守株待兔的傻瓜了。我忍不住说了一句:“母熊大白掌说不定早逃远了呢。”
“不会的。”亢浪隆说得十分肯定,“吃奶的幼崽,好比一根剪不断的绳索,拴着母兽的心,你把幼崽带到天涯海角,母兽都会跟到天涯海角的。”
“这里有猎狗看守,还有人和猎枪,它敢靠近吗?”
“刀山火海,龙潭虎穴,它都会来闯一闯的。”
果然被亢浪隆言中了,当月亮升到半空时,开阔地外的树林里传来母熊大白掌的吼叫声,大黑狗在开阔地和树林的边缘线狂吠不已,小熊崽呦呦呼应着,想回到妈妈身边去,把铁链子拉得哗哗响。
“小熊崽饿了,在向母熊讨奶吃,母熊大白掌很快就会出现的。”亢浪隆端起枪来,压低声音对我说。
树林里闪过一个黑影,一晃,又不见了。大黑狗一会儿从开阔地的东端跑到西端,一会儿又从西端跑到东端,凶猛地叫着,很明显,母熊大白掌焦急地在树林里徘徊,寻找可以安全接近小熊崽的路线。
机敏的大黑狗,把母熊大白掌的行踪和企图及时通报给我们了。
大黑狗在开阔地和树林的交接地带跑了几个来回后,突然停在西端的两棵合欢树前,吠叫声向纵深延伸,跃跃欲扑,似乎想冲进树林去。亢浪隆顾不得会暴露自己的狙击位置,从石窝里站起来,高声叫道:“大黑,回来!大黑,快回来!”
平时,大黑狗最听亢浪隆的话,只要亢浪隆一叫,立刻会摇着尾巴跑到亢浪隆身边来,但这一次,不知怎么搞的,它听到叫声后,只是回头朝我们望了一眼,汪汪汪,送来一串圆润的吠叫声,似乎在对我们说,主人,等我把这头愚蠢的狗熊收拾掉,我再回到你身边来领赏!
大黑狗倏地蹿进树丛里。
“糟糕,大黑狗完了!”亢浪隆跺着脚说。
他的话音刚落,树林里狗的吠叫声戛然而止,随即响起玻璃划黑板似的非常难听的尖嚎声,我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尖嚎声由远而近,突然,树丛里钻出个高高大大的黑影,直立着向绝壁下的小熊崽走去。毫无疑问,是母熊大白掌。亢浪隆举起了枪,还没瞄准,就又把枪放下了。我们听见,狗的尖嚎声似乎跟着母熊大白掌在移动;再仔细一看,母熊大白掌两只前爪合拢,怀里有一条东西在挣扎;等母熊大白掌再走近几步,我们终于看清楚了,被母熊大白掌抱在怀里的就是亢浪隆的宝贝大黑狗,熊爪大概掐住了它的脖子,使它的吠叫声变得尖细凄厉。
我没看到母熊大白掌是怎么捉住大黑狗的,一般来说,狗比熊灵巧得多,是不大可能会被熊捉住的。也许,母熊大白掌用装死的办法引诱大黑狗来到身边,出其不意地一掌把大黑狗打翻在地;也许,母熊大白掌假装爬树逃跑,等大黑狗追到树下仰头吠咬时,它突然松手从树上扑下来,像网一样罩住了大黑狗。
母熊大白掌把大黑狗搂在怀里,就像穿了一件质量很高的防弹衣,又像是押了个“人质”,不,准确地说应该是“狗质”,迫使亢浪隆不敢开枪。一条好猎狗价钱昂贵,再说,从小养大的猎狗和主人之间还有很难割舍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