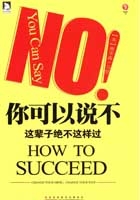大地震瞬间发生之时,北川民政局局长蒋洪生正走在从县政府去民政局的路上。他是下午一点钟走进县长谭大年的办公室,汇报近一个时期的民政工作。谭县长抬腕看看手表,对他说:“洪生啊,下午我有个经济会议,只能给你20分钟,咱们长话短说。”蒋洪生就简明扼要地汇报了21分钟,最后直截了当向县长要钱,谭县长沉吟了一会儿,拍拍他的肩膀说:“你这家伙,狮子大开口啊,我得考虑考虑再答复你。”蒋洪生说:“好的,县长,我静候您的佳音。”两点二十分,蒋洪生坐着他的北京现代车出了县委大院回民政局。车子刚刚驶出不远,忽然感觉地面轻轻晃动了两下。司机小庞惊恐地喊了句:“地震了,局长!”蒋洪生将脑袋仰靠在靠背上,出口长气,说道:“天要下雨地要小震,由他去吧。”他没有在意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两年小震时有发生,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场极为惨烈的大震正悄悄向北川人民逼近着。
就在蒋洪生闭上两眼想思考下一步工作的时候,大地突然疯狂地摇晃起来了,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大手在一起用力,发出可怕的隆隆巨响。汽车在此时成了玩具,被一只无形的大手任意摆弄着,一会儿偏向路边,一会儿拨弄回路中央,再一会儿推搡着往回退去。
蒋洪生瑟瑟发抖,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糟了”,大地震来了。
东倒西歪的楼房乌烟瘴气,大股大股的烟尘冲天而起,奔涌着,回旋着,搅成乱七八糟的一团。太阳被包裹了,化成无数大大小小的太阳,一闪一跳,一明一暗。粉尘将天空分成两大色块,太阳被粉尘包裹了。粉尘缓缓落下,北川的废墟缓缓拉开了白色的天幕,它在告诉人们,这是白天,灾难过后的白天,虽然到处一片黑暗,睁眼闭眼都是个黑。粉尘落下的刹那间,破碎的北川县城呈现出清晰的轮廓,太阳也变得血红。
“停车,快躲到安全地方去。”蒋洪生高声叫喊道。小庞还未及刹住车,就和蒋洪生一起被甩出了车子滚到了地上。蒋洪生这才发觉天地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四周围烟尘弥漫,他趴在地上足足有两三分钟不能动弹。天地死一般沉寂,突然,哭喊声、求救声响成了一片,凄厉而混杂。此时,蒋洪生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害怕和紧张,好像失去了意识。他定了定神,想站起来,腿已经软得站不起来了。在他的附近,还有十几个被震倒在地的人,大家互相搀扶着站起来。每个人都是灰头土脸的,彼此只看得到眼睛眨动。环顾四周,许多建筑瞬间变成了一堆堆废墟,北川县中心医院大楼全部垮塌,地方税务局大楼被平推出一段后倾覆了,路口也被巨石封堵得严严实实。
震后前10分钟,一片寂静,死静死静。
尘土飞扬,尘土在太阳中变幻着颜色。除了灰尘飞旋的声音外,整个北川县城还沉浸在苏醒前格外的寂静之中。大白天的,北川城似乎一下子沉入睡梦中了。
蒋洪生看着一片废墟,双腿一软,几乎跪在地上。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麻木地愣了片刻,根本无法理解周围的一切。他嘶喊了一声:“老天爷,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过了一会儿,呼喊声杂乱地响起了。他艰难地爬起来,远远望去,废墟充斥了整个视野,昔日那些熟悉的楼房商厦全都消失了,电线杆、交通指示牌、树木……要么七扭八歪,要么折断倒地,到处是散落的砖石瓦块。接下来他的第二个反应是到自己的单位民政局看一看,但前面的道路已被堵死。他只好顺着原路退回县政府大楼,这里的建筑也已倒塌,他拼命地喊叫着:“有活着的没有啊?谭县长——赵书记——”喊得嗓子出了血。不多时,废墟里响起回声:“哎,洪生,我在这儿——”是谭县长在喊。蒋洪生寻声跑了过去,只见谭县长蓬头土脸地站在一堆瓦砾中,半截身子还卡在废墟里动弹不得。蒋洪生蹲在谭县长跟前,仔细察看他身上的伤口。谭县长擦了把额头上的血水,说道:“放心,我死不了,快把我扒出去,组织救灾。”这时候,又跑过来两个机关公务员,蒋洪生和他们奋力将谭县长解救出来。谭县长朝四下乱喊乱跑的人们大声喊道:“大家不要慌,快救人!”他对蒋洪生等人下了一道命令:“想方设法把县委县政府的牌匾找到,快!”蒋洪生明白了谭县长这道指示的意义,大声说道:“县长放心,我一定找到牌匾。”他先确定了一下县委大门口的位置,然后冲进废墟寻找起来。他使劲地刨啊刨,身后堆起了一堆堆砖石瓦块,忽然,他的手似乎触到了什么,扒开砖瓦一看,果然是县委牌匾,他兴奋地叫喊起来,使劲把牌匾拔了出来,扛在肩上跑到谭县长跟前。“县长,牌匾找到了,找到了……”他沙哑的嗓子一声连一声呼喊,一扭头,发现谭县长已经泪流满面。
谭县长哽咽着说道:“赵书记他……他遇难了……”蒋洪生顿时落泪了,赵书记是一位多好的兄长啊,他从邻县桃花县调来还不到一年,可就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布了北川县的山川大地,他访贫问苦与人民群众心连心,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笑逐颜开。就是这样一位深受人民爱戴的好书记,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夺去了宝贵的生命,蒋洪生能不痛心疾首吗?谭县长能不痛哭流涕吗?
谭县长向赵书记的遗体深深鞠了三个躬,抹了一把泪水,走到一个高处,面向干部群众声嘶力竭地大声吼道:“同志们,政府办公大楼垮了,可政府还在,政府就在这里哪!大家都过来,我们部署救灾啊!”人们听到了谭县长铿锵有力的呐喊,仿佛听见了集合的号令,身体里感觉有了一股子力量在升腾,纷纷向谭县长聚拢过来。谭县长抚摩着县政府的牌子,大声喊道:“我宣布,北川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就地成立了!”然后开始布置救援工作,蒋洪生被分工负责医疗救援。北川县委县政府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了工作。
蒋洪生的脑子重新转起来了,他知道自己需要马上去医院组织救援。可当他赶到县中心医院的时候,这个拥有百年历史、一千余个床位的医院已经不复存在,他的任务变成了从废墟里救人。北川县城地处两山之间,大地震引发山体大面积滑坡,许多人被巨石砸中或身亡或受伤,到处可见废墟,到处可闻哀号,其境况惨不忍睹。蒋洪生机械地奔跑着,一边组织临时聚集的干部们救人,一边弓着腰,挥动着两条胳膊奋力地寻找着废墟底下的生命。到天擦黑时分,他一个人就从废墟里刨出了10条生命。
此时的蒋洪生有些筋疲力尽了,但他顾不上歇息,继续指挥抢险战斗。一名干部跑来报告说北川小学垮了,压住很多学生。他一听急了,大手一挥喊了声:“跟我来!”率队朝小学校那边跑去。路过电力公司宿舍楼时,他突然心里一阵悲怆:糟了!16岁的儿子不就因病休学住在这里吗?而出现在他眼前的,是夷为平地的一片废墟。听见呼救声,他顾不上是不是自己的孩子,离谁近就救谁。在北川小学,蒋洪生又救出了两个孩子。
由于余震不断,北川县政府开始安排受灾群众向平坦开阔的地带转移,大部分群众被疏散到北川中学一带,小部分群众被疏散到县政府大院。此前,蒋洪生曾越过像山一样的废墟寻找民政局。然而,民政局大楼已葬身于滚石之下,大楼上的土石厚度高达10多米。事后他知道,局里的三个副局长全部遇难。天黑了下来,蒋洪生抓紧时间奔跑呼号,招呼受灾群众向北川中学转移。在奔跑中,他的左腿不知被什么剐伤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
震后第一夜伴着凄风冷雨降临了。
北川中学门口的街上,聚集了三四千名受灾群众,他们是在绝境中获得重生的人,懂得如何逃生,如何自救互救,如何相互扶持。因为衣服被压在了废墟下,他们只能蜷缩在露天里或屋檐下,任雨水打落在身上,冻得瑟瑟发抖。没有水,没有电,只有寒冷和饥饿,而较强的余震大概10多分钟就有一次,人们惶惶不可终日。不少妇女和孩子惊吓过度,有的像傻了一样呆坐着,有的不停地来回乱走动。蒋洪生急忙去了县政府,千方百计找来两台汽油发电机,几个灯泡开始闪动微弱的光芒,惶恐不安的人们顿时感觉有了一丝暖意。有人问蒋洪生:“能不能找点儿吃的和被子啊,局长?”蒋洪生发愁了,房倒屋塌,黑灯瞎火,余震不断,上哪儿找被子和吃的啊!可眼看着群众遭了灾受了难,作为一名党的干部,岂能袖手旁观,被苦难吓倒呢?于是,他操起大喇叭,亮起大嗓门儿喊叫道:“各家各户注意啦,我是县民政局的蒋洪生,哪家房没倒的,能不能给遭灾的伤员拿点儿棉衣棉被啊?我代表县委县政府谢谢大家啦!”一些居民开始响应,冒险回家拿出棉衣棉被和食品。一时间,寒夜中又多了一丝温暖。一有什么事儿,大家就四处喊“蒋局长”,蒋洪生成了受灾群众的主心骨。得到人民群众的如此信赖,蒋洪生心里热乎乎暖融融的,有什么比群众信任更叫人舒心的呢?他忙得忘记喝水吃东西,忘记了自己的亲人的安危与否,忘记了自己流血的伤腿。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4时,终于有了个空闲,他一屁股坐在了泥水里,浑身像散了架子一样。他只穿了一件浅蓝色的T恤衫,冷得全身颤抖。偏偏老天不开眼,下起了雨,细细密密的雨丝泼洒个不停,人猫在临时搭起的窝棚里,还是觉得冷。总算得以歇息一下的蒋洪生此刻想起了他的贤惠能干的老婆,想起了他那可爱活泼的儿子,想起了局里的22名与他同舟共济的同事,身子打了个激灵站了起来,伤腿一阵钻心的疼,迫使他又坐在了地上。他喃喃自语道:“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是受伤了,还是已经不在人世了……”蒋洪生顽强地站立起来,拖着伤腿赶到民政局所在地。漆黑的雨夜里,蒋洪生和他的同事们聚到了一起。民政局共有21名干部,仅10人幸存。这一刻,在这个互相依靠的集体中,蒋洪生是中心,是温暖的依靠。大地震后的5天时间里,蒋洪生总共就睡了7个小时。群众每次见到他,他的眼圈都是红的,有人夸他是北川的英雄。“我不是什么‘英雄’,县上的每个干部都一样。”蒋洪生说着,又忙别的事去了。他来不及回头,来不及震惊,来不及感动,来不及落泪,一切都是为了救援。
早晨还是来临了,这是震后的第一个早晨。山头射出一道暖光,呼应着从噩梦中醒来的黎明。黎明的呼唤对于废墟里的人来说并不重要,可是,黎明对活下来的人尤为重要。它告诉人们,不管发生什么,日子还要继续。
蒋洪生真的很忙,事情也很杂,每天都要统计救灾物资的发放情况,并及时上报缺少什么。对捐赠单位的接洽工作,也由他牵头负责。他伤感地说:“晚上没事儿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局里的那些老哥,他们要是还活着,怎么也能替我顶一顶啊!可惜都走了,都走了。”他眼前浮现着那座集市,那条巷子,那山路,那小桥,那盏灯……现在全都看不见了。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生离死别?
噩耗相继传来。5天后的下午,蒋洪生才得知自己在地震中已经永远失去了儿子、二姐、侄儿、岳父等15位亲人。他默默地听着亲戚对他诉说这些亲人遇难的经过,一言不发,一滴眼泪也不落。妻子最了解丈夫的心情,她紧紧攥着蒋洪生的手,哽咽着说道:“洪生啊,你想哭就哭吧!”蒋洪生搂住妻子的肩膀,嘶哑着嗓音说:“失去这么多亲人,我能不伤心吗?我又不是铁打的。可我有时间哭吗?总有一天我要大哭一场的!”蒋洪生闭上眼睛说,“哭完了,还要继续做事情。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必须懂得感恩,要回报支援我们的人,奉献祖国和社会!”说完,蒋洪生告别妻子,率领身边的干部又投入到救援中。
世界的目光凝结在这一刻了。军队的行动最为迅速,老百姓说,中国军队这回真的动了血本了。每次灾难来临,军人总是冲在第一线,与老百姓生死不离。13日中午,四川军区的精干小分队抵达震中汶川县。这是进入震中的第一支部队。
英雄的历史在召唤中登场了。冲锋的时刻已到,献身的时刻已到。
北川上空,乌云滚滚。童刚他们即将在北川上空伞降了。“同志们,下面就是重灾区北川,他们急需我们救援,是天上的凤凰,还是地上的鸡,全看你们的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相信,你们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一定会出色完成任务!我的要求是,着地以后,一个都不能少!听清楚了吗?”童刚带头喊:“明白啦!保证完成任务!”范大林等20名突击队员,齐声回应:“是!”他们喊着,纷纷往伊尔—76飞机舱口聚集。
“投入伞降!”郝立国嘶喊了一声。
轰的一声,飞机舱门缓缓打开。他们个个屏住了呼吸,心提到了喉咙口。童刚没有丝毫的犹豫,眼睛一闭,嗖的一声,第一个跳下去了。随后,20位勇士紧跟着从天而降。这赌上生命去拯救生命的一跳,是世界伞兵史上最辉煌的一刻。他们离开机舱的瞬间,风没止,雨没歇。但是,他们携带着希望之光,投降到最需要他们的受灾群众中去了。
人们发现灾后的天空上,盛开起20朵绿色的云彩,向着废墟的大地扑进,扑进。这里平均海拔4000多米,大气压只有400毫米,氧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一半,而且还是强风地带,一直是空降兵的“死亡谷”。降落地点选在山谷的一块丛林里。在空中,降落伞鼓满了风,四个角像四瓣羊角花瓣儿缓缓降落着。
童刚在接近地面时,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气流,一时无法准确掌握降落地点,好在他落在一块山坡的草地上,而同乡战友老范却挂在了河谷旁的一棵树上。树干发颤,老范随时有可能掉进滚滚大江。童刚朝他呐喊了一声:“大哥,别动,等着我。”老范脸上没有恐惧:“我不动,好兄弟。”童刚爬上旁边一棵大树,上到顶端再抓紧枝杈,身子猛地一悠悠到了老范的这棵树上,一点点靠近降落伞,掏出匕首割断了伞线,艰难地营救了老范。老范激动地与童刚紧紧拥抱,连声说:“格老子谢谢你喽,我的好兄弟。”童刚说:“都是好兄弟,谢啥?”两人与其他战友会合了。但是,一个叫张一生的战友失踪了。郝国立班长留下两名战士寻找,其他队员翻山越岭向北川县城徒步跋涉,用砍刀开路,与死神赛跑。
翻过了一座小山,又转过一个山坡,童刚他们站在了山顶上。朝山下看去,北川县城,一片狼藉,除了少量矗立的高楼,楼房大多东倒西歪,有些已被泥石流淹没,石头压住了街道,到处流动着死亡的气息。他们哭了。容不得他们震惊,一阵余震袭来,巨石哗啦啦滚过,老范嘶喊了一声:“躲开!”摁下童刚的脑袋,躲过了一块巨石袭击。他们的第一任务是勘察灾情,郝国立让童刚赶紧给团长通话,卫星电话都通了,童刚却眼前一黑,哑着嗓子说不出话来。郝国立抢过他手中的电话,哽咽着说:“报告首长,北川县城平了,巨石滚落,道路堵塞,太惨了!”团长催促:“请再说一遍!”郝国立泪流满面:“首长,北川是最重的灾区,太惨了!都平了!”团长给他们下达命令:“北川的情况我们知道了,你们先冲上去,赶紧救人,时间就是生命!”郝国立抹了一下眼睛,“是!”他转身指着山下大声命令道:“同志们,灾区人民等着我们去救助,立功的时刻到了,跟我来!”童刚和他的战友们整理好行囊,像猛虎下山一样义无反顾地冲向他们的战场。
下雨了,救援队伍踏着泥泞进了北川城。粗密的雨点子,鞭子一样抽打着童刚他们。童刚耳边震响着爷爷的那些嘱托,两腿生风,虎虎生威地奔赴救灾战场。“赶快救人!”这是进入县城后,站在废墟上的班长郝国立发出的号令。有群众大喊了一声:“解放军来了,我们不怕了!”童刚和战友们奋不顾身地冲到废墟上,开始了紧张的扒人战斗。不一会儿,他就从一处废墟底下扒出了一个小男孩,大约七八岁的样子,还活着,浑身是血。他把孩子交给一名医务人员,又从木梁下面拉出了孩子的母亲,她被砸断了双腿,失血过多已经昏厥。血,掺杂着灰土的人血,沾满了童刚的双手,黏糊糊的,带着一股刺鼻的腥味。跨过几处木头与砖堆,又越过半截断墙,他的眼前猛然闪出一具白乎乎的女人的遗体,两位直了眼的老人正在院子里往她身上盖一条破被单。一问,她的新婚丈夫还埋在旁边的瓦砾中。童刚竭力控制住涌上大脑的热血,忙和大家奔上那座半人高的房堆,用双手疯狂地扒开着。玻璃、瓦片、钢筋很快就把他的双手划得鲜血淋漓。盛夏季节穿的解放鞋不断碰到钢筋上,脚被划开了一道道肉口子,他竟一点儿也没觉出疼来。砖、瓦、木片、灰土纷纷飞向一边,很快露出一个年轻男人的身体,显见是受了重伤,口鼻都在流血。
“有医生没有啊?快来人哪!”童刚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没有人回答。只是围上来不少不是医生的人,关切地凝视着眼前这个垂死的生命,扼腕叹息,泪流不止。范大林跳着脚骂着:“医生都跑到哪里去了嘛,叫老子抓住非枪毙了不可。”郝国立制止道:“别骂了,这里的医生有几个还活着都不一定啊!”范大林喊:“那就眼睁睁看着他死?他刚刚结婚。”郝国立低下头:“有啥法子么,我们又不是医生。”童刚分明感觉到,怀里的新郎呼吸越来越弱,已经气若游丝,不甘心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而自己无能为力,只能一遍遍地呼唤着:“你醒醒,醒醒啊!”那个新郎大睁着一双渴求生命的眼睛,仿佛在向童刚他们说着什么,然而只见嘴唇微微翕动,根本听不见一点儿声音。终于,新郎一动不动了,摇晃他的身体也没有一点儿反应了,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永远定格在了这一时刻。没有比这种现实更加残酷的了,童刚只觉得喉咙里在喷火,整个胸腔像吞进了一颗炸弹随时都要爆炸,他疯狂地撕扯着自己的上衣,仰天发出了一声狼一般的号叫:“啊……”声震长空。
黄昏降临,太阳还没有沉到谷底,月亮已经浮了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