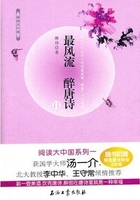我写了这么多行字,现在我发现自己像个喜欢用贝壳把海水引到岸边沙坑里的顽童。不过,艾敏,难道你没发现这字里行间有几行不是用墨水写的吗?关于那几行字的隐秘,我希望你来分析。因为那几行字是用灵魂手指写成的,因为那几行字是用心汁写成的,因为那几行字写在爱神的面颊上;那爱神挺立在大地与晨星之间,遨游在大地的东方与西方之间,永远波涌在我们的心灵与至高无上的光环之间。
艾敏,请在你父亲面前提及我的名字,向他老人家转达我对他的钦敬之情。请向你的母亲——一位给阿拉伯世界以巨大力量的母亲,一位给黎巴嫩一闪光火炬的母亲,一个以亲爱兄长让纪伯伦倍感幸福的母亲——转达我的问候。艾敏,希望你就像四月的惠风吹遍苹果树花那样向所有亲朋好友问安。玛尔雅娜从海外向你问好,为你祈祷祝福。我们希望你万事如意,平安顺利。我的亲戚穆勒哈姆及他那聪明可爱的女儿要我代他俩向你问安。大家都常提到你,亲爱的艾敏兄弟,他们都很想念你。
纪伯伦
1909年7月28日巴黎
艾敏兄:
这是我寄给你的另一篇小文章,是我昨天听说我的一位朋友与他那漂亮的女友分手之后写就的。
现在,我面前有篇新文章,刚写两页,是我今晨开始写的,写完之后将寄给你。艾敏兄弟,请稍等。
求你把你和《侨民报》的情况告诉我。我希望你告诉我个好消息:“《侨民报》不会迁往叙利亚。”艾敏,我之所以这样说,因为我知道,在东方,《侨民报》的生命将被种种危险和恐怖所包围。向所有喜欢你的人问好致意。
纪伯伦
1909年7月30日巴黎
艾敏兄:
我刚刚收到最近一期《侨民报》,使我静静地站立沉思。我不说遗憾,因为你比我更清楚《侨民报》在叙利亚的前途。告别的文章表明心中的希望和胸中的期盼。这使我展望未来——以未来的全部远离之苦——以希冀和等待的目光展望未来。
我昨天寄给你一篇短文,本想明天再寄一篇给你。但是,《侨民报》再也不在艾敏·欧莱伊的羽翼下了,因此,我不想再给《侨民报》投寄什么东西。那文章将保留在我的笔记本里,一直等到艾敏·欧莱伊的羽翼下长出第二种报纸。
现在,我求你把你想做的事告诉我,告诉我你何时赴叙利亚,以及你在美国的物质、道义关系。艾敏,假若我今天在纽约,我定把《侨民报》编辑部从你手里买下来。可是,木已成舟,生米已经做成熟饭,我还能说什么呢?
艾敏,我求你把我手里没有的《侨民报》的合订本给我保留在纽约。当你路过巴黎时,我将把钱付给你。因为《侨民报》的合订本上载有我写的全部文章,我当然是要保存它的。同样,我想保存我所喜欢的每一期报纸,因为我喜欢它胜过任何一种报纸,而且我曾竭尽全力为之效劳。最后两期合订本保留少量即可,暂放在法奥尔家,或者放在玛丽·伊莎·胡里太太那里,或者放在你的贤婿处。
《侨民报》已经落在再也不会触摸纪伯伦的手的手中了;对于《侨民报》来说,纪伯伦也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但是,艾敏,《侨民报》一词将永远是那样甜美、滋润。
爱你的兄弟
纪伯伦
1913年2月18日波士顿
艾敏兄:
这是你在这个国家,我要给你说的最后一段话;话虽短,却发自内心神圣之处,并带上思念的长叹和希望的微笑。
愿你月月、日日、时时健康快乐,尽情欣赏你在所到之处看到的美好事物,并将那些影响及其在你心中的回声保留到你返回亲友中间的时刻。请多见见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侨民报》的热情读者,向他们说说他们在海外的兄弟们的心里话;因为我们的心与他们的心之间相隔距离遥远,有许多情感难以交流,还请你代为沟通,愿你成为纽带,把我们的心与他们的心紧紧联结起来。望你清晨站在黎巴嫩的一座山顶上,观看日出及金色阳光遍洒乡村和山谷的壮景,并且将此天绘图刻画在你的心房,以便你回来后好让我们欣赏。请你在黎巴嫩青年一代面前,亲切地道出我们的衷心祝愿。请你告诉叙利亚的老人们,就说发自我们头脑和胸中的一切思想、情感和梦幻,都将飞向他们。当你乘船到达贝鲁特港时,请你站在船头,遥望萨尼山和米扎布山口,代我们向长眠地下的先辈和活在世间的父老兄弟问安。请你提及我们在公众集会和私人聚谈中所付出的努力及辛苦,就说他们在美洲播种,正是为了有一天在黎巴嫩得到收获。你只管说,只管做,只要你高兴;因为你高兴才是旅居美国的每一个真正黎巴嫩人所期盼的。玛尔雅娜紧握你的手,并衷心为你祝福祈祷……请在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侨民报》热心读者面前提及我的名字;也许我的名字一进入他们的听觉器官,会化成甜美乐曲。
艾敏,再见!再见,亲爱的兄弟。
纪伯伦
纪伯伦书信摘录
这是纪伯伦写给《侨民报》主编艾敏·欧莱伊的书信摘录。艾敏的胞弟、画家海里勒·欧莱伊将之摘录在自己的日记中,其中一部分曾发表在已故历史学家优素福·易卜拉欣·耶兹拜克主编的《黎巴嫩文稿》杂志上。
黎巴嫩、叙利亚和埃及的部分报刊转载纪伯伦在《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时,既不署纪伯伦的名字,也不提文章来源,致使艾敏·欧莱伊十分生气,并以中断文稿交流威胁这些报刊。《实况喉舌》主编哈利勒·赛尔基斯只得写信给艾敏表示歉意。就这个问题,纪伯伦写信给艾敏·欧莱伊,信中说:
……假若《实况喉舌》、《艺术之果》和《灯塔》杂志再偷我的《泪与笑》,请你手挥利刃,斩断它们的魔爪,一来教育他们,二来警告他人,让它们从《侨民报》转摘东西时,记住那是从《侨民报》上偷窃的。因为那是我的当然权力。
《埃及联合报》写信给其主编奈吉布·葛尔高尔,盛赞《侨民报》上发表的纪伯伦的散文,并提及《埃及联合报》曾转载过其中一篇。纪伯伦写信给艾敏,信中说:
我看过《埃及联合报》及其他报刊所载文章,你们愿意说我什么,就请说吧!你们乐意转载我的什么文章,就请转载吧!但是,你们不能够改变我的自我信仰,我深信纪伯伦这位在黑暗世界中蹒跚行走的柔弱老翁,一心想借朱庇特的闪电、雅典火炬之光、阿施塔特的光荣之美、阿波罗琴弦之歌,直到应该得到你们给的评价,至少让我知道自己距目的地还有多远?
纪伯伦在《侨民报》上发表了一篇谈侨民诗人的文章,从而引发了纪伯伦与艾斯阿德·鲁斯图姆之间的口角,但艾敏·欧莱伊能够使二人重归于好。纪伯伦读过艾斯阿德·鲁斯图姆发表在《侨民报》上的一首题为《将军与大军》长诗新作之后,写了一封信给艾敏,信中引了长诗中的几行诗:
其时将军像只鸟,
遭俘翻腾欲飞逃;
不期大风伤双翅,
脊梁几乎断碎了。
纪伯伦评说道:
这真是好诗。这是我近来谈到的鲁斯图姆的精辟创造性比喻。请代我谢谢他,并转达我对他的最美好问候。衷心祝福他获得成功。
《胡达报》主编奈欧姆·姆凯尔泽勒鼓励纪伯伦在他办的报上发表文章。艾敏便写了一封信给纪伯伦,信末尾说:“亲爱的物质的新朋友,我不对你说‘告别’,而是对你说‘再见’。”这句话使纪伯伦感到痛苦,他回信说:
你的纪伯伦不是物质的新朋友,也不会成为新物质的人,而是旧精神的人,尽管他在物质上是弱者,尚需要吃和穿,以便防饥御寒,免受大自然因素侵袭。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心中至爱和保留生命。
纪伯伦致贾米勒·马鲁夫
贾米勒·马鲁夫(1879-1951),生于泽哈莱。在故乡接受初等教育,后入贝鲁特希克玛学院。
1897年移居纽约,主编《天天报》;该报原由贾米勒的叔父努阿曼·马鲁夫发行。后由纽约迁居巴西圣保罗,继而迁至巴黎和矮斯塔那,然后返回黎巴嫩。贾米勒·马鲁夫留下大量政治、历史著作,其中有:《新土耳其》、《人权》、《民族如何振兴》、《拿破伦·波拿巴的统治》、《女人国》和《黎巴嫩问题》等。
1906年11月2日
亲爱的贾米勒:
你现在在太阳运行的另一个方向,而我仍在这里;我想念着你,而你已距我遥远。但是,这遥远的距离却不能将我们分开,因为巨大的心灵中有无数晕环,就像石子击破静静的湖面荡起的层层波环。
……我们这里是秋天。万木瑟瑟抖动,将剩余的黄色泪滴飘飘洒洒地抛洒在枯草地上,空气中波涌着冬翁的气息。不几天之后,田野和草原就要披上银装。你们那里是春天,生活在苏醒,欢快地唱着歌儿行进。莫非你离去时带走了春天,还是无论春天走到哪里,大自然便美上加美,一片生机?
我依如积习,忙于写作和绘画。时而遨游太空,追逐着被太阳染着金色的云朵。时而沉入大海深处,聆听波涛的呼唤声。我时而跌入黑暗的山谷里,这里充满可怖的幻影,时而又登上松柏密布的山顶,倾听回声的乐曲,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命运降临到我的头上。
这种思想折磨着我的心,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找到值得留存的东西。不过,我应该发奋图强到明天,明天将为我进行裁决,它的裁决是公正的。但是,我想在走之前听一听裁决。
……我亲爱的,爱情是爱情的镜子。爱好是爱好的猜想。真正的爱情不会居于一颗心中,而要居于两颗心中。这使我想起我们曾经谈到的那种火焰,上帝亲自将之分为两半,一半是男人,另一半是女人。
……你在最近写给我的那封信中说,你多么希望有一颗充满爱的心和一个饱含恋情的魂。亲爱的,我可不希望如此。我宁可因爱而死,因恋而亡,也不要远离爱与恋。我宁愿被圣火吞食,也不愿意身被冰包雪裹。我此生中的最大欢乐便是感到魂饥心渴;不饥之魂不会遨游梦想太空,不渴之心也不会翻飞在美之源泉四周。就请你保持原状吧!千万莫求孤独,因为孤独中存在着令人死亡的厌烦。
纪伯伦
1908年波士顿
贾米勒兄:
读到你的来信,我只觉得有一颗神奇的灵魂在房间的各个角落游动。那是一颗美丽而令人痛苦的灵魂,它以它的波涛将我分离开来,于是我看到你成了一位具有两种不同圣象的人:一种圣象展开巨大翅膀飞翔在人类的上空,那翅膀就像约翰看见的站在七个尖塔旁的宝座面前的六翼天使的巨大翅膀;另一种圣象则是被坚固的锁链锁在巨石之间,就像将第一只火把从天上降入人间的布鲁米斯,神灵们甚为生气,于是将其躯体捆绑在海岸边的一块巨石上。一种圣象令我心神欢快,因为它伴随着太阳的灿烂光辉和拂晓的惠风波动起伏;另一种圣象使我情感痛苦,令我心与肋饱受压迫,因为它是夜神的俘虏。你过去和将来仍然能够从天上取来火焰,并能将之交给人类,为他们照亮前进道路,可是,世间有哪一条法律,有哪一种力量能将你置于圣保罗,又将你的躯体禁锢在那些生来就已死亡,只是尚未被埋葬的人当中呢?难道希腊女神仍有力量束缚这几代人吗?
我听说你想回巴黎居住。我也想去巴黎,我们能在艺术之都会面吗?我们能在世界中心见面和同住吗?在那里,我们夜里同去听赏戏剧,去法兰西游乐场,然后回来谈论拉辛、高乃依、莫里哀和雨果的作品。我们相聚在这里,漫步走到巴士底狱,然后回到住处,仔细体会卢梭和伏尔泰的精神,然后再写作,写作。我们写关于自由和专制的文字,以便帮助人们摧毁东方每一个地方的巴士底狱。或者,我们去卢浮宫,站在拉斐尔、达·芬奇和柯罗的绘画前留意欣赏,之后,我们返回住处,写作,写作。我们写关于爱和美的文章,写二者对人心的影响。我们这样安排,你说好吗?啊,我的兄弟,我感到饥饿难忍,迫切需要接近艰巨伟大的工作;我感到思念难耐,曲线向往那种壮丽不朽的话语;我觉得这种饥饿和思念是深藏在我心底里的那种巨大力量的结果。那是一种想以不能估计的速度宣布自己存在的巨大力量,只是因为时间尚未到来——因为生时就已死亡的那些人成了活人行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我的健康情况,正如你所知,是一把握在不善弹奏者手中的吉他,使你听到的只能是不令人喜欢的乐曲。我的情感如同有潮有汐的大海。我的神魂如同鸟,双翅已被折断,只有藏在树枝之间痛苦不堪,因为看到群鸟展翅翻飞,而它却不能与它们长空比翼;但是,它像鸟儿一样,喜欢夜的寂静,喜欢晨曦的来临,喜欢太阳的光芒,喜欢山谷的壮美。我时而绘画,时而写作;在绘画和写作之间,我就像一只小船,漂泊在身不知底的大海与蓝天之间;那蓝天便是离奇的梦幻、崇高的意愿、伟大的希望和断断续续的思想。在这些梦幻、意愿、希望和思想当中有一种东西,人们将之称作绝望,而我却将之称作火狱。
我昨天寄给你一本小册子,名叫《草原新娘》,由三个短篇小说组成。第一篇名为《世代灰烬与永恒世界》,那是我们关于真实一半的谈话的结果。我是在它那美的灵魂用它那饰带边沿触摸我的情感和你的声音回荡在我的耳际中时,写成那篇故事的。第二篇题为《玛尔塔·芭妮娅》,那是一位烟花女子的痛苦所洒出的一滴燃烧着的眼泪。那女子还未听到一男子心灵的呼唤声,而且她的灵魂,也没有感受到遇到真正一半所激发起的天赐爱的冲动时,她便依附了那个男子。第三篇题为《痴癫约翰》,讲的是一个在黑暗舞台上的令人悲伤的故事,那是一个鲜活的故事,记录了一个盲目屈服者的生平及害人的专制制度。我观察过,认为过去作家们与牧师的专制进行斗争和反对屈服所采用的手段本身就有害于那些作家们的原则,而有利于敌人。那些作家们把蔑视宗教传统作为打倒那些坚持传统的神父的办法,那是错误的。因为宗教情绪是人的一种自然情感,而通过宗教说教实行的专制制度则相反,根本不是一种自然情感。因此,我使约翰热爱耶稣,信从《圣经》,忠实地服从宗教教育。
……你沉湎于香烟和咖啡,使我对这两种东西更加喜欢。我本以为更加喜欢香烟和咖啡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正像你所知道的那样,我的生活已离不开咖啡和香烟。我想起了一个小故事,非讲一下不可,因为它与咖啡和香烟关系密切,请听我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