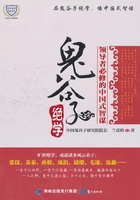黄土小屋,这种泥土的建筑代表的是一种汉语言的气质和性格,它是属于混浊不清的语言谱系里最坚刼的种子,随着春天的桃花的花蕊被播种在古人的诗句里。我以泥水匠、伐木者、酿酒师的身份站在黄土小屋的屋顶,阳光下远方的高原连绵起伏,绿色的海浪带着民间艺人沿着黄河的流水走向远方,被泥土的波浪湮没的黄土小屋只露出青黑色的屋脊。屋脊上的青草和芦苇的气息会把远方的梦境带回他们贫苦的村落,沉淀在黄土小屋的记忆里。
北方黄土高原上,骨骼清痩的黄土小屋,茅草屋檐下,我曾经在漫长的雨季中饱受刺骨的煎熬。北方的冷雨打在屋顶上乌黑发亮的一排黄土烧成的青瓦上,烟尘滚滚、瓦松、茅草、野花、洁白的棉絮、芦花都从屋顶上滚落下来。冰冷的雨水浸泡着焦渴炸裂的金色玉米。田野里一排排的黄泥小屋的屋顶在雨水的敲击下,屋瓦的夹缝里开始冒出蒸腾的水汽。贫瘠的屋顶长满粗野的花朵,金黄、橙色、黑紫的花瓣从泥土里探出身体,那微小干瘪的种子挣脱束缚的一瞬间,那些泥土就开始塌陷。从更远的高原上遥望凸出的青色的屋脊,雨水把青草的味道带给天边的云彩,那是生活在这黄土小屋里孩子的童话。
一粒盐巴,一颗小石子,一件羊皮袄,打结的草绳,这是黄土小屋的全部。
黄土高原上迷失的河流将更多的黄土和故事带到这个世界。千里茫茫,黄土的泥浪波澜壮阔,穿过山谷和石崖,在泥水匠,伐木者,酿酒师的皱纹里,这些讲给黄土地上的娃娃们的故事就是天上的云彩,无论是在传统的祭祀还是祈祷中,这种五彩的河流就是古代的大禹和造字的仓颉所使用的黄土,长大的娃娃都会因此有着健壮的体魄。
我一直相信,五彩的河流就在我手中的泥土里隐藏着,在酿酒师苍老的歌声里,它会带我像云朵一样找到汉字的归宿和童话。我在黄河的水声中学会了汉字的发音,虫,鱼,鸟,兽。我看着泥水匠用朴刀在屋脊上刻画着这些吉祥的符号,这些是我汉字的启蒙,草木山水,都是这种劳动种出的智慧。
伐木者建造的绿色屋脊,五彩的云朵,那就是高原上唱歌的河流。那是我回家的路。高原的风儿将绿色的河流带到我的心里,母性的河水哺乳着我的成长。
古代的黄土如今成为伐木者和酿酒师屋脊的一片砖瓦,呢喃的歌声穿过春天的绿色树林,跟着民间艺人一起上路了。这群穿梭在黄土高原上的民间艺人是风的歌手,他们黑色的头发里夹杂着稻草的沉香,远方泥土的气息使城市里的孩子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们背着行囊叫卖木雕的手工艺品。在孩子的眼里,他们像风一样穿过城市,他们的歌声是神奇而美丽的。这些民间艺人也像漂泊的孩子一样,穿过河流和城市,把他们的故事带到云朵飘到的地方。
我在高原的故事里寻找汉字的始祖,它是古代的大雁,在高原上栖息,有着金色的翅膀,汉字的形体,骨骼。听着高原上的民歌,风吹来的沙飘过黄土屋脊,娃娃们就在屋脊下看着那些雕刻的图画文字:蟲,魚,鳥,獸。低矮的屋脊就是他们的黑板,汉字的发音是鲜活的,他们能感觉到那黄土屋脊的寓言,风会把他们的梦想和故事带到北方的河流。
北方大地,河流苍莽逶迤,黄土高原北起古代的长城和阴山,南达秦岭,西抵祁连,东至太行。在波浪跳跃的地势上,你可以看到彩云与青草屋脊,就像内陆陆地挺起的脊梁。黄土塬上的沟沟坎坎,山尖尖,圪梁梁,羊肠小道有脚板硬过石板的孩子和抽大叶烟的泥水匠,酿酒师踩出的打夯歌,吆牛调。
高原上的孩子都有这种悲伤和故事。树木被伐木者雕刻成屋脊上的横梁,支撑着黄泥小屋,家庭,支撑着汉字的谜语。贫贱的黄土如今和着苦涩的雨水成为黑瘦而暴躁的一群人的家。泥墙里混杂着草根、砖石、瓦砾、铁屑,更多的是人的汗水。金色的稻草和骄傲的芦苇混流在这贫瘠得几乎使人发狂的世界,以一种宗教似的姿态成为这黄泥小屋最结实的一部分。这种生活方式和观念从一开始就影响着我的思考。咀嚼着苦涩的草根,看着田野上一墩墩结实的茅草房子,我对那种水土和饮食特殊的理解就扎根在这酸楚的草籽里。当暴雨狼命地抽打着这屋脊,看着人们裸露着脊背拖拉着农具陷入慌乱,看着泥浆渐满那张衰老的悲观、焦急的脸,我在古老的歌谣引导下,沉迷在这酸楚的雨季,我听到了那破旧的屋脊的呻吟。往事和心火慢慢郁积,直到风雨慢慢停歇。那泥墙里的芦苇巳经失色,丧失锋利,金色的稻草也巳经腐朽,庞大而虚弱的泥墙就在风雨侵蚀下濒临坍塌的宿命。
伐木者建造的黄土小屋,它不是清真寺,没有信仰,也不是教堂,没有人为它祈祷,为它迷狂、献身。它旋生旋灭,在这焦渴的土地上挣扎。水土接不上文明的血脉,只能由它自己来承担和选择这历史的宿命。野花的繁殖,瓦砾的腐败,荒草的疯狂,黄土世界滚滚红尘,巳经不可阻挡地陷入生存的困境。黄土屋脊雕刻的龙凤、虎豹,还有那展翅的孔雀如今只能作为一种象征牺牲了,那屋脊庞大的木质骨架在蠹虫的腐蚀下渐渐地剥离了美的符号和色彩,剩下消痩的骨骼和浄狞的身体。时间和世情一起压榨着这黄土的骨血,如今能剩下的只是狼藉的风景。这种悲壮启示着我,支撑着人们在困境里生存下来的还应该有另外一种知识和精神。
屋脊是泥土的,它并没有睡着。它还在呼吸、呢喃、唱歌、蠕动、飘浮。它是松软的,有生命的,有记忆,有翅膀,它会做梦,讲故事,会咿呀学语。站在高原上,你看到它好像是飞进你的视野里的,你觉得它又像是在缓慢地移动,是童话里的移动城堡。它没有徽派建筑的繁杂,没有竹楼的飘逸,也不是纯粹的木石结构。它活动着身子骨,像云朵一样俯卧在屋顶。从起伏的高原上看,它是流动的,伸缩着疲惫的脊背,肩胛骨,踱着步子,炊烟就从青草屋脊上升起,孩子们的朗读声也袅袅浮现。
虫,鱼,鸟,兽。掌握了汉字就懂得了黄土屋脊的意义。汉字的书写规则和美感就在于这种寓言包含的秘密和启示。父性的屋脊,承载的是一个家庭,一个故事的秘密,就像黄土高原承载着汉语的秘密,它是在这个寓言中成长的孩子的童话。汉字的骨骼,黄土的厚重,它们构成高原上绿色的文明。雕刻的木纹承受着风雨的侵蚀,它对于我来说就是汉字文明的脊梁。高原苍莽一片,母亲河的水声和歌声都沾染着这种血性与唯美。这种丰腴的汉字和娃娃们健壮的躯体因此在高原的恩泽和河流的哺育之下,有着金石的质地,文明的建筑即使被高原的沙砾湮没,也不会土崩瓦解。
屋脊覆满青草、芦苇和爬山虎,落满蒲公英、矢车菊、荞麦,有时候会发现一棵羊齿、玉米秸秆、铁蒺藜。疏雨茅檐,泥土小屋,漏雨苍苔,但是不能惊动中枢的屋脊。它沉静,富有智慧和经验,坚忍而倔强。+年,几+年的光阴不会磨损它的锐气和稳重。泥水匠和酿酒师的黝黑的脊梁就像山脊一样,风吹雨晒,兀然自若,这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和勇气。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古代的文明血液浸染着黄土,它们成为娃娃们的姓氏,名字中的一部分。它们就像高原上传奇的山鹰,是贫困的家庭里那巨大的檩,是父亲们歌声中绵延的山脊,承载着一种勇敢。
遥望黄土高原上的村落,你会看到那结实坚刼的青草屋顶,雕刻着鱼纹陶盆的屋脊。使用青铜农具,背诵汉语拼音的黄土地的后代有着钢铁的筋骨,动情的腔调。犁铧翻开汉语的书卷,那种东方古老的传说在黑污的棉絮,发黄的牙齿,黑脸膛的孩子们的童话里复活。如果你从文明的城市,跟随酿酒师、伐木者、泥水匠的歌声一路穿越波澜的黄土来到这彩云之下,你会为生命的坚刼,无聊的慰藉而失色。看着泥水匠,伐木者在黄土谷地上穿梭着,赤裸着青铜色皲裂的脊背,烈日的暴晒之下,你会联想到他们与黄土小屋草绿屋脊的本质关系。
从遥远的文明世界,黄河的歌声会把你从尘嚣的中心带到汉语的腹地。沧浪之水,无疆的高原山梁挺拔,地势连绵,母语的海洋那最珍贵的一抹绿色原来就是贫瘠的黄土小屋那屋脊之上不息的绿色。
从遥远的古代长城开始,高原的孩子美丽的童话会把你从城市的沙漠带到母语的河流边。让你跟随戴着白头巾和羊皮兜的伐木者和唱爬上歌的酿酒师的歌声,来到文明奔腾浩荡的绿色流域。人们会击鼓而歌,把你的悲伤湮没在绿色的潮水里。巨大的脊梁黑色累累的伤痕,像被割破了血肉的陶罐色彩烧伤了我疲惫的眼睛,色彩点燃了整个黄土地,流淌着,浦动着,湮没古代的卵石,古老洁雅的音调,逍遥的文字。
我不知道古代的仓颉有没有眼泪。文明的世界,汉字的秘密如烧毁的胛骨,木刻,被伐木者和酿酒师雕刻在贫瘠村落里茅草覆盖的屋脊上。这种吉祥的文字成为人性的沙漠里灼烫的绿色,蘸着笔墨,写下的全是五彩华章。
渐渐地,我感到了它的柔软和苦涩,青草的绿色弥漫原野,那是泥水匠掌心里的春雪,是屋脊上的刀痕。文明的大陆,彩陶色彩一样的屋脊,我所歌唱的就是那生命河流中一抹绿色。
金色的阳光下,风儿吹过,白云飘过,我坐在黄土高原的屋脊上,让我扯开嗓子给你唱一首高原情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