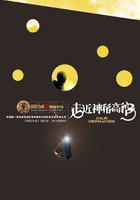前段时间我在广东,本来想去罗浮山,没去成,就在深圳呆了几天,碰到了一帮搞影视的朋友,他们想拍讲惠能大师的片子,片名就叫《三更鼓》。关于这个“三更”,广东和香港的朋友用广东话来读,指出应该读成“三更(jīn)”。这种读法合于古法,是客家人保留的中原古音,我认为是正确的。广东的朋友都因为惠能是广东人而感到很骄傲,我身在广东,也跟着沾了光。惠能原来是北京人,关于这一点,又重要又不重要。《三更鼓》这部戏,究竟拍没拍我也不知道,但事情的发展往往奇妙,从广东回来后没想到我自己讲起了惠能大师和他的《坛经》,也许这是暝瞑之中的安排。当初存了一个念想,日后必会实现,这已是屡试不爽了。人只要发心正,一切皆有可能。《大学》所谓“正心诚意”,即此谓也。回北京后,我感觉惠能就在我身边,足音相接,气息相闻。我的左手摸着《坛经》,右手好像握着惠能的手。他想给我什么呢?他的衣钵我不要,还是请他自己留着用吧,我想知道他究竟有什么心事?一千六百年来无人知晓。也许,不是我与惠能有缘,而是惠能与我有缘。窗外暮色,室内华光。夜,又静了;心,也净了;人,更近了一分。如今,我就跟大家讲讲《三更鼓》的故事。
《坛经行由品》:祖(五祖)潜至碓坊,见能腰石舂米,语曰:“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乃问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惠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
这个故事讲的是,五祖弘忍大师偷偷摸摸跑到惠能干活的作坊,看见惠能的腰上绑了一块石头,增加自己的体重,正在跳上跳下舂米,把自己当成一个大棒槌。五祖哪里见过这种场面,见这小伙子这么能搞,忍不住就说:“求道之人为了佛法奋不顾身,也应该这样啊!”这个片断,是《三更鼓》的前奏。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惠能舂米很有节奏,就像三更打鼓一样,任何事情都必须要有节奏才能成。这个舂米的情节和接下来要发生的《三更鼓》的故事之间是有联系的,总之充满玄机。说是玄机也不对,有的事情该发生自然就会发生,你把玄机当玄机他就是玄机,玄之又玄,妙不可言;你不把它当玄机,就什么也不是。五祖见了六祖舂米,这老头就问了一句怪话,他问:“米饭煮熟了吗?”这不是句怪话吗?米还在石窝里,稻子刚脱皮,有的变成了大米,有的还没变成大米,这老和尚明明看见了,是不是饿疯了,几百年没吃东西?看见大米就想抓起来的是米饭,难道这就是他的活法?老头子戏弄小伙子,小伙子就大战老头子,惠能听了弘忍的怪话,回了一句更怪的话,他说:米饭早就熟了,只是还要筛两下。这句是怪之又怪的怪话,等于在命令一只已经煮熟的鸭子:去!下河去抓条鱼上来。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五祖见六祖破了他的禅机,知道斗不过这小伙子,看来这个接班人找对了,心里面很欢喜,不再废话,马上办事。老头用拐杖在石窝上“磕磕磕”敲了三下,然后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惠能对老头玩的这一手,感到很好玩,这不就是鸡啄米吗?老头啄了三下,看来是让他做一只鸡呀!鸡是干吗吃的?当然得打鸣,人还没有起床的时候,鸡就起床了。惠能明白:老师是让他在打三更鼓的时候进去。进去就进去,于是进去了。老师知道他要进来,先用袈裟把说话的地方围起来,做成一个袈裟帐篷,不让人看见,好秘密传法。这是一场遮得密不透风的无遮大会。我们可以想像得到:五祖先坐在这个袈裟帐篷里面,静悄悄地一动也不动,他的方丈室很小,不小也不能叫“方丈”,现在他在这小房间的小帐篷里面,要在这个小空间里办一件大事情。他闭上了眼睛,听啊。他听到了秋天的夜晚,风在瑟瑟地响,他的庙宇一片宁静,宁静之中暗暗有噪声。他又听,又听,听到了自己的呼吸与心跳,不紧张是不可能的。禅宗的命运今天晚上就要决出分晓。一更天,二更天,一声鼓,两声鼓,当三更鼓响起来的时候,鼓响他就来了。他坚定的脚步和鼓点融为一体,他踩着鼓点进发。他的肩头披着星辉,他的粗布衣袖盛满秋风鼓翼而进。一进方丈室,他带来的风就把门关上了。顿时,整个房间陷入了惊人的黑暗之中,这是他期待已久的静谧。“来了?”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他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师父”。“进来。”于是膝行而前,肩头披拂着袈裟,几乎就撞在了老师的胸前。黑暗中没有废话。老师向他讲起《金刚经》,这是他的本愿。当初,他兴起这段佛缘,就是因为有人告诉他师父在黄梅讲《金刚经》,如今他已经在黄梅,已经在师父的身边,师父正在给他讲《金刚经》,这是命定啊。师父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指导我不要执著才会得到自我。下雨的云怎样从空空的天上生出来,我们下雨的心就应该怎样从空空的世间生出来。四大皆空,真性不空。这就是惠能“三更鼓”得法所悟。
我们听了这个故事,是不是觉得五祖对六祖真好!要是你这么想,又被老和尚忽悠了。半夜三更把人叫进屋里说话,这只不过是老头儿的常用手段,并不是对惠能的特殊待遇,也毫无神秘可言。人已到老年睡眠就少,到时候你也会有听到三更鼓响就想找人说话的时候,寂寞呀!那时你会想起这句话。弘忍在黄梅,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法脉传下去,这个三更鼓,先前他已经上演过一次。那次他找的是谁?就是神秀。你细细地翻一翻《坛经行由品》就知道了。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这是我的研究,在别处你是听不到的。这个秘密就是:“三更鼓”上演了两次,弘忍传法先后传给了两个人,第一次他已经传法给了神秀,第二次他又传法给惠能。我这么一讲大家明白了吧,弘忍所说的“米饭熟了吗?”暗示他早就吃过米饭了,惠能如果不知道真正的米饭在谁手上,惠能舂米也白舂。这句话的机锋是何等凌厉!幸好被惠能识破。弘忍既然传了两次法,一法双传,那么以谁为准?他这么搞不是在制造矛盾与斗争吗?他这个做法埋下隐患,不是自己在拆自己的台吗?他是用心良苦搞了个备份,还是在告诉我们佛法本来就是同生同灭的?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没有读惠能的开宗明义第一偈,是不可能得到圆满回答的。
我们来看《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里面交代宝、黛、钗三人的来历。书是这样写的:“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到:‘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
空空道人这段话,一口气交代了宝、黛、钗三人的来历,称贾宝玉为“石兄”,称林黛玉为“蔡女”(蔡文姬),称薛宝钗为“班姑”(班婕妤);评贾宝玉为“自己说有些趣味”,评林黛玉为“或情或痴”,评薛宝钗为“小才微善”。我们姑且不管空空道人的评语如何,他开头说的那句话很有意思,照他说来,石头的故事是石头自己编写的,也就是说林黛玉、薛宝钗是贾宝玉所“经历”的,或者说,压根就是编造的。换言之,贾宝玉“生”出了林黛玉和薛宝钗,以提供他自己所谓的“趣味”。这层“玉生玉”、“玉生金”的关系是我们以往没想到的,却是《红楼梦》明文记载,这对我们准确把握《红楼梦》的创作动机有帮助。
《红楼梦》这个三角关系,其实说白了就只有一块石头在那里,正如《坛经》里的三角关系,其实也只有一个老和尚在那里把袈裟脱了又穿、穿了又脱,如此而已!什么叫“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就是要直面自己。当你找到了一个变无可变、失无可失的自我时,就找到了真实的自己,你就是你心中的佛。佛不分男女,佛也没有过去,惠能打出了弘忍的袈裟,这才有了一片新的天地。你想想看,简易房修出了大楼房,茅草棚捧出一个国家,只要直心直意干,路就在眼前。对上了号,自己就是门,自己就是台阶,自己就是大雄宝殿,还需要供什么佛?此为坛经第一偈。
坛经第二偈
惟求作佛,
不求余物。
(《行由品》)
一个和尚在私下里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两个和尚在一起肯定要说偈子。这首偈子就是惠能第一次见弘忍的时候说的偈子,那时候他还不是和尚,说了这首偈子他就成和尚了。
“惟求作佛,不求余物。”这是惠能对弘忍的回答。弘忍问他:“你是哪里的人?到我这里干什么?”惠能就恭恭敬敬地对师父说:“弟子是广东新余人,大老远跑过来拜见师傅,只求作佛,再不想做别的。”
我们细想:惠能这句话好无礼呀,他到底是来拜师,还是来拜佛?师父就在眼前,他却说想做佛,言下之意是他想迈过去,不想做师父这样的人,想超越师父做佛,这岂不是当面打师父的脸吗?后生可畏呀!当下弘忍就教训惠能说:“你是广东人,不是中原人,又是一个打柴的,就跟山林里的野人没什么区别,凭什么做佛?”好个惠能,牙尖嘴利,回答说:“人虽然分南北,佛性没有南北,野人的身体跟和尚不同,但在佛性上有什么差别吗?”见这打柴郎一下一下地来,弘忍觉得有意思极了,还想和他说几句,这时候人越来越多,庙里的老和尚、大和尚、小和尚都围过来,听这野和尚吹牛皮。弘忍呵叱了一句:“干活去!”安排惠能到作坊干粗活,对这孩子上了心,留了意,下了注,想赌一把,看他是不是真正能干大事的人,这才有接下来的“三更鼓”。
上述公案,是惠能见弘忍,不是弘忍见惠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此事对惠能来说,是必然、当然、定然,他在做打柴郎的时候,听人说起讲《金刚经》的弘忍这个人,那一瞬间,他被激活了因缘,启动了因果,心生欢喜,当下就发了大愿,一定要见弘忍,一定要听他讲《金刚经》,一定要成佛。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他能见到弘忍确实是一件必然会发生的事情;而对弘忍来说,惠能的出现完全是个意外。弘忍的庙在湖北,惠能从广东跑过来,要经过江西与湖南,前前后后走了四个省,好几千里路,不容易呀。但是这依然还不能说明什么,肯下功夫吃苦的人大有人在,敢发大愿心、敢说豪言壮语的人也大有人在,凭什么说他惠能就是佛菩萨选定的接班人?“惟求作佛,不求余物”。谁求谁?怎么个做佛?这段公案怎么参?惠能一来就要做佛,一来就要当老大,要做师父的师父,虽然自称“弟子”,他可不是来当徒弟的,那他来干吗?显然他的目的性很强,目标很明确,他来是想得宝,也可以说是抢宝、夺宝来了,怪不得接下来他就惹下了杀身大祸,有人欲灭之而后快。弘忍倒是容得下他,也在罩着他,但一个老头,行将就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都要日夜防着有些人来夺他的宝,又怎能不提心吊胆?原来是一个人想来夺宝,这下好,第二个夺宝的又来了,更凶、更强,更加目中无人,无法无天,这老头还保得住吗?都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也都说新来的就是最好的,往往最后出现的那个人就是得宝的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你不坐的车,它一辆接一辆地来,你要坐的车,等半天他也不来,世上的事情就这么怪,整得你没脾气;人也是这样,你想见的人见不着,不想见的人,一拨接一拨地闹。其实这些还是不关别人的事,是我们自己没想清楚,没看明白。弘忍能忍,他很喜欢这个无礼的惠能,他这是有道理还是没道理?什么叫做缘?它是方的还是圆的?如果真是一个圆,那么圆心在哪里?圆心的圆心是不是空心?心空了还是不是心?一颗空空的心,到底能装下多少东西?“唯求作佛,不求余物”。惠能说心就是佛,是想把心放在佛里面,还是把佛放在心里面?肉心能接纳真佛吗?肉身就是真身吗?为何人的肉体如此沉重?也许只有沉重的东西压在那里,才会发出一根灵芽。老子说:“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就是说人要把自己压在这里,才能长出希望。把自己压扁了,希望就压出来了。没有雪山,哪有雪山上的莲花?有雪有莲才叫雪莲,雪与莲原是一体,雪中莲、莲中雪都是它。看来惠能并不是来夺宝,因为他自己就是一块宝,怪不得弘忍喜欢他,并不是老的把宝传给小的,而是这老老小小都是活宝啊!哪里还需要什么别的宝。惠能见弘忍,这个公案就应该这么参。
《红楼梦》里的宝是贾宝玉,这块宝被人夺来夺去,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有无数的化身,可以分给所有的人,最终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人不把自己当完整的人,别人就会撕了你!《红楼梦》里这“一宝三身”,他们想合一,最终没能合一,留下了残缺美。我们来看宝、黛、钗三人最初的出场。
贾宝玉的出场:“这政老爷的夫人王氏,……后来又生一位公子,说来更奇,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就取名叫作宝玉。”(《红楼梦》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林黛玉的出场:“雨村便相托友力,谋了进去,且作安身之计。妙在只一个女学生,并两个伴读丫鬟,这女学生年又小,身体又极怯弱,工课不限多寡,故十分省力。堪堪又是一载的光阴。谁知女学生之母贾氏夫人一疾而终。女学生侍汤奉药,守丧尽哀,遂又将辞官别图,林如海意欲令女守制读书,故又将他留下。近因女学生哀痛过伤,本自怯弱多病的,触犯旧症,遂连日不曾上学。”(《红楼梦》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薛宝钗的出场:“且说那买了英莲打死冯渊的薛公子,幼年丧父……寡母王氏乃现任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之妹,与荣国府贾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纪,只有薛蟠一子。还有一女,比薛蟠小两岁,乳名宝钗,生得肌骨莹润,兴趣娴雅。当日有他父亲在日,酷爱此女,令其读书识字,较之乃兄竟高过十倍。自父亲死后,见哥哥不能体贴母怀,他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线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红楼梦》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这三段文字,表明了宝、黛、钗出处,三段文字要合起来看才有意思。《红楼梦》可不是一般的书,我说了《红楼梦》是小说版《坛经》,里面讲的是因缘,讲的是“直了成佛”,讲的是“惟求作佛,不求余物”。这一个人化出来的三个身体:宝、黛、钗,最后都惨兮兮的,谁也没成佛,但把他们三个人合起来看,依然是佛。
佛是什么?佛不是贾宝玉的誓言,不是林黛玉的眼泪,不是薛宝钗的金锁,但是他们三个人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那就是自由,也可以叫做解脱,也可以叫做归宿。贾宝玉和谁都有缘,跟林黛玉是木石缘,跟薛宝钗是金玉缘,他的缘大了去、多了去,偏偏跟自己没有缘,这样是成不了佛的。大家都把一块顽石当成宝,岂不可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