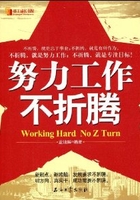第三十五章 处斩与狂欢 (1)
基督山伯爵一边向里走,一边说道:“请二位原谅我没能够先登门拜访,然而我又害怕去得太早会打扰你们休息。而且,你们也已给了我回音,你们是乐意来看我的,所以我真的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这时阿尔培回答道:“弗兰士以及我万分感激您,伯爵阁下。我们真是左右为难,现在真是大伤脑筋。然而正是您给我们解了围,接到您那恳切的邀请之时,我们正在发明一种稀奇古怪的车呢。”
伯爵一边请两个青年坐下,一边说:“真的!这都要怪那个派里尼,他真糊涂,否则我可以更早一些帮你们把困难排除。他没有跟我说起你们困难的境遇,而我,我又寂寞又孤单。我很希望有个好机会能够认识我周围这些邻居们。当我听到这件事上可以帮助你们,我便迫不及待地来抓住了这个大好的机会。”
青年人双双鞠了鞠躬。这时弗兰士还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合适,他也没有决定该怎样行动,而从态度上看,伯爵丝毫没有表现出他愿意承认他们已经相识了,他真是拿不定主意:究竟该提提过去的事情,还是随便看看外面的风景再作决定呢?更何况,他真的能确定他肯定是昨天夜里对面包厢中的那个人,但却不能断然肯定他就是斗兽场的那个人。所以他最后决定任其自由发展下去,因此就不向伯爵作任何正面的提示。再说呢,现在他比他占有优势,他已知道他的秘密了,然而他却没有捉到弗兰士任何东西,因而作为弗兰士,没有任何掩饰的必要了。但是,他决心要把话题引到一个或者能够搞清他现在还感到疑惑的问题上面。
他又说:“伯爵阁下,按您的意思,我们坐了您的马车,分享您在罗斯波丽宫所定的窗口。那么您能否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可看到波波罗广场呢?”
伯爵的目光死死盯着马瑟夫,漫不经心地回答说:“啊!不是说在波波罗广场上要杀人吗?”
弗兰士回答说:“对!”他的计谋也初见成效了。
“稍等一下,昨天我曾通知管家,叫他办完此事,在这一点上或许我可以为你们效劳吧!”伸出手,他便拉了三下铃。他又对弗兰士说:“不知您是否想过,用何办法可以使召唤仆人的手续更加简化?我倒是有的:我拉一下铃,意思是叫我的跟班;拉两次,则是叫旅馆老板;拉三次是通知我的管家。照此,我便可以少浪费时间,少说废话。哦,他已来了!”
这时,走进来一个人,约四十五岁到五十岁,很像那个领弗兰士进山洞的走私贩子,但是他好像并不认识他。显然,是别人吩咐了他。
伯爵说:“伯都西奥先生,昨天我说过,叫你去弄个可看得见波波罗广场的窗口,不知你现在办得怎么样了?”
管家回答说:“是,大人,但是那时已经太晚了。”
伯爵显然面带愠色,怒道:“我不是说我想要一个吗?”
“我还是给大人弄到了一个,那原本是租给洛巴尼夫亲王的,但是我出了一百——”
“那就够了,那就够了,伯都西奥先生,这些家务上的琐碎小事别在两位先生面前唠唠叨叨的了。既已弄到了窗口,那就够了。代我告诉车夫,叫他备好车在门口等我,准备送我们过去。”于是管家鞠了一躬,正准备离开房间,不料伯爵又说:“啊!麻烦你问问派里尼,问他是否收到了‘祈祷单’,能否给我们拿一张行刑的报单来。”
弗兰士却说:“不用了,因为我已看到了报单,而且顺便抄了一份。”说着他拿出了报单。
“那太好了,你去吧,伯都西奥先生,早餐准备好了立即来通知我们。这两位先生,”他转向两位朋友说,“我相信,你们大概可以赏脸和我共进早餐吧!”
阿尔培说:“但是,伯爵阁下,那可是太打扰您了。”
“你说到哪里去了,恰恰相反,你们肯赏光我感到非常荣幸。你们两位中至少一位,或许可以在巴黎有机会回请我。伯都西奥先生,别忘了放三副刀叉。”从弗兰士手里,他接过了报单。
他用读报时用的语气念道:“‘公告:奉宗教审判厅令,狂欢节的第一天,即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三,两名犯死刑的囚犯将于波波罗广场明正典刑,一名叫安德里·伦陀拉,一名叫庇庇诺,即罗卡·庇奥立;前者犯了谋害罪,他谋杀德范可风之圣·拉德兰教堂教士西塞·德列尼先生;后者则是臭名昭著的大盗罗杰·范巴之同党!第一名处以锤刑,第二名处以斩刑。’”
伯爵又接着说:“对啊,本是这样预定的,但是我想这个典礼的节目在昨天似乎已有某些改变了。”
弗兰士说:“真的?”
“太对了,昨晚我在红衣主教罗斯辟格里奥赛那儿,听别人说,两人之中已有一人被赦无罪了。”
“是安德里·伦陀拉吗?”
伯爵很随便地说:“不,而是另外的一个,”向报单瞟了一眼,似乎他一下子忘了那个人的名字一样。“是庇庇诺,也就是罗卡·庇奥立。因此你们虽然看不到有人上断头台,但是看锤刑的机会还是有的,那种刑法,如果你们是第一次看到,你们会感到非常奇怪的,甚至即使你是第二次看到,也不必惊讶仍有这种感觉。至于斩刑,你们肯定是知道的,那很简单。那断头机从不会有失灵的时候,也绝不会颤抖,当然也不会象杀夏莱伯爵的那个兵那样连砍三十次。红衣主教黎希留显然是由于看到夏莱伯爵被杀头的那种惨景,因而恻隐之心顿生,故而改良刑法了。”伯爵却以一种轻视的口吻又说道,“千万不要向我谈到欧洲刑法,如果单以残酷而论,说它处于婴儿期,还不如说它已至日薄西山的境地呢。”
弗兰士回答说:“伯爵阁下,是真的,肯定有人会认为您正研究着世界各国的刑法呢。”
然而伯爵却冷冷地说:“至少我可以说,我没见过的真不多了。”
“看到这种情景,你很高兴吗?”
“哦,开始也觉得很可怕,后来便逐渐麻木了,最后觉得很有意思。”
“有意思,这太可怕了。”
“为什么呢?我们在一生中,最担心的事就莫过于死了,那么,来研究研究灵魂和肉体分开的各种方法,并根据各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气质,甚至各国不一样的风俗,来测定从生至死,从存在到消亡这个转变过程中每一个人所能够忍受的限度,这难道算是好奇吗?至于我自己,我完全可以向你们保证——你看见人死愈多,你死时就愈容易。依我看,死可能是一种刑罚,但是并不就等同于赎罪。”
“但我并不完全懂得您的意思,”弗兰士道,“麻烦您再解释一下,因为您已经把我的好奇心引至最高点了。”
伯爵却说:“听着,要是一个人用些闻所未闻,最为残酷,最痛苦的方法来摧毁你的父亲,和母亲,以及你爱人,总而言之,夺去了你最心爱的人,在你的胸膛上留下一个永远都没办法愈合的伤口;而社会所补偿给你的,只不过是用断头台上的刀在那为数不多的凶手的脖子上割一下,让那个使你精神苦恼很多年的人只不过受了几秒钟肉体上的痛苦,你觉得那点补偿够吗?”说着,伯爵脸上流露出深切的仇恨。
弗兰士说:“您说得对,人类的正义是不够得到应有的慰藉的,她只能够以血还血,仅此而已。但是,你也只能够向她提出要求,而且实际上只能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要求啊。”
“而且我还可以简要举一个例子,”伯爵又继续说道,“在社会上,每当一个人受到死亡的威胁时,社会就会以死来报复死。然而,难道不是有些人遭受千千万万种惨刑,而社会对这些连知都不知道,甚至于连我们刚才所听说的那种不足以补偿的报复方式也不能提供给他吗?有一些罪恶,即使用上土耳其的刺刑,波斯人的钻刑,印第安人的炮烙和火印也都嫌不够呢,而社会却还是仍不闻不见,丝毫没有给予任何处罚吗?你能否回答我,这些罪恶难道不是存在的吗?”
弗兰士回答说:“对,而就是为了惩罚这种罪行,社会上才允许人们进行决斗。”
伯爵喊道:“呀,决斗!说句实话,当你的目的是为了报复时,用此法来达到目的未免太轻松了吧!如果有人抢去了你的爱人,奸淫了你的妻子,玷污了你的女儿,本来你是完全有权利向上天求得幸福的,因为上帝创造了人,也就允许人人均可得到幸福,而这个人的一生却遭了严重的破坏,并且终生痛苦蒙羞。使这个人大脑疯狂,心里绝望。而你呢,只因为你已把一颗子弹射进他的脑袋,或是用一把剑刺穿了他的胸,就自以为不共戴天之仇已报,然而却想不到,在决斗之后,胜利的往往是他,因为在所有人的眼光里,他已变得清白了,在上帝的心目中,他已经抵罪了,不不,”伯爵又接着说,“如果是我为自己报仇,我是不会用这种方式去报复的。”
“您的意思是,您并不赞成决斗了,您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和人决斗吗?”这次终于轮到阿尔培发问了,他对于刚才这种意见显得十分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