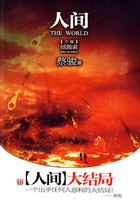第三十一章 水手辛巴德在意大利 (1)
一八三八年初,巴黎社会上层的两个青年人物,阿尔培?马瑟夫子爵和弗兰士?伊辟楠男爵,到佛罗伦萨来了。他们约好一同参加罗马的狂欢节,约定由弗兰士当阿尔培的向导,因为这三四年来他一直住在意大利。可不能小看罗马狂欢节,特别是如果你不愿在布尔广场或者凡西诺广场过夜。于是他们便给爱斯巴广场伦敦旅店的老板派里尼写信,定了几个舒服的房间。那老板回信说,那里一个里间和两个卧室,在三楼,租金很低,每天只要一个路易。他们接受了。因为还有时间,阿尔培便到那不勒斯游玩去了。弗兰士留在佛罗伦萨。在这几天里,他去了一家叫卡西诺的俱乐部,在佛罗伦萨的几个贵族家里住了两三天,访问了波拿巴的故地科西嘉以后,他突然想去参观一下拿破仑的监禁地爱尔巴。
一天傍晚,他解开一艘系在里窝那港内的小船,跳进去,裹紧身上的衣服,躺在里面,对船员说:“去爱尔巴岛!”小船飞快地开出了港口,第二天早上便到了,弗兰士下船登岸,逛遍了拿破仑去过的地方以后,他又在岛上玩了一番,然后便又上船,到马西亚纳去。过了两个小时,他在皮亚诺扎上岸,据别人绘声绘色地讲,那儿有许许多多的鹧鸪。但弗兰士的运气很差只打死了几只,像所有倒霉的猎人一样,他回到船上便大发脾气。
“哦,如果您高兴,”船长说,“我可以带您去一个很奇妙的地方打猎。”
“去哪里?”
“看到那个岛了吗?”船长指着远方,一个圆锥形的小岛耸立在蔚蓝的海面上。
“嗯,这是什么岛?”
“基 督山岛。”
“但我没有获得在上面打猎的许可证呀。”
“不需任何许可证,没有人住在那个岛上。”
“啊,真的?”这个年青人说,“地中海中居然会有一个荒岛。”
“那没什么,这座岛上面全是岩石,根本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
“它是属于哪个国家?”
“属于托斯卡纳。”
“上面都有些什么东西?”
“好多野山羊。”
“它们是靠舔石头而生存下来吧?”弗兰士带着疑问地笑了笑。
“不,石缝里会长出小树,可以吃嫩叶。”
“可是我在什么地方休息呢?”
“在上面的岩洞里,也可以睡在船上,而且,只要您愿意,打完猎后我们就马上回去。晚上我们也能航行,没有风,可以用桨。”
阿尔培一时还不会回去,罗马那旅店也给他们留着,于是弗兰士便答应了。听到他同意了,水手们又似乎在交头接耳地议论什么。“喂,”他问道,“什么事,还有问题吗?”
“不,”船长回答说,“但我们必须提醒你,那上面可能有麻烦。”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是说,虽然基 督山现在没有人在上面住,但有时也有走私贩子或海盗躲到那里去,他们是从科西嘉、撒丁或非洲来的。如果我们去那里的事情被举报了,那回到里窝那时,就得被检疫站扣留六天。”
“真倒霉,还有这种事情!六天,上帝创造世界正好用了这么久。朋友们,这也太长了一点吧?”
“但谁会说过您去过那里呢?”
“哦,我当然不会了。”
“我也不会,我也不会!”水手们一起说道。
“那调头去基 督山。”
船长下了命令,船开始拐弯,不久便朝那儿开了过去。弗兰士见一切都弄好了,船帆鼓了起来,水手们各就各位,三个在船头,一个在船尾。“盖太诺,”他对船长说,“你说有海盗去基 督山,但是,我也不是任人摆布的。”
“是,大人,您说的没错。”
“我知道走私贩子是有的,但是,自从阿尔及尔被攻克后,独裁统治被推翻了,海盗恐怕只能在库柏 (库柏(1789-1851),十九世纪初的美国小说家。)和玛里亚特 (玛里亚特(1792-1848),十九世纪初的英国小说家。)的小说中听到了吧?”
“不,您错啦,海盗是有的,正像现在还有一样——原来不都认为教皇利奥十二已经把强盗给消灭了吗?可现在仍有人在罗马城门口进行抢劫。您没有听说过吗?六个月前,法国临时特使在距韦莱特不到五百步的地方被抢劫?”
“哦,这我听说过了。”
“行了,如果您也住在里窝那,您就能经常听到,一条小货船,或一艘小游艇,本来是要到巴斯蒂叶费,拉约港,或契维塔?韦基叶去的,但最后谁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都以为是碰到岩石沉没了。哼,其实他们碰到的是一条狭长的船,六个或者八个人坐在上面,他们常在风高月黑的晚上,去袭击和抢劫这些过往的船只,如同强盗在树林里抢劫一辆马车一样。”
“但是,”裹着衣服躺在船里的弗兰士问,“那些被抢劫的人为什么不向法国、撒丁或者托斯卡纳政府去告他们呢?”
“您问为什么?”船长笑着说。
“对,为什么?”
“因为他们先把船上值钱的东西抢走,放到自己的小船上,然后把船员们绑起来,在每人的脖子上挂一个二十四磅重的铁球,在船底下凿一个大洞,再跳到自己小船上去。过了十分钟,那船便左右摇摆不定,然后晃悠悠地沉下去。最后,轰地发出一声巨响——这是甲板中的空气爆炸了。过了一会儿,排水孔里的水飞速地喷了出来,帆船最后打一个转,便不见了,只是在大海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一切都完蛋了。五分钟以后,只有上帝才知道它会躺在什么地方。现在您知道了吧?”船长大笑道,“为什么没有人去控告,为什么船到不了港了吧?”
如果船长在决定去基 督山之前说了这些话,弗兰士可能会迟疑一下,然而现在已经晚了,他认为后退就是怯懦的表现。有的人不轻易冒险,但一旦有了什么危险,他却能够镇定地对待,他便是这种人。有些人很镇定果敢,他把威胁看成一次奋斗中的对手,仔细地揣摩它,他们知道在有利条件下,便能一下置敌人于死地,他也是那种人。“哼!”他说,“我去了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的所有地方,我曾在爱琴海上航行了两个月,却没有碰见过海盗或强盗。”
“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要改变您的计划,”船长回答说,“因为您问到我,我就这样告诉您,没有别的意思。”
“哦,对,亲爱的盖太诺,你说得非常好,我回忆起来还很有趣味。把船开到基 督山去。”
风很大,这艘小船每小时只能前进六七海里。离目的的地越来越近了。当接近那个岛的时候,那岛好像是突然从水底下冒出来似的,透过傍晚那一点依稀的薄光,可以看到岛上石头一块一块地堆积着,像弹药库里的炸弹一样,绿色的灌木和小树从石头缝里冒出来。那些水手们,看起来似乎很镇静,但心里都有一番戒备,极其谨慎地望着前面一望无际的大海。海面上只能看到几艘渔船和上面的白帆。当离基 督山只有十五海里的时候,太阳落到了科西嘉的后面,科西嘉的群山在天空中显示出鲜明的轮廊。整个基 督山岛像亚达麦斯脱 (亚达麦斯脱传说是好望角的鬼灵,它在这里出现向水手预示着灾难。)一样气势汹汹地望着这条帆船,它把太阳遮住了,山顶被夕阳染得通红。夜幕慢慢降临,赶走了太阳的余辉。最后,太阳出现在山顶的后面,停留了一会儿,山顶如同一座火山的山峰。然后,山峰逐渐完全浸没在黑夜里,像刚才吞没山脚一样,全岛越来越灰暗。半小时后,天完全黑了。
好在船员们走习惯了,熟悉这里的每一块礁石,因为在这样的黑暗之中,弗兰士心里并不镇静。看不到科西嘉了,基 督山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但水手们却如夜猫一样,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继续前进。一个钟头以后,弗兰士觉得从右边能看到一大堆黑压压的东西,但看不清楚是什么,为了怕把一片云当作陆地而引起水手们的笑话,他还是没有作声。猛然间,上面出现了一大片光,陆地可能会像一片云,但这光总不可能是陨星吧。“这片光是什么?”他问。
“别出声!”船长说,“那是火光。”
“你不是说上面没有人烟吗?”
“我说上面没有常住居民,但我也说有时有走私贩藏在那儿。”
“而且还有海盗?”
“而且还有海盗,”船长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正是这个原因,我叫他们绕过了岛,您看,火光已在后面了。”
“但这个火光,”弗兰士说,“我觉得这反而可以使我们放心,如果他不愿意被人发现,他怎么会举火呢?”
“哦,不是这样的,”船长说,“如果在海上您也能到达这个岛,那您便会发现,那火光从侧面或从皮亚诺扎岛都是看不见的,除非您是在海上。”
“那么,你是说,突然有人到了那上面。”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船长回答说,他紧紧盯着那些火光。
“怎么能够确定一下呢?”
“等一会儿您就知道了。”
船长和水手们商量了一下,五分钟后,他们开始行动起来,调转船头。他们把船划向来时的方向,过了几分钟,火光不见了,前方是一片高地,船员们又转过来,使船迅速靠岸,很快离岛只有五十步之遥了。船长把帆解下来,小船静止了,这一系列行动完成得干脆利落,自始至终没人说一句话。
这次前来打猎是船长提议的,因此他主动负起全部责任,四个水手都眼望着他,桨随时准备好了,以便随时可以划走,因为天非常黑,所以这是有可能的。而弗兰士,他特别仔细地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武器。他有两支双铳猎枪和一支马枪,他装上子弹,谨慎地等着。这时候,船长已经把背心和衬衫脱了,勒紧裤带,他本来就赤着脚,因此也就不用脱鞋袜了。然后,他示意了一下大家,叫他们保持安静,便无声无息地滑入海里,轻轻地游向岸边,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只有水中的粼光才能知道他在哪儿。接着水痕也不见了;可见,他上岸了。之后的半小时内,船上没有一点动静,当波浪又出现的时候,他又使劲地游回来了。
“什么事?”大家齐声问道。
“是西班牙走私贩子,”他说,“另外还有两个科西嘉强盗。”
“科西嘉强盗怎么会和西班牙走私贩子一起在这里?”
“唉!”船长带着一种怜悯的口气说,“人总得相互帮助才行。强盗常常被宪兵或骑兵逼得走投无路。嘿,他们突然看到一艘船,而船上恰是我们这样的好人,他们请求帮助。面对这么可怜的人,我们怎么好意思拒绝呢?只好收留他们。安全起见,我们只好驶到海上来。我们没有损失什么,但却救了人命,起码使他们莸得了自由,而他们,有时给我们通一通消息,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安全,使我们能够顺利安全地卸下货物。”
“啊!”弗兰士说,“那你们偶尔也走私了,船长?”
“先生,什么事都要灵活一些,我们也得活命呀。”对方苦笑着说。
“那你认不认识岛上那些人?”
“哦,没错,我们水手如同互济会 (一种秘密团体,以互助为目的,最早发源于石工工会。)会员,凭暗号可以相互认识。”
“如果我们上去,没事吧?”
“根本不用担心!走私贩子不是强盗。”
“但那两个科西嘉强盗呢?”弗兰士说,心中暗暗算计着。
“哦!”船长说,“那也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也是被逼的。”
“为什么呢?”
“他们也实在没有办法,由于一次‘摘了一个瓢儿’,政府却认为他们不该这么做。”
“你说‘摘了一个瓢儿’是什么意思——杀了一个人吗?”弗兰士不断地发问。
“我是指杀了一个仇人,而不是普通的暗杀。”船长回答。
“行,”弗兰士说,“那我们去请他们帮帮忙吧,不知道他们答不答应。”
“他们一定会答应的。”
“他们一共多少人?”
“四个,另外加上那两个强盗,一共六个。”
“和我们一样,如果他们要找麻烦,那我们也不用怕,我最后请求一次,我们划船到基 督山去吧。”
“是,但我们得预防一下,请等一会儿。”
“尽管做吧,应该具有涅斯托 (古希腊特洛亚战争时代的部族首领,事见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精明和尤利西斯的谨慎,我不仅赞同,而且鼓励这么做。”
“好,别说话。”船长说。
大家都默不作声了。像弗兰士头脑那么精明的人,知道自己所处的环境。他现在一个人和这些水手在一起,他们并不相识,水手们并没有义务去保护他,水手们知道他身上有几千法郎;他们多次查看他的武器,都非常漂亮,谈论的时候带着嫉妒。另外,马上就要上岸了,除了他们,再没有可以依靠的了,这个岛的名字有一种宗教的意味,但弗兰士觉得,除了能够供走私犯和海盗躲藏以外,再也得不到其它保护了。帆船被凿的那件事,白天里是想象不到的,但夜里是极有可能的。面对这两重危险,他必须时刻监督着船员,也不敢离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