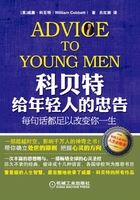第十六章 一个意大利的知识分子 (1)
邓蒂斯兴奋得一下子拥抱住了这个渴望已久的伙伴,然后拖他至窗口,借着从窗户射进的微弱灯光仔细观察那个人的面貌。此人身材瘦小,头发灰白,可能因为苦虑交迫的结果,而并非是年龄所致,眼窝深陷,但炯炯有神,灰色的长眉毛几乎掩没了双眼,一丛长而黑的胡须垂到了胸前,脸色疲惫而且充满了皱纹。他的轮廊显示其个性十分坚毅,一眼望去,便知是个脑力劳动者。他额头上有大滴的汗珠淌下来,衣服破破烂烂的,几乎衣不蔽体,无法想象衣服原来的样子。
此人年龄大概有六十至六十五岁,可从他生气勃勃的行动判断:他的年龄多半是由于长期的监狱生活所致,而并非仅仅因为岁月的不断流逝。他显然被这个青年的热情感动了,他早已冷却的心灵也似乎受这个青年的感染而重新温暖激奋。他对青年的热情欢迎表示诚意的感谢,尽管他十分失望,因为他预期得到自由的想法一下子落了空,如今接待他的是另外的一间黑牢。
“我们来观察一下,”他说,“能不能除掉我进来的痕迹。我们一定要保守秘密,万不可让你的看守了解一丝一毫的情况。”他向洞口走去,蹲下来,十分轻松地举起那块大石头,又把它塞在了原来的位置;说道:
“你难道没有工具吗?你看你挖这块石头太大意了。”
“怎么,你难道有工具吗?”邓蒂斯几乎惊奇地大叫起来。
“对,我自己研制了几样,现在缺少的仅仅是一把锉刀而已,其他的包括凿子、钳子和锤子之类的都有。”
“噢,让我欣赏一下你这些发明创造!”
“好,这是我的凿子。”他边说边拿了出来,这是一片尖利结实的装有木棒柄的铁块。
“你是用什么东西制成的?”邓蒂斯问。
“从我床子卸下来的铁楔子,我挖这条洞时,这个工具帮了大忙,大约挖了五十英尺吧。”
“五十英尺!”邓蒂斯吃惊地大叫。
“小心别大声谈话,小伙子,别大声!在这样的监狱中,经常有站在监牢外偷听犯人们谈话的人。”
“可他们都清楚我孤身一人。”
“那也同样。”
“那你挖了五十英尺的洞才到这儿吗?”
“对,那几乎就是我俩房间之间的距离吧,令人遗憾的是我转弯时没有设计好,因为没有必须的几何仪器计算我的草图比例。按图上的比例,仅仅需要挖四十英尺的弧线就够了,可我却足足多挖了十英尺。我已对你说过,我原打算挖到外墙,挖穿之后跳进大海中,可是我却沿着你房间对面的走廊挖,挖到再往底下一点儿。我等于白白地干了一场,因为这个走廊通向满是士兵的天井。”
“对,”邓蒂斯说,“可你所说的走廊只是我房间的一面墙,还有另外三面呢,这三面的情况你了解吗?”
“这一面的筑成靠的是实心岩石,需要十个有丰富经验的矿工,带上必需的工具,花费几年的功夫才能把它给挖穿。另外的一面相连于堡长住宅的下部,即使挖了过去,也仅仅能钻进另外一间地牢中,肯定还是被捉住。第四面,即剩下的一面——稍等,它朝何方向呢?”
这一面有一个开着的窗口,能够引起好奇心,微弱的灯光从这面射了进来。窗洞越往外越小,开口时连一个小孩子都无法从中钻出,何况还有三条铁栅栏拦住呢,因此看守性格再多疑也十分放心,他清楚犯人无法从这个地方逃去的。“爬上去。”那怪客观察了一阵子,把桌子拖到窗口对邓蒂斯说。
青年奉命爬了上去,他猜测着那个怪客的意思,把背死死地贴住墙壁,把双手伸了出来。邓蒂斯到现在只知道那怪客的号码是二十七号,其他一概不知,从外表的年龄判断,他不可能这样敏捷。他一下子跳上去,如同一只猫或一条蜥蜴一样敏捷地拉住邓蒂斯的手,又爬上他的肩头,然后,弯下腰——由于天花板使他无法伸直身体——他十分别扭地从窗口的栅栏间塞进去,以便上上下下看个究竟。
停了一会儿,他迅速撤回头,说:“我估计得没错!”于是和刚才一样敏捷地跃下来,从桌子再跳回地面上。
“怎么了!”青年用一种焦急的口气问道,也从桌子上跳了下来。
那个犯人考虑了一下。“对,”他开口说道,“对,没错。你的牢房的这面看出去有一条露天的走廊,巡逻的兵来回在那里走动,并且有日夜值班的哨兵。”
“你敢保证吗?”
“那是自然。我已经发现了士兵的帽子和毛瑟枪的枪管子,我因此才迅速缩回头,让他们看见就麻烦了!”
“那我们将采取什么办法呢?”邓蒂斯问。
“如今你明白从你的黑牢中逃出是没有办法的事了吧?”
“那么?”青年口气充满了疑惑。
“那么,我们不得不服从上帝的意志!”那个犯人回答,并且是一字一顿的,听由天命的神色也在充满忧虑的脸上布满。邓蒂斯盯着这个犯人,他那么长时间热情培养的希望一下子如同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邓蒂斯脸上充满着惊异和钦佩的神情。
“我求你了,告诉我你的名字吧。”他终于开口说了。
“太好了,”那个怪客回答道,“可喜的是你对我还存有好奇之心,因为如今我已经无法帮助你了。”
“你能够给我安慰和鼓励,——因为据我判断,你是强者当中最强的人。”
老犯人微笑了一下,笑容当中带着凄然的神色。“那么你听好,”他说,“我是法利亚长老,在一八一一年我被关到这个伊夫堡监狱中。 这之前,我曾经在费尼斯德里监狱关了整整三年。一八一一年,我从皮埃蒙特给转押至法国。那时,拿破仑好像一帆风顺,屡屡得手,连摇蓝中的儿子都给封成了罗马国王。我实在没有预料到你说的转变。没有想到四年之后,这个庞大的强国竟然崩溃了。那么现在谁统治法国呢——是不是拿破仑二世?”
“不是的,现在是路易十八国王。”
“是路易十六的兄弟!真是太出乎意料了!什么原因导致苍天使赫赫有名的人贬出,让一个虚弱无能的人当政呢?”
邓蒂斯被他吸引去了所有的注意力,这个人太怪异了,他只顾想着别人的不幸,连自己本人都给忘了。
“可英国也何尝不是如此?”他继续说道,“查理一世死了之后,有克伦威尔,再后是查理二世、詹姆士二世,詹姆士二世把他的一个外甥、亲戚之类的作为他的继承人,他自任为国王的总监管,随后对人民妥协了,直至制定出一部宪法,获得了自由,你能够享受得到的,年轻人,”他看着邓蒂斯,像一位预言家一般,兴奋地盯着邓蒂斯,“对,你如此年轻,肯定能够享受得到的。”
“对,只要有一天我能够活着出去!”
“对,”法利亚长老说,“作为犯人,有时候我们时常不记得这些,甚至当我想象我在牢墙外时,我都以为是真的呢。”
“你为什么被捕呢?”
“是在一八○七年,我给拿破仑出谋划策,帮助他一八一一年实现。由于我和马基维里一样想改变一下意大利的政治局势,我不想让它分裂成诸侯国,每个诸侯国都有一个或无能或残暴的国王。我想让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团结的强壮的帝国。可最终结果是,我错认了一个头戴王冠的家伙作为凯撒?布琪亚,他假装接受了我的建议,事实上把我出卖了。亚历山大六世和克力门七世也曾有过类似的谋划,但不可能取得胜利,因为他们不重视这样的计划,认为它不可能成功,而拿破仑又无法完成他的圣命。意大利注定要遭厄运。”老犯人的头无力地垂在胸前,充满了极度的沮丧。
邓蒂斯听着这些不可思议的话,搞不清楚为何有人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干这些事情。很正确,他多少有点了解拿破仑,由于他曾经见过他,和他进行过交谈,可是克力门七世和亚历山大六世,他却从未听闻。
“你难道就是那个有病的长老?”邓蒂斯问他道,他开始相信看守以及伊夫堡监狱所有人的看法了。
“是一位疯子,你是这个意思,对吗?”
“我可不想这样说。”邓蒂斯笑了笑说。
“对,我承认,”法利亚苦笑着重新说起来,“我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伊夫堡可怜的疯子,许多年中,他们都把我作为笑料谈天,让来视察的人参观我,说我如何颠三倒四,并且,如果有可能派一些孩子们来参观的话,肯定会让我给他们耍把戏。”
邓蒂斯长时间地呆立着,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又过了很久,他终于开了口:“那么你难道放弃所有的希望了吗?”
“已经不可能逃走了,并且现在看来,尝试那上帝不让做的事情对他太不尊敬了。”
“不,千万不要灰心。你首次试验就想着成功,那岂不太容易吗?我们再试一次,在别的地方打个一个逃出去的洞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