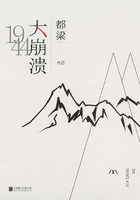第十一章 科西嘉岛的逆贼头目 (1)
一见警务部长的焦急神情,国王就一下子推开了他趴着写字的桌子。
“怎么回事,男爵阁下?”他禁不住喊了起来,“情况是不是十分不妙。你是不是十分犹豫不决,难道和勃拉卡斯阁下说的又经维尔福先生所证实的一模一样吗?”
勃拉卡斯公爵连忙走向男爵,他那惊慌失措的样子一下子把这个元老大臣的好心情吓到了九霄云外。说句实在话,在这个场合,他倒希望是他本人受到屈辱,被警务部长所战胜。
“陛下,我,我——”男爵语无伦次地说。
“到底怎么啦?”路易十八国王问道。警务部长绝望透顶,仿佛要扑倒在路易十八脚下长跪不起,国王向后撤了撤身,眉头紧锁着。
“你倒是快说呀?”国王说。
“噢,陛下,太令人恐怖了,我罪该万死,罪不可恕!”
“阁下,”国王不耐烦了,”我命令你快说!”
“呃,陛下,我说,我说,波拿巴已经于二月二十六日离开了爱尔巴岛,并于三月一日登陆上岸。”
“在什么地方上岸的,是在意大利吗?”国王急不可待地问。
“不,不,是在法国的一个小港口,陛下,就是昂蒂布附近,靠近琪恩湾。”
“那逆贼波拿巴三月一日就在离巴黎才七百五十哩的琪恩湾昂蒂布上岸,为什么今天才到这儿报告!哦,先生,快说这是个捏造的报告,是万万不可能的,你难道发疯了吗?”
“不,没有,陛下,确确实实是真的!”
路易十八表现出无法形容的愤怒和慌张,可还企图强作镇定,仿佛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同时击中了他的身心。
“竟然在法兰西!”他歇斯底里地叫喊,“他竟然已经在法兰西了!那他们看来肯定没有看牢他。谁了解底细,到底谁和他们勾结在一块的呢?快告诉我!”
“噢,陛下!”勃拉卡斯公爵大吃一惊,劝说国王说,“邓德黎肯定不是一个叛国者!陛下,我们都太盲目了,警务部长也许也和我们一样呢,事情可能就是这样。”
“可是——”维尔福说了两个字,又马上闭上了嘴,“请您原谅,陛下,”他边说边弯腰鞠躬,“我的极大的不可控制的热情使我情不自禁说了那些话,陛下请赐恩不要加罪于我?”
“尽管大胆地说,维尔福先生,”路易十八回答说,“只有你把这个天大的危险提前让我得知了,现在我洗耳恭听您的解救险情的办法!”
“陛下,”维尔福说,“南方的人十分痛恨逆贼波拿巴,让我看来,如果他企图从那儿起义,肯定会引起郎格多克省和普罗旺斯两省的人民的极大不满和反抗。”
“这是一定的,”部长答复,“不过他却沿着加普和锡斯特龙逼进巴黎。”
“前进!他竟然一直在前进!”路易十八说,“你说他正在向巴黎进军?”
警务部长默认了这个可怕的事实。
“陀菲内省呢,阁下?”国王向维尔福法官发问,“你认为那里也会如同普罗旺斯省一样吗?”
“陛下,很不幸,我不得不告诉陛下一件难以接受的残酷事实:陀菲内的民情糟透了,无法与普罗旺斯或郎格多克相比,因为那里有很多拿破仑的党羽分子。”
“那么,”路易十八压低声音说,“他的情报千真万确了。他大概带了多少兵马?”
“我不清楚,陛下。”警务部长回答说。
“怎么?你连这个都不清楚?你是不是昏过了头?事情到了这份儿上,你还不赶快去打探新的消息?你还以为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琐碎小事吗?”他边说,边露出一个极其勉强的笑容。
“陛下,这如何能够打探得到?快报上只提供说逆贼已经登陆以及走哪条路线前进。”
“你是如何得到这个消息的?”国王问道。
部长低下了头,脸上出现了冲血的颜色,低声嘀咕着,“是通过信号送过来的,陛下。”
路易十八又向前走了一步,如同拿破仑一般把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哦,是这样,”他脸色气得发紫地叫喊,“七国联合部队才推翻了那个逆贼,经过二十五年的流亡生活,上天助我,使我得以重返父王的王位。这些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研究,探索和分析我所应该负责任的法兰西的民情国事,当我一切都如愿以偿的时候,我的权力却遭受了攻击,并粉碎了我的一切,如同粉末一般!”
“陛下,这是一场灾难!”部长小声说道,他冥冥之中感觉这是一种压力,虽然命运之神看来十分正常,可却可以击垮任何一个人。
“看起来,敌人批评我们的话都十分正确: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却忘记不了任何东西!如果我也遭受国人的唾弃,则我还能够安慰自我,可既然大家都让我当国王,他们就应该拥护我甚于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与他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我当国王之前,他们什么都不是的,在我倒台之后,他们也将什么都不是,——而我的生死存亡竟寄托在他们身上!噢,阁下说得对极了,这是命中注定的灾难!”
一番自我嘲讽之后,部长低垂着脑袋。勃拉卡斯公爵只是不住地擦自己额间的冷汗。维尔福心里不免暗自发笑,由于他觉得此刻他的地位已得到快速的提升。
“难道国家要灭亡吗!”国王路易十八又喃喃自语,好像他已经洞察了王国的前途命运。“灭亡就灭亡吧,毕竟只是快报上才明白将要亡国的消息!噢!我宁愿被绑上我的王兄路易十六的断头台也不想如此地离开杜伊勒里宫!太可笑了,阁下!你怎么会不清楚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呢!这些你原本应该十分清楚的!”
“陛下,陛下,”部长吞吞吐吐地说,“请陛下饶恕臣下的罪——”
“你过来,亲爱的维尔福先生,”国王招呼那个愣在那里屏息倾听这番决定法兰西命运的谈话的人,“快过来,对部长说清楚,为什么他不知道的有的人就能够一清二楚。”
“陛下,逆贼把消息保守得特别严,根本无法得知详细的情报!”
“根本无法得知!好,这几个字眼太了不起了,阁下,太令人不幸了,我已考虑过了,天下竟然确实有如此伟大的字和人物。如此大的机关,如此多的职员和密探,如此多的达到一百五十万法郎的活动经费,都干什么去了?连离法国海岸一百八十哩外的情况都不可得知,你这个部长是干什么吃的?好,现在你听一听这位先生的,他可是什么都没有,仅仅是一个法官而已,他却了解比一个偌大警务部的人还多的情况。你设想一下,如果他拥有你的条件,还有什么不能知道的吗?如果那样,我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警务部长用一种仇恨的眼神扫了一眼维尔福,而后者却低着头,带着一副胜利者的谦逊的神情。
“我指的并不是你,勃拉卡斯先生,”路易十八继续说,“因为虽然您没能知道那么多,可您却十分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怀疑,这一点也十分难能可贵。如果是另外一个人,肯定会认为维尔福的发现无关紧要,不过是想升官罢了。”
显然,这番话针对的是一个小时前警务部长的那万分自信的言论,维尔福十分了解国王的言行所指。如果是别人,肯定会被一片赞誉所陶醉,飘飘然不知其所以然,可他十分担心自己为警务部长所忌恨,尽管他已经发现邓德黎的失败已成为定局。而事实确实是这样,这个警务部长在其掌权的时候尽管无法知道拿破仑的秘密,可凭他临死的反抗,却有可能把他维尔福的秘密给戳穿,因此维尔福并不落井下石,而是要救这个将要倒霉的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