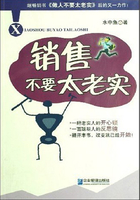第十章 书 斋 (1)
维尔福是怎样昼夜不停地去往巴黎的,我们先不去管他,反正他窜过两三座宫殿,潜入了杜伊勒里宫的书斋里;这个书斋有个拱形的窗门,十分著名,由于不但往昔的拿破仑和路易十八爱在这里处理国家大事,而且现在的路易?菲力浦也是这样。
书斋之中,国王路易十八正在一张胡桃木制的桌子前坐着,这张桌子是他从赫德威尔带到这里来,他对它喜欢备至。这很平常,由于大人物都有些怪癖,而路易十八的癖好正是这个。他正在心不在焉地听一个人讲话,这个人大约有五十岁出头,花白的头发,风度翩翩,颇有贵族的样子。而路易十八正在一卷格里夫斯版的贺拉斯诗集上圈圈点点,也许国王正是从这本书上获得了聪明博学的见解。
“您继续说,先生。”国王亲切地说。
“我感到心神不宁,陛下。”
“是吗?您难道真的梦见了七只肥牛和七只瘦牛?”
“并非这样,陛下,那个梦仅仅昭示我们会有七年丰收和七年的灾荒而已,而如果遇到您这样的旷古明君,灾荒又算得了什么?”
“那还有其它令人担心的祸害吗,亲爱的勃拉卡斯先生?”
“陛下,种种迹象表明,现在有一场大风暴正在我国的南部酝酿着。”
“哦,先生,”路易十八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回答到,“您肯定搞错了,我了解的情况正好相反,南方的天气一向很好。”路易十八作为一个国王也会时常开个令人出其不意的玩笑。
“陛下,”公爵勃拉卡斯继续说,“为了使作为臣仆的心安,您是否可以派几个忠实的钦差到郎格多克、普罗旺斯和陀菲内视察一下,回来汇报一个令人放心的消息?”
“我们低声唱歌。”国王答非所问,继续在那本书上圈圈点点。
“陛下,”朝臣笑着回答,表明他好像也明白为引证诗歌中的话,“陛下可以相信全体法兰西人民的忠心,但是我所担心的某种想起义的企图也错不了。”
“您指的是谁?”
“波拿巴或者他的党羽们。”
“勃拉卡斯公爵,”国王路易十八说,“您说的这种情况吓得我几乎无法工作了。”
“可是陛下您的若无其事的样子更加令我担心不已。”
“稍等一下,亲爱的公爵先生,——我在《当牧童跟着走的时候》这首诗上看到一个十分有趣的注解,——再稍等几分钟,我就详细听您讲是怎么回事。”
谈话被打断了,这个时候,路易十八用极小的字在他的贺拉斯诗集书边的空白处记下了他的灵感,然后带着一副洋洋自得的神色看着公爵,似乎他想向众人炫耀他的独创的见解。他说:“继续说,亲爱的公爵,接着往下说,这次我在认真听着。”
“陛下,”勃拉卡斯说,他十分想独吞维尔福的功劳,“我必须明确告诉您,这个可能不仅仅是谣言。我手下有一个人很聪明,并且我也十分信任他,我派他到南方打探了那里的情况。”公爵说这些的时候吞吞吐吐,“他刚才十万火急地告诉了我威胁到您安全的大危机,因此我赶紧来告诉您这件事。”
“最大的危机是半愚半智。”国王还在那本书上写注解。
“陛下不想听臣下诉说了吗?”
“不是,公爵先生,您不妨伸手寻找一下。”
“找什么东西?”
“随便找什么都行,在您的左边。”
“是这里吗,陛下?”
“我说的是左边,您怎么摸右边呢。我说的是我的左边,——对,就是那里,您能够发现警务部长昨天的报告。哟,邓德黎阁下本人来到了,我预料得真准。”侍从官报了名之后,邓德黎就走进了书斋。
“快过来,”路易十八笑了笑,“快过来,亲爱的男爵,告诉他你所了解的一切,特别是关于波拿巴阁下最近的情况。一切都不要隐瞒,不管它有多么危言耸听。爱尔巴岛到底是不是一个火山,会不会爆发恐怖的战争,您尽管说,战争,恐怖的战争!”邓德黎把双手交叉在身后,十分严肃地靠在椅子背上,说:
“昨天我呈上来的报告陛下您看了吗?”
“早就翻阅过了,你给公爵再讲一下,他还没有找到那份报告,特别是造反者在爱尔巴岛上的所作所为,一定要尽可能详细地告之。”
“阁下,”男爵对公爵严肃地说,“陛下全部的臣仆听到我们从爱尔巴岛得来的情况都欢呼雀跃。波拿巴,”邓德黎说着停顿了一下,看了看路易十八,他正在记笔记,头连抬都没抬,“波拿巴,”男爵继续说,“几乎就要闷死了,只有每天在隆江港看矿工们劳动。”
“并且时而搔一搔痒。”国王不失时机加了一句。
“搔痒?”公爵问道,“陛下您是什么意思呢?”
“没错,公爵。您难道忘了吗,这个英雄加伟人、兼半仙得了一种顽癣,每天使他痒得快要发了疯。”
“并且,公爵阁下,”男爵又接着说到,“我们甚至可以确定,要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丧心病狂。”
“您说他快要疯了吗?”
“没错,只要有一定程度的发疯,就表明他头脑不清醒了。他时而痛哭,时而哈哈大笑,有时整日在海边捡石片打水漂,如果石片一连在水面上连续漂五六下时,他就高兴得乱蹦乱跳,像个小孩子一样。您也肯定同意,这些都表明是脑力衰弱的征兆。”
“但也可能是智慧的征兆,男爵阁下,”路易十八不完全同意他的说法,“你难道忘了古代那些伟大的船长们不也以打水漂为乐吗,这都在普罗塔克的《施底奥?阿菲力加弩传》上写着的。”
勃拉卡斯公爵对国王和部长的盲目乐观的态度深表忧虑。可是维尔福也没有告之全部的秘密,怕功劳被他全占了,但从仅有的一点消息来看,正是令他坐卧不安的原因。
“喂,邓德黎,”路易十八说,“这位公爵还没有相信咱们的推断,再告诉他一点逆贼波拿巴的近况。”
这位男爵兼警务部长又鞠了一躬表示遵命行事。
“逆贼现在怎么啦?”公爵口中念念有词,而眼睛只是盯着如同维吉尔诗中的一唱一答的牧童一般的国王和邓德黎,“逆贼难道有所转变?”
“对极啦,亲爱的公爵先生。”
“他变成什么样啦?”
“变得遵守规矩了,男爵,详细讲给他听。”
“哦,是这么一回事!公爵阁下,”部长十分严肃地说,仿佛他是世界上最严肃的人,“拿破仑时下进行了一次考察,他的几个旧时的臣下表示想重返故国,他严厉地训斥他们,让他们‘服从国王的命令。’这是拿破仑亲口所言,这一点我可以作保证,公爵阁下。”
“喂,公爵先生,你是怎么看的?”国王十分得意地问,停下了手头的工作。
“陛下,我和警务部长两人当中肯定有一个人受骗了,可他是不大可能受骗的,因此可能是我受了愚弄。但是,亲爱的陛下,如果我能够提一点意见的话,陛下应该赐给刚才我给你提及的那个人荣誉。”
“我十分乐意,公爵。只要您同意,您让我接见谁就可以,惟一的条件是他手中没有枪。部长阁下,你还有最近的报告吗?这个是二月二十日的,而如今已经是三月三日了。”
“暂时还没有,陛下,不瞒您说,我也正朝思暮想地等待着呢,可能在我今天上午我离开这会儿,就会有人呈上新的报告。”
“那赶快回去看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哦哦,”路易十八又说,“那就赶快造一个,你不总是这么办吗?”说着哈哈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