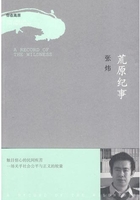第5章莫里斯?林代是怎样一个人
莫里斯?林代匆匆忙忙穿上衣服,去勒拜尔梯埃街上的队部,他是该部的书记,读者已经知晓了。现在,让我们试着为大家讲述一下此人的先祖吧,他本人则是出于有力而豁达的天性,凭着冲动,登上这个戏剧舞台的。
头天晚间,他在回答陌生女人的问题时,他说他名叫莫里斯?林代,家在鲁尔街上,当然,这个年轻人说得不差分毫。他还可以补充说,他是个有着半贵族血统的孩子,出生于法官之家。两百年来,他的先祖都以议会反对派著称,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便是莫莱(莫莱(1781—1855):法国保皇党政治家。)和莫贝乌(莫贝乌(1714—1792):1768年曾任法国首相。)。他的先父,老好人林代,其一生都在为反对专 制制度而奔走呼号,直到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落入庶民之手,他看见专 制主义被军事独 裁所取代,忧心忡忡,惊恐而死,留下一遗孤,经济上独立,感情上倾向共和。
这件石破天惊的事情发生后不久便爆发了法国大革 命,其时,莫里斯正当英姿勃勃、成熟好斗之年,接受的是共和教育,加之受革 命俱乐部的熏陶,读了许多时兴的小册子,共和思想更加牢固。只有上帝才知道,莫里斯一共读了多少这类的书。他从理性上轻蔑社会特权,从哲学上主张社会有机的平衡,对整个贵族阶层绝对的否定,倒不是针对某个人,而对往昔爱作不偏不倚的评价,对任何新思想都有热情,对庶民百姓同情的同时又掺杂了他那贵族化的感情倾向,这些构成了这个故事主人公的道德特征,他不是我们挑选出来的,而是我们读的有关报纸给我们推荐出来的。
体形上,莫里斯?林代身高五英尺八英寸(约1米85的高度),二十五六岁,像海格立斯(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英雄,力大无比。)那样结实,具有法国人的典型美,又有祖先法兰克族人的特征:宽额、蓝眼睛、栗色的卷发、粉红的腮帮和洁白的牙齿。
我们描绘了此人的外形之后,轮到叙述这个公民的立场了。
莫里斯不能说富裕,但至少经济上能独立:他的姓氏受人尊敬,却更具有大众化倾向;莫里斯接受的是平民教育,而他的原则则比他所受的教育更加平民化;莫里斯就凭这些优势,当上了一群年轻的小资产爱国者团体的头头,在无套裤汉当中,也许他是温和派,而在国民卫队队员之间,他有点公子哥儿味,然而他得到了无套裤汉的宽容,因为他能把最结实的粗短木棍像细嫩的芦苇那样折断;他的高雅又受到队员们的谅解,因为有谁胆敢放肆地盯着莫里斯瞧,他能在二十步开外一拳打在此人眉心处,把他击倒。
莫里斯凭着他的体魄,他的道德观,和他的全部公民意识参加过攻占巴士底狱、远征凡尔赛宫;他在8月10日(指1792年8月10日,那天巴黎起义公社囚禁了法王路易十六和他的眷属。)像猛狮那样战斗过,而在这永远难忘的日子里,得为他讨句公道话,他杀死爱国者与杀死瑞士人一样多,因为他既不能容忍穿短上衣、滥杀无辜的刽子手,也不能放过穿红上衣的共和国敌人。
就是他,为了劝告宫堡里的卫士投降,也为了避免流血,投身于一个巴黎炮手行将点火的炮口之中;就是他,在五十个瑞士雇佣军以及同样数目被困的世家子弟的枪林弹雨之中,最先越窗进入罗浮宫;当他那柄可怕的长剑刺穿了十来个穿制服的卫兵之后,他才看见投降的信号,但却又看见他的朋友还在任意砍杀已经弃械投降伸出哀求的手乞求活命的俘虏,于是,他又愤怒地去宰杀他的朋友,这个举动使他成了声名远扬、无愧于罗马和希腊伟大时代的英雄。
战争爆发后,莫里斯入伍上了前线。他作为中尉,带领一千五百名城市新自愿兵去抗击入侵者,这支队伍每天新增加一千五百人。
他参加的首次战役,也就是在杰马普(比利时一村庄。1792年11月6日,法军在这里大败奥地利军队。此后,比利时归并法国。),他中了一弹,子弹穿透了他背部铁般硬的肌肉,直顶到骨脊上。人民代表认识莫里斯,把他送到巴黎治疗。整整一个月,莫里斯发着高烧,疼痛得在床上打滚。到了一月间,他康复了,虽然不是名义上,但在实际上已成了温泉俱乐部的头头,也就是管辖着巴黎中产阶级阶层里百把个年轻人。他们武装起来,随时准备打击支持贵族暴君的任何企图。更有甚者,处死国王的那天,他因愤怒而紧锁眉头,睁着眼睛,脸上苍白,内心被理念上的仇恨和肉体上的怜悯双重感情所折磨,手握长剑,观看了这个场面;当圣路易的儿子(即法王路易十六)的头颅被斩,灵魂升天时,在人群中也许只有他一人沉默不语,只是等到这颗脑袋落地之后,他才向苍天举起他那柄令人畏惧的长剑,而当他的所有朋友高呼“自由万岁”时他们没有发觉,这一次出现了例外,莫里斯的声音没有参与到他们的口号中去。
就是这么一个人,在3月11日的早晨,向勤拜尔梯埃街走去,我们的故事将要对他暴风雨般的一生作出更多的介绍,勾勒出更多的细节,那是他的劫数,他在那个时代命中注定该如此。
十点钟光景,莫里斯来到队部,他是部里的书记。
群情激昂。人们正在酝酿通过向国民公会递交一篇宣言,意在镇压吉伦特党人的阴谋。大家都焦急地等着莫里斯。
事情涉及到红屋骑士返回巴黎,这是这个胆大妄为的叛乱者第二次回来了,他本人也知道到处在悬赏着他的头颅。大家把他返回与头天晚上在寺院监狱发生的事联系在一起,无不对叛徒和贵族表示出憎恶和愤怒。
然而,与大家期望相反,莫里斯有气无力、默不作声地飞快起草宣言,用三个小时做完了这件差事后,问会议是否结束,得到肯定答复之后,他就拿起帽子,出了门,向圣-奥诺雷街走去。
到了那里,他觉得巴黎焕然一新了。他又看到了公鸡街的一角,在那儿,头天夜里,那个美丽的陌生女人在自愿兵手中挣扎的情景犹如眼前。这时,他把目光从公鸡街溜到了玛丽桥,这一条路是他与她一起走过的,那时,他们每遇到巡逻队阻拦就得停下,他重温着他俩的对话,仿佛那些地方保留着他们对话的回声似的。不过,时值午后一时,一路上炽烈的阳光照射着他,使他每走一步都对夜晚的回忆更加鲜明。
莫里斯穿过一座座桥,很快就来到了维克多街,当时人们是这么称呼这座桥的。
“可怜的女人啊!”莫里斯喃喃地说道,“她怎么没想到夜晚也就是十二个钟点,她的秘密也许再也过不了一夜了。在明媚的阳光下,我要重新找到她溜进去的那扇门,说不定我在某个窗口还能看见她的倩影哩。”
于是,他走进圣-雅克老街,站定在头天晚上陌生女人让他站定的地方。他居然闭上了眼睛,可怜的疯子啊!刹那间他期望着昨夜的吻会再次灼烫他的唇。然而,他得到的只是回忆!不错,回忆还在灼烫着他。
莫里斯又睁开眼睛,看见了两条小巷,一条在他左边,一条在他右边。巷子泥泞,坑坑洼洼,栏栅横七竖八,小河穿越其中,上面架起了一座座小桥。那里还有一些木梁拱廊,一些死角以及许多破破烂烂的门扉。一切都是粗制滥造,破败不堪,丑陋无比。还有些小园子混杂其间,有的隔一道栏栅,有的支起了丛丛绿篱,有的干脆用墙封死;还有一些兽皮在敞篷下晾着,散发出皮革的臭味,让人恶心。莫里斯寻找着,用了两个小时揣摩着。什么也没发现,什么也猜测不着。有上十次,他来回徘徊以辨别方向,但所尽的努力一无所获,所有的寻找毫无结果。那少妇的足迹已被迷雾和淫雨消抹了。
“算了吧,”莫里斯心里想道,“算我在做梦。这个垃圾场如作为昨夜那位仙女的隐居地,她是一分钟也呆不下去的。”
这个大无畏的共和分子的心中的诗,与他朋友的四言爱情短诗一样真实,且别有韵味,因为他又回到了他的梦幻之中,以免使映照在那陌生女人顶上的光环黯然失色。他回家时确实灰心丧气了。
“别了,神秘的美人儿!’他说道,“她把我当成了傻瓜或是孩子。倘若她真的住在这里,她会带我来吗?不会!她只是路过一下,如同天鹅掠过一片污秽的沼泽地;又犹如小鸟在天空一闪而过,她的芳踪也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