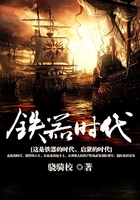第4章时代的风尚 (2)
“什么!像别人那样说话!可我比别人说得好呀,我说话如同德莫斯梯埃公民(德莫斯梯埃(1760—1801):法国作家。)用散文和诗的语言。说到诗,亲爱的,我知道有一位叫埃米莉的女人,她觉得我的诗不坏。唉,还是谈你的诗吧。”
“谈我的诗?”
“不,谈你的埃米莉。”
“行啦!行啦!你的羚羊变成了母虎,并向你露出利齿,你恼火了,但又爱上了。”
“我爱上了!”莫里斯摇摇头说道。
“是呀,我爱上了。
“请别再守口如瓶,
这一击来自西代尔岛(希腊爱奥尼亚群岛中最南部的一个岛屿,在文学艺术上以爱情享乐的胜地而著称。)
不偏不倚打中心脏,
比咆哮的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主神。)更加糟糕。”
“洛兰,”莫里斯边说边拿起床头柜上一把带孔钥匙作武器,“我郑重对你说,你不要再吟一句我厌恶的诗句了。”
“那么咱俩说说政治吧。再说,我也为此而来。你知道最新消息吗?”
“我只听说卡贝寡妇(这里指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自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之后,她被关进监狱。)想越狱。”
“呸!这不算回事。”
“那么还有什么?”
“那个尽人皆知的红屋骑士到巴黎来了。”
“真的吗?”莫里斯惊呼着,半支起身子。
“就是他。”
“他何时进城的?”
“昨天晚上。”
“怎么回事?”
“一个男人化装成国民卫队的队员,另一个女人看起来像贵族,化装成平民百姓,到关卡去给他送衣服,不一会儿,他俩挽着手臂进城来。直到他俩已过关卡后,哨兵才生疑。因为早先他是看见那个女人拎着一个包裹走出去的,却勾住一个军人模样的人返回来,这太邪乎了,于是他发出警报,一伙人去追赶他俩。他俩跑到圣-奥诺雷街的一家旅馆,旅馆门像着魔似地及时开启,他俩就此从中消失。这家旅馆另有一道门开向香榭丽舍大街,得啦!红屋骑士与他的女伴逃得无影无踪了。这下,我们可以把旅馆毁掉,可以把其主人绞死,但阻止不了红屋骑士重新干他的阴谋勾当,四个月前他首次失利,昨天是第二次,也还是没成功。”
“他没被捕吗?”莫里斯问道。
“哼!是啊,要逮捕普洛代(普洛代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神,他会变形,只有在午睡时才能抓住他。)吗,亲爱的,逮捕普洛代吗?你知道阿里斯梯特(阿里斯梯特,生卒不详,希腊神话作家。普洛代是他笔下的一个人物。)花了多大的劲才达到目的的。”
接着,洛兰用拉丁文背诵了维吉尔(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罗马最伟大的诗人。不朽著作《埃涅阿斯记》是他的主要成就。)的一句诗。
“当心点吧。”莫里斯说着把钥匙放在他的嘴前晃晃。
“你也小心点吧,咳!因为这次不是我让你生厌,而是维吉尔。”
“不错,只要你不把它翻译出来,我就无话可说啦。嗯,再谈谈红屋骑士吧。”
“好吧。我们得承认他是一个堂堂男子汉。”
“事实是,要有很大勇气才称得上堂堂男子汉的。”
“或是伟大的爱情。”
“你相信骑士爱上王后的传说么?”
“我不相信,但我像大家一样也随口说说而已。既然她使许多人堕入了情网,即便她勾引了红屋骑士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听说,她不是已经俘获了巴尔纳夫(巴尔纳夫(1761—1793):法国大革命中因接近王室而被斩首。)了吗?”
“管不了那么多了。骑士在寺院监狱里总有内线吧。”
“有可能。
“爱情摧毁铁栏
遑论区区门闩。”
“洛兰!诗瘾又来了!”
“哦!是这样。”
“这么说,你也相信这件事啦?”
“为什么不?”
“因为在你看来,王后该有二百个情人啦。”
“二百、三百、四百。她够美的,不足为奇。我没说她个个都爱,但他们却个个爱她。世人都看得见太阳,而太阳不必看见世人。”
“那么,你说那个红屋骑士……”
“我说,此时我们正在全力追捕他,倘若他真能从共和国警探的手中溜掉,他也真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了。”
“公社在处理这件事上有什么措施呢?”
“公社将颁布一个公告,要求每一户人家在他的大门上写上屋里男女居民的名字,像一本打开的户籍本那样,让人一目了然。这样就实现了古人的梦想:愿每个人的心灵都有一扇窗户,让外人窥见他心里在想什么。”
“啊!好主意!”莫里斯大声说道。
“在人的心灵上安一扇窗子?”
“不,而是在各家的门上贴一张名单。”
说实在的,莫里斯对此另有想法,因为这不失为是一个能找到他那个陌生女人的办法,至少能暴露出蛛丝马迹可以让他去寻找她。
洛兰又说道:
“我已经打赌,这个措施可以让我们抓到五百个贵族,是么?哦,对了,今天上午,我们在俱乐部接待了一个自愿兵代表团,他们是我们昨夜的那些对手领来的,后来我把这些人灌得半死。我说,他们还带着花饰和花环来着。”
“真的吗!”莫里斯笑着应道,“有多少人?”
“三十个,他们刮了胡子,衣扣上别着花。其中有一个演说道:‘温泉俱乐部的公民们,我们都是真正的爱国者,但愿同胞之间不会因一个误会而伤和气,我们是来重叙兄弟情谊的。’”
“后来呢?”
“后来我们又热闹一番,正如迪阿夫鲁斯所说,我们称兄道弟了。我们用书记的桌子作祖国的祭台,在两只大口水瓶里插上鲜花。因为你是这次欢聚的主角,大家高呼三声你的名字,为了给你加冕;你不在,没有回音,但又必须给什么加冕,最后把花环放在华盛顿的半身像上了。这就是仪式的程序和经过。”
洛兰说的这一段真实的故事,在那个年头倒也没什么荒唐可笑的。忽然,街上传来了喧哗声,鼓声由远至近,当时,这样的情景经常出现。
“怎么回事?”莫里斯问道。
“是公社宣布公告。”洛兰说道。
“我得归队了。”莫里斯说道,从床上一跃而起,招呼公务员来给他更衣。
“我这就回家睡觉,”洛兰说道,“昨夜我只睡了两个小时,都是为了你那发疯的自愿兵。倘若那边打起来,但不厉害的话,你就让我安睡,倘若打得厉害,你来叫我。”
“你穿得这么漂亮干嘛?”洛兰已起身准备出门,莫里斯在他身上瞥了一眼说道。
“因为到你这里必须经过贝梯西街,而在那条街上的四楼有一扇窗户,每当我经过,它必打开。”
“你不怕别人把你当成花花公子么?”
“花花公子,我?啊哈,相反,我是闻名遐迩的无套裤汉。为了女性,总得有所牺牲。对祖国的忠诚不排斥对爱情的崇拜。相反,这两者相辅相成。
“共和国颂布公告,
国人该效法希腊精神;
而在自由的祭坛下,
爱情还得与之相称。”
“你再敢吹嘘这首诗,我就揭发你是贵族,把你的毛剃光,叫你戴不上发套。再见,朋友。”
洛兰向莫里斯亲热地伸出一只手,年轻的书记友好地紧握了一下,接着,洛兰出门了,心里还在盘算着是否要买一束花献给克洛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