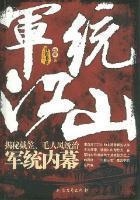第49章断头台
革 命广场上,有两人背靠着一根灯柱,等待着。
部分人群呆在法院广场,另一部分呆在革 命广场,其他的人则分散在两个场之间的路上熙熙攘攘,碰碰撞撞,他俩与大家一齐等待着,等待王后上断头台。这架断头机经过日晒雨淋、刽子手的操作、牺性者的摩擦已经锈蚀了。锈蚀,这是多可怕的景象啊!这架机器,幸灾乐祸地俯视着一个个低下的头颅,就如国王君临驾于臣民之上一般。
这两个人臂挽着臂,嘴唇发白,眉头紧蹙,说说停停,声音轻轻的,他们就是洛兰和莫里斯。他俩虽然被埋没在人海之中,然而他们的优雅与教养却使庶民钦羡,他俩低声交谈着,其内容比起从交易桥蜿蜒到革 命桥的像电线一般、又像波浪起伏的人海的一簇簇凡夫俗子的谈话更有意思。
我们刚才说的,断头台高高在上,临驾于所有头颅之上的看法,也使他俩深有感触。
“瞧,”莫里斯说道,“那恶心的怪物把那红色的胳膊举得多高啊;它是不是在招呼我们,从它那个活像血盆大口的门里冲着我们笑吧?”
“哦!天啊,”洛兰说道,“我承认,我的诗学主张不属于把一切都看成是红色的那一派。我把一节看成是玫瑰色的,即便我在这架丑恶的断头机下面,我还是要唱,并且仍抱有希望。”
“人们已经在向女人大开杀戒了,你还抱有希望?”
“啊!莫里斯,”洛兰说道,“革 命的儿子不否定革 命。啊!莫里斯,还是做一个好样的忠诚的爱国者吧。莫里斯,将要死去的那个女人不同于一般女人,她是法兰西的魔鬼啊。”
“哦,我依恋的不是她;哭泣的不是她!”莫里斯大声说道。
“嗯,我明白,是热纳维也芙。”
“啊!”莫里斯说道,“我一想到热纳维也芙到了‘喂机者’埃贝尔和富纪埃-坦维尔的手里,就控制不住自己,她落到了把可怜的爱洛绮斯、现在又把高傲的玛丽-安托瓦内特送上断头机的那帮人手里了。”
“啊哈,”咯兰说道,“这便是我的希望所在的。老百姓在盛怒之下,借这两个暴君泄恨,他们总会有息怒的时候,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就如大蟒吞下猎物之后要消化三个月一般。届时,它不再想吞食任何食物了,如同郊区的预言者所说:到了那时,任何小东西都使它害怕。”
“洛兰,洛兰,”莫里斯说道,“我比你更加激进,我对你悄悄说,但准备大声向你重复道:洛兰,我憎恨新的王后,她消灭奥地利女人,似乎想取而代之。这个王后的王位是用人们每天流出的血染红的,桑松是她的首任宰相。”
“嘿,我们就避开她!”
“我看不行,”莫里斯摇头说道,“你瞧,我们为避免在家中被捕,居然流落街头而别无他法。”
“哼!我们可以离开巴黎,什么也阻止不了的。别自卑了。我的叔叔在圣-奥梅等我们;金钱、护照,我们都有。个把宪兵对我们无可奈何的。你怎样想?我们之所以留下来的是因为我们愿意。”
“不,你说的不是实情,你是不可多得的朋友,忠肝义胆……你留下是因为我想留下来的缘故。”
“而你留下是想找到热纳维也芙。那么有什么比这个理由更单纯更正确更自然的呢?你以为她入狱了,很有可能嘛。你想照料她,就为这一点,也不该离开巴黎啊。”
莫里斯叹了一口气,显然,他的想法有些自相矛盾。
“你记得路易十六是怎么死的吗?”他说道,“我现在想起来仍激动不己,充满了自豪感哩。那时,我是群众的首领,可现在我却在人群里藏身。那时我站在断头机下面,比起那个爬上去的国王在位时都要威风。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洛兰!九个月时间足以让人彻底改变立场,多不可思议!”
“是九个月的热恋,莫里斯!……爱情,使你失去了特洛瓦(小亚细亚西北部古城,亦是传说中的名城。)。”
莫里斯唉声叹气;他的游移不定的思想滑上了另一条歧路,看到了一番天地。
“这个可怜的红屋骑士啊,”他喃喃自语道,“今天是他举丧的日子。”
“算了!”洛兰说道,“莫里斯,革 命期间,有比这更不人道的事情,你要我对你说吗。”
“说吧。”
“这就是人们常视敌为友,视友为……”
“有一件事我想不通。”莫里斯打断他的话说。
“什么事?”
“他怎么不策划去救出王后,哪怕看来荒诞可笑也罢。”
“单枪匹马能比十万人更强大吗?”
“我说了,哪怕看来荒唐可笑……我么,我知道,为了救王后……”
洛兰蹙起了眉心。
“我再对你说一遍,莫里斯,”他接着说道,“你误入歧途了;不行,即便你要救出热纳维也芙,也不能成为不良的公民啊。别说了吧,莫里斯,有人在偷听我们说话哩。瞧,人头攒动了;瞧,桑松公民的仆人从囚车上站起来了,在向远处眺望哩。奥地利女人来了。”
果然,洛兰发现人群起伏的同时,发生了经久不息、并且愈演愈烈的骚乱,如同一阵狂风呼啸而来,怒吼而去似的。
莫里斯借助灯柱,攀高了一截,他朝圣奥诺雷街的方向看。
“嗯,”他声音抖颤地说道,“她来了。”
人群开始看见了另外一架机器,几乎与断头台同样地可恶可憎,那就是囚车。
卫队的枪支在囚车左右闪着幽光,前面由格拉蒙开道,他挥舞着闪闪发光的长剑,向几个大喊大叫的狂热分子示意。
随着囚车前移,叫喊声在被判死刑的女囚那冷峻而沉着的目光下骤然停止。
王后的尊容比以往任何一个人都更具有震慑力量;玛丽-安托瓦内特也从未像现在那么伟大,那么像王后。她以非凡的勇气与高傲使在场的人感到恐惧。
她对不请自来、伴随着她的吉拉尔神甫的劝告置之不理,她的头纹丝不动;她头脑里的思想如同她的目光一样坚定不移;囚车在高低不平的地砖上颠簸,车身的震荡更显得她坚韧不拔;她仿佛像一尊大理石雕像在四轮车上前行似的;不过,这尊帝王的雕像有一对明亮的眼睛,它的头发在迎风飘舞。
不一会儿,在莫里斯和洛兰站立的地方,传来了囚车的滚动声和卫兵战马的嘶鸣声。
囚车在断头台下嘎然停下。
王后大约没有意识到这时刻的到来,这时蓦然清醒,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一切;她傲视人群,而先前她曾看见站在炮筒上的脸色苍白的年轻人,此时又站在一块界石上了。
当她走出附属监狱时,他曾向他表示敬意,现在,他站在界石上亦作出同样的手势;随后,他跳下了界石。
有好几个人看见他了,由于身着黑袍,于是话传开了,说是有个教士在等待玛丽-安托瓦内特,以便在她登上断头台时为她作赦罪仪式。不管怎么说,没有人去打搅骑士。对于某些事件来说,在崇高的时刻里,总会伴之以崇高的敬意。
王后十分留神地走下三级踏脚板;桑松扶着她,直到最后的时刻,他一直在执行肩负的重责,同时又对她表现出最大的关注。
当她走向断头台的梯级时,有几匹马直立起来,几个站岗的守卫和几个士兵好像失去了平衡,在晃动;又似乎有一个黑影钻到断头台下面去了,不过人们即刻又安静下来,因为在这庄严的时刻,谁都不愿离开原位,谁都不愿放过即将谢幕的伟大悲剧里的最微小的细节,所有的人都死死盯着女囚。
王后已经站在断头台的台面上。神甫仍然在对她喋喋不休;一个副手从后面轻轻地推她向前;另一个解开了披在她肩头上的方巾。
玛丽-安托瓦内特感到这只手亵渎到她的脖子,猛地抖动一下,踏到桑松的脚背,桑松那时在一边忙着把她系在那块索命的木板上,她没看见。
桑松收回了脚。
“请原谅,先生,”王后说道,“我不是故意的。”
这是凯撒们的女儿,法国王后,路易十六的遗孀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杜伊勒宫的钟声敲响午后一刻钟。就在这时,玛丽-安托瓦内特将投入永恒之中。
惊天动地的呼喊声——这声音汇总了所有的情绪:欢乐、恐惧、悲哀、希望、胜利、赎罪——像狂风暴雨般地盖住了另一个虚弱、悲惨的声音,它同时也在断头台下面呼喊出来。
声音虽弱,宪兵们还是听到了;他们向前迈开几步;就在这时,变得稍稀的人群像决堤一般向前涌来,推倒篱栅,冲散了卫兵,如同海潮似的冲击着断头台,把它冲撞得摇摇晃晃。
每个人都想就近看着王朝最后的残骸,每个人都以为王朝在法国已一去不复返了。
可是宪兵们在寻找其他东西:他们在寻找这个黑影,它刚才越过了警戒线,钻到了断头台下面去了。
有两个士兵抓着一个年轻的人的衣领回来了,他的一只手把一块鲜血淋淋的手绢压在心口上。
年轻人后面跟着一条长毛垂耳的小狗,它在悲惨地哀嚎。
“处死贵族!处死旧党!”人群中有几个人指着年轻人喊叫道,“是他把手绢浸入奥地利女人的鲜血之中的,处死他!”
“伟大的天主啊,”莫里斯对洛兰说道,“你认识他么?你认识他么?”
“处死王族分子!”几个狂怒的人叫喊道,“把他的手帕拿掉,他想留作纪念呢;拿掉!拿掉!”
年轻人的嘴角上挂起轻蔑的微笑,他撕破衬衣,露出胸膛,手绢掉落了下来。
“先生们,”他说道,“这鲜血不是王后的,而是我的;让我安静地死去吧。”
在他的左胸,有一个又深又大的血淋淋的伤口。
人群惊呼一声,向后退去。
这时,年轻人的身体慢慢不支了,他曲腿跪地,眼睛死死盯着断头机,就如殉道者凝视祭台一般。
“红屋骑士!”洛兰在莫里斯的耳边说道。
“永别了!”那个年轻人面露圣洁的微笑,低下头,喃喃说道,“永别了,或者说,再见!”
说完,他在一群惊愕不已的卫兵中间断了气。“在成为不良公民之前,还有一件事可做,洛兰。”莫里斯说道。
小狗围着这具尸体转圈子,发疯似地狂吠着。
“瞧,是黑子,”一个人手上拿着一根粗大的棍子说道,“瞧,是黑子;到这里来,我的老朋友。”
小狗向叫唤它的人走去;可是它刚刚挨近他,那人就举起粗棍,把它的脑袋砸烂了,并且放声浪笑。
“啊!浑蛋!”莫里斯大声说道。
“别出声!”洛兰拉拉他轻声说道,“别出声,要不,我们就完了……他是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