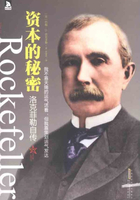第4章时代的风尚 (1)
林代清醒过来后,向四周瞧瞧,他只看见一条条阴森森的窄巷在他左右延伸。他努力寻找着,辨识着,但他的头脑乱糟糟地,夜色沉沉;月亮方才刚刚探出头照亮了一下陌生女人迷人的脸庞,这时又躲进了云层里,年轻人惊魂未定,重新上路向他的鲁尔街的寓所走去。
莫里斯回到圣-可伏街时,看见大批巡逻队在寺院街区巡逻,非常谅讶。
“发生了什么事,中士。”他向一支执行任务的巡逻队头目问道,这支队伍刚刚在喷泉街进行搜查,一路过来。
“什么事?”中士说道,“我的军官,今天夜间有人想劫走卡贝女人(法国大革命期间,“卡贝”这个绰号喻指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室成员。)和她的一窝人。”
“怎么回事?”
“贵族的一支巡逻队不知怎么得到了口令,穿着国民卫队的队员制服窜到寺院街,想把他们劫走。幸而那个伪装小头目的人向卫队军官说话时,称呼‘先生’,这下露了馅,卡贝贵族。”
“见鬼!”莫里斯说道,“把叛变者抓到了没有?”
“没有,那个所谓巡逻队冲上街头后,四处逃跑了。”
“还有希望追上那些家伙吗?”
“其中有一个头目,是瘦高个子,得抓住才好。……他是被一位市政府人员介绍到卫队来的,他使我们疲于奔命,该死的东西!他大概找到了一道后门,从玛德隆修道院跑掉了。”
换个背景下,莫里斯会整夜与这些爱国者在一起为了祖国的利益值勤的;然而,在过去的一小时里,对祖国的爱已经不是他惟一的了。因此他走着走着,方才得到的消息在他的头脑里开始化解,并且在刚刚发生的那件事情前面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再说,这些所谓的劫案层出不穷,爱国者本人心里也明白,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政治手段来利用的,因此,这条新闻并未引起年轻的共和党人多大的不安。
回到家中,莫里斯看见了他的“公务员”;在那个非常时期,谁也不时兴有什么仆人的。我们说了,莫里斯看见他的公务员在等着他,他等着等着睡着了,睡着时还在不住地打着呼噜。
他小心翼翼地把他叫醒,请他脱下自己的套靴,又把他打发走,免得自己分神;他上床时,天色已晚,他又年轻,因此尽管有心事,也不由自主地睡了去。
次日,他在床头柜上发现了一封信。
信上的字迹娟秀、雅致,出自陌生人之手。他看看漆封,漆封上印有惟一一个英文字:Nothing,——没有。
他打开信,信里只有这几句话:
谢谢。
永久的感谢报以永恒的忘却!……
莫里斯把仆人叫来;时下,真正的爱国者已不再按铃,因为按铃是叫仆役的。再说,许多公务员进入他们的主人家服务时,就提出不用铃的条件,主人们当然同意了。
莫里斯的公务员约在三十年前在洗礼时接受了约翰这个名字,然而到了九二年,他自作主张把教名废了。他觉得约翰这个名字有点贵族和神道的味儿,便自称斯赛伏拉。
“斯赛伏拉,”莫里斯问道,“你知道这封信是怎么回事么?”
“不知道,公民。”
“是谁交给你的?”
“门房。”
“谁捎来的?”
“大约是一个跑腿的人,既然信上没贴国家的邮票。”
“下楼去,请门房上来一趟。”
门房上来,因为这是莫里斯在招呼他呀,莫里斯得到所有与他打交道的公务员的爱戴。不过,门房还是作出声明,换了另一位房客叫他,他相反会请房客下楼来的。
门房名叫阿里斯蒂特。
莫里斯询问他。他说上午将近八点钟,一个陌生男子给他捎来了这封信。年轻骑士又问了他好多问题,从种种角度启发他,门房什么也不知道。莫里斯请他接受十个法郎的小费,说,如果这个人再次出现,就请他大大方方地跟踪他,并且回来告诉他此人到哪里去了。
我们应该要告诉读者的是,阿里斯蒂特虽然受命去跟踪一个同一个阶层的人,自尊心多少受点委屈,但使他大为宽慰的是,那个人没有再来。
莫里斯一个人呆着,气恼地搓揉着信,把戒指从手指上脱下,与揉皱的信一起放在床头柜上,转过身子把脸对着墙,急欲重新入睡。一小时又过去了,莫里斯再也不能佯装洒脱了,他吻吻戒指,又读了一遍信,发现那枚戒指是晶莹夺目的蓝宝石制成的。
我们说过了,信笺是一张精致的小纸片,散发出浓烈的贵族气息。
正当莫里斯在仔细观察时,门开启了。莫里斯重新把戒指戴上,把信藏在枕头下面。这是爱情萌发的羞怯表示呢,还是一个爱国者的内疚的反映呢?他不愿意别人知道他与这样粗心大意的人有联系,因为这个人居然写了这么一封信,光凭信笺的香味就能累及写信人和收信人了。
来者是一个年轻人,普通爱国者的穿着打扮,但眉宇间透露出非凡的高雅气派。他的短上衣是细呢料子制成细毛绒短裤,长统袜是丝织的。他戴的红色锥形高帽,就其优雅的形状和美丽的紫红色而言,该让象征巴黎的流行帽相形见绌。
此外,他的腰带上挂着一对昔日凡尔赛宫王家特制的手枪和一把又直又短的佩剑,如战神广场(法国陆军学校设在那里。)上的学生佩戴的那种。
“啊,你在睡觉,节鲁图(节鲁图(?—公元前43):罗马将军。曾参与刺杀凯撒。),”来者说道,“祖国在危难之中,别睡了吧!”
“没有,洛兰,”莫里斯笑道,“我没在睡觉,我在做梦。”
“是呀,我明白,在梦想欧沙里(法国作家费纳龙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吧。”
“唉,我自己也说不清。”
“算了吧!”
“你在说谁?这个欧沙里是谁?”
“嗯,一个女人……”
“什么女人?”
“就是圣-奥诺雷街的那个女人,巡逻队遇见的那个女人,昨天晚上你我险些为她掉脑袋的那个陌生女人。”
“啊,是的,”莫里斯说道,他非常明白他的朋友想说什么,但他佯装不解谁是那个陌生女人。
“可我一点也不知道。”
“她漂亮吗?”
“呸!”莫里斯说道,不屑地嘟起嘴。
“一个可怜的女人,幽会时情人没来。
“……我们是多么软弱,
永远为这类爱情丧魂落魂。”
“有可能吧。”莫里斯喃喃地说道。他起初也有这个想法,但眼下很厌恶这个假设,他宁愿那个美丽的陌生女人是叛国者,也不愿她是浪荡女。
“她住在哪儿?”
“不知道。”
“算了吧!你什么也不知道!不可能!”
“为什么?”
“你送她回家的。”
“她在玛丽桥就溜掉了。”
“从你手中溜掉?”洛兰大声说道,放声大笑,“一个女人从你身边溜掉,不可能!
秃鹫是天空的暴君,
白鸽能逃脱它的巨爪?
荒野恶虎已攫获羚羊,
难道它还能插翅高飞?”
“洛兰,”莫里斯说道,“你就不能学学像别人那样说话么?你那刺人的诗句让我听了怪难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