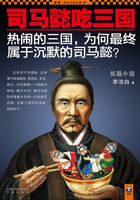第44章红屋骑士的准备
上一章里描述的情景在王后牢房对面,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两个宪兵占有的第一隔间对面的书记员室里发生时,那么在另一头,即在妇女院子里正进行着其他准备工作。
一个男人突然出现了,如同一尊石雕从墙上脱离开来。此人身后跟着两条狗,他一边哼着当时的流行小调《来日方长》,一边用手中的那串钥匙连着刮了刮拦在王后囚房窗户上的五根铁栅。
王后起先惊了一下,之后认定是信号,便即刻轻轻打开窗户,用她那只出乎人们想象的灵巧的手开始干起活来,由于往昔,她那当国王的丈夫喜欢常去匙锁房消遣,她那纤细的手指也就时不时地触摸过这些大同小异的工具,眼下,这件东西成了她生死的主宰了。
挂钥匙的人听见王后的窗户开启声,就走去敲宪兵的门。“啊!啊!”吉尔贝穿过铁栅栏边看边说道,“是马尔道什公民。”
“正是,”管钥匙的狱卒答道,“怎样,似乎防卫挺严嘛?”
“一贯如此,挂钥匙公民。我觉得您倒不常认为我们不尽责哩。”
“啊!”马尔道什说道,“今天夜间要加倍警惕才好。”
“算了吧!”杜谢斯纳凑过去说道。
“肯定要这样。”
“发生什么事情?”
“您打开窗户,我对您细说。”
“打开吧。”杜谢斯纳说道。
吉尔贝打开窗子,与挂钥匙者握了握手,他早已是这两个宪兵的朋友了。
“发生什么事了,马尔道什公民?”吉尔贝又问道。
“国民公会争辩得很激烈,您读报纸了吗?”
“没有。出什么事了?”
“啊!首先是埃贝尔公民有了新的发现。”
“什么?”
“一些谋反者,大家都以为他们死了,居然还活着,而且还挺活跃呢。”
“啊,是的,是特莱莎尔和梯埃里,我已听说了;他们现在在英国,这些叫花子。”
“还有红屋骑士呢!”挂钥匙者提高噪门说道,以便让王后听见。
“什么!他也在英国?”
“不是的,他在法国。”马尔道什以同样的音调继续说道。
“这么说他回来了?”
“他根本没离开过。”
“真是个胆大妄为的人。”
“他就是这样的。”
“要设法逮捕他。”
“当然啦,要设法逮捕他;但似乎不那么简单。”
这时,王后的锉刀在铁窗栏上锉得过响,挂钥匙者担心自己的声音盖不住,宪兵会听见,于是就把脚跟踩住一条狗的尾巴,狗发出痛苦的惨叫声。
“哦!可怜的畜生!”吉尔贝说道。
“算了吧!”挂钥匙者说道,“它穿上木屣就好了。住口,吉伦特,住口行不!”
“你的狗叫吉伦特,马尔道什公民?”
“是的,这是我给它起的名字。”
“你说什么来着,”杜谢斯纳又问道,他本人在这里也如同囚犯,因此与囚犯一样对新闻有强烈的兴趣,“说什么来着?”
“啊,对,我想说埃贝尔公民—他是一个爱国者—我说埃贝尔公民提议把奥地利女人带回寺院监狱。”
“为什么?”
“哼!因为他声称当初有人把她从寺院监狱转移走是为了免使她受到巴黎公社的直接控制。”
“啊!还有一层理由是防止这个该死的红屋骑士再次企图劫狱,”吉尔贝说道,“好像那条地道还存在。”
“桑代尔公民也是这样说的;可是埃贝尔说,既然大家已知道了,也就不存在危险了;在寺院监狱看守玛丽-安托瓦内特用的人力比这里少一半,因为那所监狱比附属监狱要安全得多。”
“天哪,”吉尔贝说道,“我宁愿她回到寺院监狱去。”
“我晓得,你守她守得厌倦了。”
“不是的,而是心情不愉快。”
锉刀在铁栏上锉得愈深发出的声音愈大,于是红屋骑士就咳嗽愈烈。
“最后如何决定?”当挂钥匙者的咳声止住之后,杜谢斯纳问道。
“她仍留在这里,不过立即开庭审理。”
“啊!可怜的女人!”吉尔贝说道。
杜谢斯纳的耳朵大概比他的同事更加灵敏些;要不就是对马尔道什的叙述不那么专注,他居然弯下身子细听左边隔间的动静。
挂钥匙者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你得明白,杜谢斯纳公民,”他飞快地说道,“阴谋者知道他们实现计划的时间不多了,困兽犹斗,就变得更加危险。附属监狱的防守要加强,因为他们只能以武力袭击;谋反者以后会见人就杀,一直杀到王后也就是卡贝寡妇跟前为止,我想说的就这些。”
“哦,算了吧!这些阴谋者怎么能进来呢?”
“化装成爱国者的模样,重演一遍9月2日的大屠杀,这些坏蛋!一旦门开了,嘿!晚安!”
宪兵吓呆了,一时出现了片刻宁静。
挂钥匙者听见锉刀继续在锉,喜惧交加。九点钟敲响了。
与此同时,有人在敲书记员室的门,可是这两个宪兵正在想心事,没有答理。
“嗯,我们得提高警惕,提高警惕。”吉尔贝说道。
“如有必要,我们要像一个真正的共和党人那样战死在岗位上。”杜谢斯纳补充道。
“她该快结束了吧。”挂钥匙者擦着额头沁出的冷汗,心里想道。
“您呢,我想您也要留神呀,”吉尔贝说道,“因为假如像您所说的事当真发生了,他们同样也不会放过您的。”
“我相信,”挂钥匙者说道,“我整夜巡逻;因此我也实在吃不消了你们至少有间歇时间,隔天可以美美睡上一觉。”
这时,有人第二次敲书记员室的门。马尔道什打了一个哆嗦,因为这是再微小的细节都能影响他们计划的成功。
“什么事?”他不由自主地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吉尔贝说道,“是军部文书要走了,通知我们一声。”
“啊!很好嘛。”挂钥匙者说道。
可是书记员仍执拗地在敲门。
“知道了!知道了!”吉尔贝叫喊道,没在窗口边挪动身子,“晚安!……再见……”
“好像他在同你说话,”杜谢斯纳把头扭向门口说道,“答应他……”
这时,传来了书记员的声音:
“来吧,宪兵公民,”他说道,“我想同你说一会儿话。”
这人声音听起来似乎很激动,与平时的声调有所不同,因此引起挂钥匙者的注意,他似乎听了有点耳熟。
“你想干什么,杜朗公民?”吉尔贝问道。
“我想对你说一句话。”
“那就明天说吧。”
“不,要今晚说;我得今晚说。”那个人又说道。
“噢!”挂钥匙者暗忖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迪克斯梅的声音。”
这个声音颤颤抖抖的,充满了不祥的预兆,在阴森森的过道上悠悠地回荡着,一如报丧的信号。
杜谢斯纳转过身子。
“去吧,”吉尔贝说道,“既然他非见不可,我就去。”
说着,他向门口走去。
挂钥匙利用了宪兵打岔的这个契机,奔向王后的那个窗口。
“完事了吗?”他问道。
“锉了一半多了。”王后答道。
“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啊!”他轻声说道,“快点儿,快点儿!”
“怎么啦,马尔道什公民,”杜谢斯说道,“你怎么啦?”
“我在这儿。”挂钥匙者大声说道,又飞快地回到第一个隔间的窗口旁。
就在他刚要回到原位上的刹那间,监狱里响起了惨叫声,接着便是咒骂声和剑出鞘的金属碰撞声。
“啊!恶棍!啊!匪徒!”吉尔贝叫喊道。
在过道上响起了格斗声。
这时,门打开了,挂钥匙者看见两个黑影在门口互相厮打,给一个女人让出了一条路,那女人把杜谢斯纳一推,冲进王后的隔间。
杜谢斯纳没把女人放在心上,奔去援助他的伙伴。
挂钥匙者奔向另一个窗口;他看见那个女人跪在王后膝下,苦苦哀求女囚与她交换衣装。他目光灼灼地弯下身子,想竭力辨认这个女人,他似乎对她太熟悉了。蓦地,他发出了痛苦的呼叫声。
“热纳维也芙!热纳维也芙!”他叫喊道。
王后一松手,锉刀落下了,她似乎已经累垮了。这又是一次流产的劫狱行动。
挂钥匙者两手抓住已被锉刀锉开的铁栅栏,拼命摇晃。
然而锉缝进得不深,铁栅栏没松动。
这时,迪克斯梅在过道一边的门口已经击退了吉尔贝,正欲冲进房间,可是杜谢斯纳沉沉地压住门,并把门向外推。
但他没能把门关死。迪克斯梅孤注一掷,把胳膊嵌进了门与门框之间。
他伸进来的那只手上拿着匕首,方才匕首刺在对手腰带的铜钮上,锋刃弄钝了,只是在宪兵的胸前浅扎了一刀,仅划开了他的制服,刮破了他的皮肉而已。
这两个人同心合力,相互鼓励,同时又大声呼救。
迪克斯梅觉得他的胳膊快要断了,他把肩膀顶住门,猛地一撞,把胳膊收了回来。
门重重地关上了;杜谢斯纳推上门栓,吉尔贝还把钥匙拧了一圈。
一个人快速的脚步声在走廊上震响,过后都归于寂静。
两个宪兵面面相觑,向四周张望。
他们听见那个伪装狱卒想把铁栏搡断的声音。
吉尔贝冲进王后的隔间,发现热纳维也芙跪在她的膝下,哀求王后与她互换衣服。
杜谢斯纳拿起他的短枪,向窗口奔去:他看见一个男人抓住铁栅栏,发疯似地在摇晃,想翻越进屋却没有成功。
他把枪瞄准了这个人。
年轻人看见短枪枪筒向他移来。
“啊!好啊,杀了我吧,杀吧。”
他因绝望而变得无所畏惧,他挺起胸膛面对枪膛。
“骑士,”王后大声说道,“骑士,我求求您了;活下去,活下去吧!”
红屋骑士听见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声音,一下扑倒,跪在地上。开枪了;但他刚才的动作使他得救了,子弹从头顶上飞过去。
热纳维也芙以为他的朋友被杀了,倒在地砖上失去了知觉。
硝烟过后,妇女院子里已空无一人。
十分钟之后两个委员带着三十名士兵搜索整个附属监狱,连最隐蔽的角落也没放过。
他们没发现任何可疑分子;军部文书在理查德老爹的安乐椅前走过时,神态安详,面带笑容。
至于那个挂钥匙者,他出门时高呼:
“警报!警报!”
哨兵本想用刺刀挡住他,可是他身边那几条狗扑到哨兵的颈脖上了。
只有热纳维也芙被抓住了,受到审讯和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