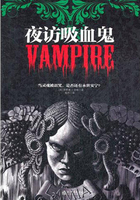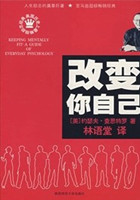第41章陆军部书记员
爱国者走出去后,并未走远,他透过烟雾蒙蒙的窗玻璃,窥视着狱卒看他是否与某些共和国警方的暗探接头,因为这个警察系统是有史以来最严密最有效的一支力量,社会的一半人在监视着另一半人,他们与其说是为了忠于政府,还不如说是为了保住脑袋。
可是,爱国者的担心是多余的;九点不到数分钟,狱卒站起来,用手摸了摸女店主的下巴颏,走了出去。
爱国者在附属监狱的码头上与他会面,于是这两个人就一齐走进监狱。
就在当天晚间,交易做成功了:理查德老爹同意马尔道什狱卒接替格拉居斯公民。
就在上述这笔交易在监狱里成交的前两个小时,在监狱的另一头又演出了一场,虽说从表面看无关宏旨,但对于本书的几个主人公而言却不无重要意义。
附属监狱的书记员白天干累了,合起登记本,刚欲走出门,看见理查德老婆领着一个人来到他的办公室前。
“书记员公民,”她说道,“他是您的陆军部的同行,部长公民吩咐他来抄录一些军籍囚犯的姓名。”
“哦!公民,”书记员说道,“您来迟点儿了,我已经收摊了。”
“亲爱的同事,请原谅,”新来者答道,“我们有做不完的事情,因此只能抽空出去跑跑,所谓抽空,也就是别人吃饭睡觉的时间而已。”
“既然如此,那就抄吧,亲爱的同事;不过请抓紧时间,因为正如您说的,已到吃晚饭时间了,我的确也饿了。您带公文来了吗?”
“带来了,”陆军部的文书说道,递上了公文袋,他的同事尽管很匆忙,仍然极为仔细地审阅着。
“啊!完全符合规定,”理查德妻子说道,“我丈夫已检查过了。”
“不碍事,不碍事,”书记员边说边看。
陆军部文书耐心等着,他早已习惯这些严格的审查程序了。“好极了,”附属监狱的文书说道,“现在,您随时都可以工作。您有很多犯人要抄录吗?”
“百把人。”
“那么,您需要好几天罗?”
“因此,亲爱的同事,我要在您这里安顿几天,当然得征求您的意见。”
“这话什么意思?”附属监狱的文书问道。
“今晚,我请您去用餐时会解释的,你不是说,您饿了么。”
“我不否认。”
“那好,您将会见到我的妻子,她烧得一手好菜;您也会进一步了解我!我是一个好小伙子。”
“当然罗,您给我的印象不错;不过,亲爱的同行……”
“啊!别客气了,请接受我路经夏特莱广场时欲将买下的牡蛎和在烤肉店买下的烤母鸡,以及杜朗太太做得尽善尽美的两三样小菜吧。”
“您让我垂涎三尺,亲爱的同行。”附属监狱的文书说道;他动心了,一个由革命法庭支付薪金的文书是不能常吃到这样的菜肴的,他每月仅能拿到两个利弗尔的证券,实际上至多值两个法郎。
“这么说,您接受了?”
“我接受。”
“那么明天开始干活吧;今晚就出去。”
“走吧。”
“您来吗?”
“等一下;让我去通知一下看守奥地利女人的宪兵。”
“通知他们干吗?”
“让他们知道我出去了,书记室里没有人,如有声响,他们就会警觉的。”
“啊!太好啦;真是小心谨慎。”
“您能理解,不是么?”
“非常理解。去吧。”
附属监狱的文书果真去敲小门了,一个宪兵打开门问道:
“谁?”
“我!书记员;告诉您,我走了。晚安,吉尔贝公民。”
“晚安,书记员公民。”
小门又关上了。
军部文书极为专注地观察着这个场面,当王后囚室的门开启时,他的目光迅速扫视了整个外隔间,他只看见宪兵杜谢斯纳坐在桌旁,因此肯定王后身边仅有两个看守。
不消说,一旦附属监狱的文书转过身子,他的同行又在脸上恢复了冷漠的神态。
当他俩走出附属监狱时,正好有两个人走了进去。
走进去的这两个人,一个是格拉居斯公民,一个是他的表哥马尔道什。
马尔道什表哥同军部文书打照面时,仿佛出于同一动机似的,一个拉了拉他的皮帽子,另一个把他的宽边帽也拉下,仅露出两只眼睛。
“这两个人是谁?”军部文书问道。
“我只认识其中一个,是一个名叫格拉居斯的狱卒。”
“哦!”对方装出漠然的口气说道,“狱卒也能离开附属监狱?”
“他们也有休假。”
谈话没有深入下去,这一对新朋友走上了昌目桥。在夏特莱广场的一角,军部文书按照说好了的,买了一筐十二打牡蛎,接下走过热夫尔码头。
陆军部文书的住宅相当简单:这位杜朗公民在格雷夫广场上租下一个小三居室的套房,整幢楼没有门房。每个房客身上都带着一把开大门的钥匙;如果房客没有带钥匙,就按自己住的楼层,用门锤在大门上敲一二或是三下,里面在等人的人听到敲门的信号,便下楼开门。
杜朗公民口袋里揣着钥匙,他无需敲门。
法院文书觉得军部文书的太太很配自己的口味。
她果然是一个迷人的妇人,一脸愁容让人一看就生怜。应该说,忧愁是漂亮女人最可靠的引诱手段之一,忧愁使所有男人顿生怜爱,连文书也不例外;因为,无论人们如何说三道四的,文书也是人,自尊心再强的人,或是生性再冥顽不化的人都希望去宽慰一个痛苦中的美人,如同多拉(多拉(1508—1588):法国人文主义者、诗人。)公民所说的,把“苍白的白玫瑰变成鲜艳的红玫瑰”。
两个书记员用餐时胃口大开;只有杜朗太太没动刀叉。
不过,谈话是从东头说到西头。
军部文书带着每天都出事的非常时期人们惯有的好奇心,向他的同行打听法院的审理程序,审判的日子和看守的方法。
法院文书看见对方如此专注地恭听自己说话受宠若惊,非常乐意回答,向他讲述狱卒生活起居,富纪埃-坦维尔的日常工作,甚至桑松公民的习好,说他可是每天晚上在革命广场悲剧演出的导演啊。
接着,法院文书也向军部同行兼主人问及军部的情况。
“啊!”杜朗说道,“我算不上正式文书,只是抄抄写写而已,比起您来地位差远了,我知道的可没您的多。我是个不起眼的雇员,干的倒是书记长的活儿,苦是自己吃,好处是当官拿。官僚衙门都是这样,即便革命机构也如此。也许会有一天乾坤倒转,但官僚体制是不会变的。”
“嗯,我会帮您一把的,公民。”法院文书说道,主人的好酒,特别是杜朗太太那一双美丽的眼睛使他心迷意乱了。
“啊!谢谢,”受到宠幸的那人说道,“对一个不卑贱的职员来说,多一些生活内容,能走动走动都是一种消遣,因此,只要每天晚上我能把杜朗太太带到书记室来,我宁愿在附属监狱拖下去,也不愿早早结束这个差事,她在这里实在闷得慌……”
“没什么不方便的,”法院文书说道,很高兴他的同行向他提出这么一个有趣的消遣方式。
“这样,她就可以向我口述犯人的名册了,”杜朗公民继续说道,“再说,倘若您不以为今晚的饭菜难以下咽的话,请您不时地来吃上一顿便饭。”
“谢谢,可不能太经常呀。”法院书记员自鸣得意地说道,“因为不瞒您说,倘若我回到小磨街的那所小房子里比平时稍晚的话,我会受到呵斥的。”
“好啦,一切都解决得很完满,”杜朗说道,“是么,亲爱的朋友?”
杜朗太太的脸上始终是那么苍白和悲哀,她抬起眼睛看看她的丈夫,答道:
“悉听尊便。”
十一点钟敲响了,是告辞的时间了。法院书记员起身,向他的两位新友告辞,并为能结识他们及他们的盛情款待表示出由衷的高兴。
杜朗公民把客人送到楼道上,然后回到房间里。
“行啦,热纳维也芙,”他说道,“睡吧。”
少妇一言不语地站起来,拿起一盏灯,进入右首的房间。
杜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迪克斯梅,眼睁睁地目随她走出去,思索了片刻,一脸愁容,接着,他也走进自己的房间,在她房间的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