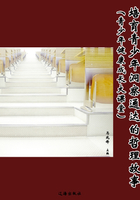第40章诺亚井洒店
我们曾经与那个穿着紧身上衣在法院大厅里来回踱步,并且在吉罗建筑师、昂里奥将军和理查德老爹走去揭开秘密的当儿,与留守在地道口的狱卒谈话的那个人谋过面,也就是那个头顶熊皮无檐帽,蓄着浓厚的胡子,曾向西蒙自诩为提过朗巴尔王妃脑袋的那个狂热的爱国者。此人就在那个波澜起伏的傍晚的次日,在将近晚上七点钟光景,来到了开在旧衣街拐角上的诺亚井酒店,这些,我们在前面都已交代过了。
他坐在酒店老板,或者不如说呆在酒店老板娘开店堂的最里端,仿佛在大啖一盘臭奶酪煎鱼。店堂黑黢黢的,被烟叶和蜡烛熏得雾气腾腾。
他就餐的店堂没什么人,仅有两三个常客留下还没走,他们在享受因每天光顾这家酒店而得到的特权。
大多数餐桌都是空空的;不过也应该替诺亚井酒店说句公道话,桌上红红的,或者不如说红得泛紫的桌布表明,仍有不少来客在此地酒足饭饱,满意走过一遭的。
最后三位客人也先后离去了,到了将近八点差一刻,这个爱国者便只身一人了。
这时,他才带着贵族气派的厌倦神态,把那盘刚才似乎还吃得津津有味的劣质菜肴推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西班牙巧克力。他慢嚼细咽,与我们方才描绘的那个形象已判若两人了。
他一面嚼着西班牙巧克力和黑面包,一面时不时地向已用红白小方格门帘遮住的玻璃门瞥上一眼,目光里充满了焦虑和急躁。有时,他侧耳细听,放下那简单的饭菜,那心神不定的样子,使坐在紧靠门边的柜台前的女店主不无根据地还自以为这个爱国者老瞟着自己,使得她心猿意马了。
门铃响起,响声怪异,让我们眼下的这个人猛地一惊;他又拿起了那盘鱼,而店堂女主人没有觉察到,他早已把一半鱼扔给了一条眼睁睁看他吃的饿狗,把另一半扔给向狗伸出细细的利爪的猫了。
遮着红白相间门帘的门开启了;一个人走了进来,他的穿着几乎与那个爱国者别无二致,只是戴的不是熊皮无檐帽,而是红色无檐帽。
来者的腰带上挂着沉沉的一串铜匙,腰间还垂落下一柄宽厚带贝壳纹铜鞘的步兵大刀。
“我的汤!我的酒!”此人走进大餐厅时嚷嚷道,红帽子也不脱,只是对女店主点了点头。
接着,他有气无力地叹了一口气,在我们那位爱国者用餐的邻近的那张餐桌坐下。
酒店女老板出于对新来者的尊重,站起来,亲自去要那两样东西了。
这两个背对背坐着;一个望街,另一个面对厅堂。只要女店主还在,这两个彼此就不说一句话。
女店主身后的门关了,一根铁丝上悬吊着一支蜡烛,烛光巧妙地落在这两个顾客之间,带熊皮檐帽的人借着他对面的镜子,发现厅常已空无一人了,便头也不回地对他的伙伴说道:
“您好。”
“您好,先生。”新来者答道。
“怎么样,办完了。”
“什么办完了?”
“我们说定了,由我去向理查德老爹辞去职务。我借口说我耳聋眼花,并且在大庭广众之中昏过去一次。”
“很好,以后呢?”
“以后,理查德老爹叫他的老婆,他的老婆就用醋擦我的脑穴,我终于醒过来了。”
“好,说下去。”
“下面,如同我俩说好,我说缺少新鲜空气是我耳聋眼花的原因,因为我是个多血质的人,眼下附属监狱监禁着四名囚犯,我在那里干活会送命的。”
“他们说什么来着?”
“理查德大妈同情我。”
“那么理查德老爹呢?”
“他把我赶出来了。”
“可光是他把你赶出来还不够呀。”
“请等等;这时,好心的理查德大妈就说他没心肝,因为我有孩子哪。”
“他又怎么说?”
“他说他老婆言之有理,不过狱卒工作的首要条件是坚守岗位;共和国不是闹着玩的,在执行任务时头晕眼花一样要掉脑袋。”
“见鬼!”爱国者说道。
“理查德老爹说的也没错;自从那个奥地利女人到来之后,那地方简直成了人人自危的地狱,即便对自己你父亲也深究再三的。”
爱国者把他的盘子让狗去舔,猫就去咬它。
“说下去。”他头也不回地说道。
“最后,先生,我开始打哼哼,说是身体不舒服,我请求去诊所,我肯定地说如果国家把我开除了,我的孩子就会饿死。”
“理查德老爹怎么讲?”
“理查德老爹说,一旦当上了狱卒,就不该生孩子。”
“可我想,您有理查德大妈在您身边呀?”
“幸好如此。她与她丈夫干了一场,责备他心肠不好,最后,理查德老爹就对我说:‘好吧,格拉居斯公民,你找一个朋友来,让他在薪水中扣一部分给你;把他作为替补人介绍给我,我答应你让狱方把他收下来,我听了这番话,就说:‘行,理查德老爹,我这就去找。’于是便出去了。”
“那么你找到了么,小伙子?”
就在此时,酒店老板娘走进来,给格拉居斯公民带来了他要的汤和酒。
她的到来对格拉居斯和爱国者都不是时候,他俩无疑还有许多话要说。
“女公民,”狱卒说道,“我从理查德老爹那里得到一点点赏钱,所以今天我还要一份猪排小黄瓜和一瓶布洛涅葡萄酒;你差一个女仆到肉店去买,而你自己就到地窖里替我去拿吧。”
女店主立马吩咐下去,女仆从临街的那道门出去了,而她本人则从地窖门走出去。
“好嘛,”爱国者说道,“你是个聪明的小伙子。”
“虽说聪明,但实不相瞒,尽管有您的美丽的诺言在先,我还不知道这件事的结局如何。您猜测会有什么结果呢?”
“完全猜得到。”
“我们在用脑袋赌博。”
“别担心我的脑袋。”
“先生,我得承认,我最为担心的也不是您的脑袋。”
“是你的?”
“是的。”
“可如果出我这颗脑袋的双倍价钱……”
“喔!先生,脑袋瓜可是一件十分值钱的东西哟。”
“不是你的。”
“什么!不是我的?”
“至少现在不是。”
“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的脑袋瓜不值一个铜子儿,譬如说,如果我是公安委员会的一个暗探,你明天就得上断头台。”
狱卒猝不及防,猛地回头,引起狗向他吠叫。
他的脸苍白得像个死人。
“别掉头,也别害怕,”爱国者说道,“相反,静静地把汤喝完吧。我不是爱找碴儿的暗探,朋友。让我进入附属监狱,替代你的位置。把铜匙给我,明天,我就给你五万金利弗尔。”
“是真的么?”
“啊!我的脑袋在你身上,这可是一笔可观的保证金啊。”
狱卒沉吟了数秒钟。
“行啦,”爱国者从镜子里看着他说道,“行啦,别胡思乱想啦;如果你尽责而揭发我,共和国不会给你一个子儿;如果你不为我效力,你就失职了;在这世上作出牺性而得不到报酬是不公平的,因此我给你五万利弗尔。”
“啊!我很明白,”狱卒说道,“我按您的要求去做可是一本万利,可是我担心后果……”
“后果!……你有什么可害怕的?瞧,我总不会揭发你吧。”
“当然啦。”
“我上班后的第二天,你到附属监狱来转一圈;我给你二十五卷钱,每卷有两千法郎;这二十五卷东西揣进两个口袋就行了,我另外再给你一张出国的地图;你走吧,无论走到哪儿,你就是称不上富有的话,也可自立了。”
“好吧,这这么说完了,先生,该怎样就怎样吧。我是个可怜虫;我从不过问政治,法国没有我照样在前进,也不会因为我而一蹶不振;倘若您干坏事,就没好下场。”
“无论怎么说,”爱国者道,“我不认为会做出能比现在更坏的事情来。”
“先生,您能允许我对国民公会的政策不加评议么。”
“你既有哲学头脑,又烦神不多,了不起啊。说说看吧,你什么时候把我介绍给理查德老爹?”
“您愿意就今晚。”
“当然愿意;我以什么身份?”
“我的表哥马尔道什。”
“马尔道什,行;这个名字不错。干哪行的?”
“做裤子的。”
“从做裤子到制皮革,都是用手。”
“您是制革商?”
“我可以是。”
“嗯。”
“何时引见?”
“再过半小时吧。”
“那么九点整。”
“我什么时候有钱?”
“明天。”
“这么说您是个大富翁了?”
“马马虎虎。”
“一个贵族是吗?”
“关你什么事!”
“自已有钱,又肯冒着上断头台危险去花钱,说真的,只有贵族才这么傻!”
“怎么办哪!无套裤汉太聪明了,什么也没给别人留下。”
“嘘!我的酒来了。”
“今晚在附属监狱对面见。”
“好。”
爱国者付了自己那份帐,走了出去。
从门口传来了他那雷鸣般的吼叫声:
“快,女公民!黄瓜猪排!我的表弟格拉居斯饿死了。”
“好样的马尔道什。”狱卒边啜酒边说道;酒店女主人刚刚为他斟了一杯名葡萄酒,并且温情地在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