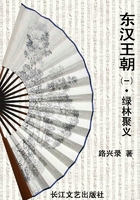第39章一束紫罗兰 (1)
读者不难预见,在藏匿热纳维也芙和莫里斯的这个如此温暖的小屋里,是不可能长时间保持平静的。
狂风暴雨,雷鸣电闪之中,鸽子的小巢与隐藏它们的大树一齐晃动起来。
热纳维也芙又为另一个人操起心来,现在她不再担心红屋骑士,而是为莫里斯惶惶不安了。
她很了解她的丈夫,她心里明白,既然他失踪了,说明他得救了;她料定丈夫得救,就轮到为自己发抖了。
在那个似乎没有胆小鬼的年代里,也不敢把她的心事说给最胆大妄为的人听,然而她那红红的双眼和苍白的嘴唇还是流露出她心事重重。
一天,莫里斯轻手轻脚地转回家,其时,热纳维也芙正想入非非,没听见他进门。莫里斯在门口站住,看见热纳维也芙坐着一动不动,目光呆滞,双手无力地平摊在膝上,脑袋垂落在胸前,她正走神。
他带着深深的忧虑看了她好长一会儿,因为少妇心里在想什么,他也一清二楚,仿佛他对她的内心洞若观火一般。
他向她迈进一步,对她说道:
“您不喜欢法国,热纳维也芙,向我承认吧。您甚至对这儿的空气也避之不及,而您走近窗子向外边看时,也会恶心的。”
“呵!”热纳维也芙说道,“我明白我的想法瞒不了您;您猜对了,莫里斯。”
“可这是个美好的国家,”年轻人说道,“眼下的生活很有意义,也很充实:法庭上,俱乐部里和谋反者都在积极而紧张地活动,反衬了家庭生活格外温馨。在回家的路上,人们的心里热情洋溢,又带着明天不能再爱的一点恐惧,因为明天也可能活不成啦!”
热纳维也芙摇摇头。
“这是一个无法效忠的无情无义的国家!”她说道。
“什么意思?”
“嗯,您为这个国家的自由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如今,你不也受到怀疑了吗?”
“可是您,亲爱的热纳维也芙,”莫里斯说道,目光里充满着怜爱,“您是这种自由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您对它坏事做尽,然而现在您还不是安安静静,无忧无虑地在一个共和分子的家里睡大觉么!您瞧,扯平了吧。”
“是的,”热纳维也芙说道,“是的;可这个局面维持不了多久,因为不公平的事都长不了。”
“此话怎讲?”
“我想说,我是一个女贵族,我做梦也在希望您的主张失败和您的思想体系崩溃;我甚至在您的家里还在幻想着旧秩序的回归;至少按照你们的理论,我一旦被认出来,就会让您丧命和蒙受耻辱;莫里斯,我不会像个幽灵似的在这里住下去的,我不能把您引向断头台。”
“您到哪儿去呢,热纳维也芙?”
“到哪儿去?等哪一天您出门了,莫里斯,我就去自首,也不说出从哪里来的。”
“啊!”莫里斯从内心发出叫喊,“已经忘恩负义啦。”
“不是,”少妇把胳膊搂住莫里斯的颈脖说道,“不是的,我的恋人,最忠诚的恋人,我对你起誓。我不希望我的兄弟像一个谋反者那样被抓住,处死;我不希望我的情人像叛徒那样被抓住,处死。”
“您真会这么去做,热纳维也芙?”莫里斯大声问道。
“真得与天堂上有一个天主一样!”少妇答道,“再说,惧怕已不足道,我只有悔恨。”
说着,她垂下了头,仿佛悔恨重得难以承受似的。
“啊!热纳维也芙!”莫里斯说道。
“您现在明白我说的,特别是我经受住的考验了吧,莫里斯,”热纳维也芙继续说道,“因为这种悔恨,您也有……您知道,莫里斯,我献出我自己,并不等于我拥有自己;您得到我并不等于我有权献出啊。”
“行啦!”莫里斯说道,“行啦!”
他的额头蹙起了皱纹,他那如此明澈的目光里流露出决心已下的光彩。
“我将会向您表明,热纳维也芙,”年轻人继续说道,“我只爱您一个人,我将向您证明,任何牺性与爱情都不能相提并论。您憎恨法国,那行,我们就离开它。”
热纳维也芙合起双手,看着他,炽热的目光充满了敬佩之情。
“您没骗我吗,莫里斯?”她讷讷地问道。
“我什么时候欺骗过您啦?”莫里斯问道,“莫不是我为得到您而名誉扫地的那一天吧?”
热纳维也芙把嘴凑近莫里斯的嘴,久久地搂着他,如同悬挂在她情人的颈脖上似的。
“是的,您说得对,莫里斯,”她说道,“是我想错了。我所感受到的,不再是悔恨,也许是灵魂的堕落。而您,至少您是理解的,我太爱您啦,除了害怕失去您以外不可能有另一种感情。让我们远走高飞吧,我的朋友;到那任何人都找不到我们的地方去。”
“啊!谢谢。”莫里斯喜不自胜地说道。
“可怎样逃跑呢?”热纳维也芙想到这里,又紧张地问道,“当今,人们再也不能轻而易举地在9月2日杀人犯的屠刀和1月24日屠夫的斧钺下溜掉了。”
“热纳维也芙!”莫里斯说道,“天主保佑我们。听着,您刚才说到了9月2日,说到那一天,我做了一件好事,今天该得到补偿了。我曾想拯救出一位教士,他是我的同窗旧友。我跑去找丹东,在他的斡旋下,公安委员会为这个不幸的人和他的妹妹签署了一份护照,丹东亲手把护照交给了我。可是,不幸的教士非但没如我所说的到我那里要护照,而是把自己关进加尔默罗会修道院(又称圣衣会,中世纪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之一,靠募化为生。),并且死在那里面了。”
“那么护照呢?”热纳维也芙问道。
“我一直留在身边;今天价值百万法郎,可它不止值这些,热纳维也芙,它与生命,与幸福同价。”
“哦!我的天主啊!我的天主啊!”少妇大声说道,“保佑我们吧!”
“我的财产,你也知道,就是一座庄园,现在由一老仆照看,他是个纯洁的爱国者,诚实的人,我们完全可以信赖。他会托人把我的进款送到我指定的地方去的。去布洛涅港的路上,我们要经过他那里。”“那么他住在哪儿?”
“在阿布维尔附近。”
“我们何时动身,莫里斯?”
“再过一小时。”
“可不能让人知道我们走了。”
“没人知道的。我先到洛兰家去,他有一辆马车但没马!而我有一匹马而没车厢;我回来后就动身。你呢,你呆在这儿,热纳维也芙,准备一下出发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多少行李,到了英国可以再买么。我马上吩咐斯赛伏拉办一件事,把他支开,今晚,洛兰会告诉他我们走了,届时,我们已经走得远远的了。”
“如果在半路他们抓到我们呢?”
“我们不是有护照么?我们到乌贝尔家去,乌贝尔就是我说的管家的名。从阿布维尔到布洛涅港一路上,他一直陪伴并护送我们,到了布洛涅港,我们买或是租一条船。再说,我也可以到委员会去,让他们给我一个去阿布维尔的差事算了,别再虚伪了,是么,热纳维也芙?我们宁愿冒生命危险去争取幸福。”
“对,对,我的朋友,我们会成功的。你今天早上好香呀,我的朋友!”少妇说道,把脸藏在莫里斯的怀里。
“不错,早上,我经过平等宫时,为你买了一束紫罗兰,可我进门时,看见你如此伤心,只顾问你伤心的原因了。”
“啊!快把花给我,我会还你的。”
热纳维也芙狂热的嗅着花香,几乎所有生性敏感的人对花香都有偏好。
突然,她的眼睛里涌满了泪水。
“怎么啦?”莫里斯问道。
“可怜的爱洛绮斯啊!”热纳维也芙喃喃道。
“啊!是啊,”莫里斯叹息道,“还是想想我们自己吧,亲爱的朋友,死者嘛,无论他们属于哪个党派,就让他们在‘效忠’为他们挖掘的墓穴里安息吧。再见!我走了。”
“快回来。”
“要不了半小时,我就来了。”
“如果洛兰不在家呢?”
“有什么关系!他的仆人认识我;我在他家可以随意拿东西,他不在一样,他在这里不也是这样吗?”
“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