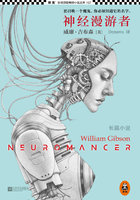第38章王子
在前一章里,读者已经知道,审理王后一案已经进入议题了。
隐隐约约可以看出,假如牺牲这一颗高贵的头颅,群众日益增长的仇恨情绪将会得到平息。
欲使这颗人头落地的方法是不缺的,不过握有生杀大权的检察长富纪埃-坦维尔决定采用新的指控手段,这是西蒙答应为他提供的。
西蒙与他在法院大厅碰面的次日,武器的击撞声又在寺院监狱里响起,让那些坐牢的王族囚犯们心惊肉跳。
这些囚犯便是伊丽莎白夫人、公主和那个孩子,那孩子在摇篮里时就被称为“陛下”,现在只是被称为小路易卡贝。
昂里奥将军(昂里奥(1761-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无套裤汉分队首领,后被任命为巴黎国民卫队临时总指挥,最后上了断头台。)戴着三色羽翎帽,骑着高头大马,腰佩长剑,在几个国民卫队队员的簇拥下走进主塔堡,王子在里面已奄奄一息了。
在将军身边走着一个书记员,一脸奸相,手执一个墨水盒、一卷纸和一杆长得过分的羽笔。
走在这个书记员后面的就是检察长了。我们已经见过他,现在正逐渐对他加深认识,以后还会发现这个脸色发黄、冷酷无情的人的那布满血丝的眼睛,甚至使全副武装、勇猛异常的桑代尔本人见了也心颤胆跳。
他们身后跟着几名国民卫队队员和一个伍长。
西蒙假惺惺地笑着,一手拿着一顶熊皮无檐帽,另一只手拿着鞋匠的专用皮条,走在前面为委员们指路。
这一些人来到一间空荡荡的黑屋里,少年路易坐在房里端的床上,木然不动。
当时,我们看见可怜的孩子在暴怒的西蒙面前逃窜时,身上还存在着生命的活力,能与寺院监狱里的鞋匠给的不公正待遇进行抗争,他逃跑、叫喊、哭泣;这说明他害怕,他难受,他同时也在希望着。
如今,惧怕与希望同时消失了;当然啦,痛苦仍然存在;不过,倘若说它仍然存在的话,这个苦命的孩子只是把它埋在内心最深处,摆出完全漠然无知的样子来掩饰罢了。人们是以多么残忍的手段让这孩子来为他的父母赎罪啊!
委员们向他走去时,他连头都不抬。
这些人二话不说就拣位置坐下。检察长坐在床头,西蒙坐床尾,书记员临窗,国民卫队队员和他们的伍长坐在一边的稍暗处。
他们都带着某些兴趣与好奇看着小囚徒,其中一些人发现孩子脸色不好,胖得不正常,其实那是浮肿,他的双腿弯曲,说明关节已经开始肿胀。
“这个孩子病得挺重。”伍长肯定地说道;这时,富纪埃-坦维尔正准备坐下提问,听见这话回过头来。
小卡贝抬起头,在微明中寻找说这话的人,他认出此人就是那天在寺院监狱的院子里不让西蒙揍他的那个人。在他深蓝色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线温和而有神的光芒,然而瞬息即逝了。
“啊!啊!是你,洛兰公民。”西蒙说道,借此提醒富纪埃-坦维尔注意到他是莫里斯的朋友。
“是我,西蒙公民。”洛兰以惯有的沉着与冷静的声调答道。
虽说洛兰是个临危不惧的人,但他也决不会作出无谓的牺牲,于是他便利用这次机会向富纪埃-坦维尔套近乎,后者亦以礼相待。
“我想,公民,”这时检察长说道,“你指出孩子病了,难道你是医生么?”
“我不是医生,但至少我研究过医学。”
“那么你觉得怎样?”
“说说病征么?”洛兰问道。
“是的。”
“我觉得他的双颊和眼睛浮肿,双手白而瘦,双膝肿胀;倘若我搭他的脉,我肯定,他的脉搏每分钟至少跳动八十五到九十下。”
孩子似乎对旁人列数他的病状毫无兴趣。
“对犯人的病状,医学上怎么说呢?”检察长问道。
洛兰搔搔鼻端,自言自语道:
“费利斯想要我开口,
我没有一点胃口。”
然后又说出来:
“天哪,公民,”他答道,“我解决不了小卡贝的饮食,没法回答你……不过……”
西蒙在认真听着,看见他对头正在牵累自己而窃窃自喜。
“不过,”洛兰继续说道,“我觉得他缺少锻炼。”
“这个小家伙呀!”西蒙说道,“我认为他不再肯走路了。”
孩子对鞋匠的斥责无动于衷。
富纪埃-坦维尔起身,走向洛兰,向他耳语几句。
没人听清检察长在说什么,但可以看得出,他是在询问着什么。
“哦!哦!你这么认为,公民,这对一个母亲来说太严重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就会知道的,”富纪埃说道,“西蒙声称亲耳听他说起过,并且保证能让他说出这件事。”
“如果这样就太丑恶了,”洛兰说道,“但这有可能:那个奥地利女人肯定有罪;不过是是非非与我无关……他们已经把她说成了是麦莎琳(麦莎琳,公元48年死于罗马,罗马皇后,对其丈夫春洛德皇帝有绝对权威,并以淫荡著称。最后被皇帝派人暗杀。)第二,但还不满足,还想把她说成是另一个阿格里宾纳(阿格里宾纳,尼禄之母,骄横拔扈,最后把自己的丈夫亦是她的叔叔——春洛德皇帝毒死。),我看有点儿过分了,我承认。”
“西蒙是这样报告的。”富纪埃不动声色地说道。
“我不怀疑西蒙说的这些……总有些人对任何性质的指控都不怕,甚至是不可想象的指控……”洛兰死死盯着富纪埃继续说道,“你是一个聪明而正直的人,说到底是一个坚强有力的人,你不认为向一个孩子去询问这些细节,询问这些最天然的法则,询问大自然最神圣的法则命令他必须尊重的细节,是在借孩子辱没整个人类吗?”
检察长连眉都没皱一下,他从口袋里掏出记事本,递给洛兰看。
“国民公会命令我调查,”他说道,“其他我管不着,我只是调查。”
“没错,”洛兰说道,“倘若这个孩子承认了,承认……”
年轻人厌恶地摇摇头。
“再说,我们也不会完全依据西蒙的揭发进行审理;你知道,法庭是公开的。”
说着,富纪埃又从他的口袋里掏出第二张纸。这张纸便是埃贝尔(埃贝尔(1757-1794):法国记者。他创刊的《杜谢斯勒老爹》报纸,实际上成了大革命时期极端革命派的代言人。)主编的名为《杜谢斯勒老爹》的一期报纸。
果真,诉状在上面用大字号发表了。
“写着哩,甚至印出来了。”洛兰说道,“无论如何,只要这样的控诉不是从孩子的嘴里说出来的,我说,是自愿的、自由的、毫无威胁的情况下说出来的……那么……”
“怎么样?”
“那么,虽说有西蒙和埃贝尔的诉状,我像你一样,还是不能肯定。”
西蒙不耐烦地等待着这场谈话的结果;这个恶棍还不了解聪明人在众人身上攫获一个眼光所产生的力量:产生同情或是仇恨。有时,这是一种推力,有时又是一种引力,泄露了对方的真情和人格,以致他承认此人确比其他人略胜一筹。
富纪埃是感觉到洛兰这目光的分量的,也希望能被这个旁观者所理解。
“审讯就要开始了,”检察长说道,“书记员,拿出笔来。”
书记员刚写完审讯记录的开场白,与西蒙,与昂里奥,总之与所有人一样在等着富纪埃一坦维尔和洛兰之间的这场谈话结束。
只有孩子一个人似乎对眼下的一切完全漠然处之,其实他才是主角,他的眼睛方才闪过一道智慧的目光,此刻又变得呆滞了。
“安静!”昂里奥说道,“富纪埃一坦维尔公民就要审讯孩子了。”
“卡贝,”检察长说道,“你知道你母亲现状如何么?”
小路易的脸色由惨白而变成猩红。
但他不予回答。
“你听见我说的话么,卡贝?”检察长又问道。
还是沉默。
“啊!他听得很清楚,”西蒙说道,“不过他像猴子一般狡猾,他不愿回答,因为他害怕别人把他当成大人,让他去劳动。”
“回答,卡贝,”昂里奥说道,“现在是国民公会委员们在审问你,你应该服从法律。”
孩子的脸色变白了,但还是拒不回答。
西蒙做了一个狂怒的动作,对于粗暴而愚蠢的人来说,愤怒便是醉态,带着酒精中毒者的一切丑陋的征象。
“你不想回答么,狗崽子!”他说着向他伸出拳头。
“住嘴,西蒙,”富纪埃一坦维尔说道,“你没发言权。”
这句话他是在革命法庭上常说的,现在又漏出了嘴。
“你听见了么,西蒙,”洛兰说道,“你没发言权,这是别人当着我的面第二次对你说这样的话了;第一次,是在你起诉迪松大娘的女儿时,你想煽动别人把她的头割掉。”
西蒙不开口了。
“你的母亲爱你么,卡贝?”富纪埃问道。
还是沉默。
“有人说不爱。”检察长继续说道。
孩子的嘴唇上掠过了一丝苦笑。
“可是我对你说,”西蒙怒吼道,“他对我说过,她太爱他了。”
“瞧,西蒙,小卡贝与人单独在一起时话很多,当大家的面就沉默不语了,这有点儿不正常。”洛兰说道。
“啊!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就好了!”西蒙说道。
“是啊,如果只有你们两个人就好了,可不巧的是你们不是两个人。啊!如果只有你们两个在一起,勇敢的西蒙,优秀的爱国者,你就会殴打这可怜的孩子了,是吗?可你不是一个人,你不敢撒泼。这里我们都是有教养的人,我们懂得古人尊重弱者,我们也应该效仿,因此,当着我们的面你不敢,就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在场;我的大活宝啊,倘使在你面前的是个身高五尺六寸的孩子,你就不敢动手了。”
“啊……”西蒙咬牙切齿地咕哝道。
“卡贝,”富纪埃接着又说道,“你对西蒙说过什么心里话么?”
孩子的目光里明白无误地流露出难以描述的讥讽神色。
“有关你母亲的?”检察长继续问道。
孩子的目光里闪过一丝轻蔑的光。
“回答的还是不是。”昂里奥嚷嚷道。
“回答是!”西蒙向孩子举起皮条,吼叫道。
孩子打了一个哆嗦,但没挪动一下身子以避免挨打。
在场的人一齐发出了反感的斥责声。
洛兰更近一步,在西蒙的手臂尚未落下之前,已冲上前去抓住他的手腕。
“你放不放?”西蒙脸上气得发紫,怒喊道。
“嗨,”富纪埃说道,“母亲爱自己的孩子没什么不好的;卡贝,告诉我们你的母亲是如何爱你的。这对她可能有所帮助。”
小囚徒想到这样可能对母亲有所帮助,悸动了一下。
“她像爱一个亲孩子那样爱我,先生,”他说道,“母亲爱孩子与孩子爱母亲一样,并不存在两种方式。”
“什么,小恶棍,你对我说过,你的母亲……”
“你不是在做梦吧,”洛兰平静地打断他的话说,“你大概常做恶梦,西蒙。”
“洛兰!洛兰!”西蒙咬牙切齿地说道。
“怎样,说呀,还有呢!没有法子去揍洛兰,因为只有他揍那些坏人的份儿;没有法子揭发他,因为他刚刚才拉住了你的胳膊,而且是当着昂里奥将军和富纪埃一坦维尔公民的面拉的,他们赞同这个举动,但他俩可不是温和派啊!也没有法子让他像爱洛绮斯?迪松那样上断头台;真让人生气,甚至让人发病,但事实又是如此,可怜的西蒙啊!”
“走着瞧!走着瞧!”鞋匠像豺狼般地狞笑道。
“好啊,亲爱的朋友,”洛兰说道,“我希望借助天道!……啊!你早料到我要替天行道了?我希望求助天主和我的宝剑首先为你开膛破肚,不过,西蒙,站开,你挡住了我的视线。”
“匪徒!”
“住口!你影响我的听力。”
洛兰逼视着西蒙。
西蒙紧攥着拳头,拳头上的黑褐色的斑斑点点很使他自豪,不过如同洛兰所预料的,他的能耐也就局限于此了。
“现在他开始说话了,”昂里奥说道,“他大概会说下去;继续审问吧,富纪埃公民。”
“你现在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吗?”富纪埃问道。
孩子又沉默不语了。
“你瞧,公民,你瞧!”西蒙说道。
“这个孩子执拗得古怪。”昂里奥说道,他看见王子如此坚定沉着,不禁有点儿迷茫了。
“他被人教坏了。”洛兰说道。
“谁?”昂里奥问道。
“还用说,他的监护人呗。”
“你指控我?”西蒙嚷嚷道,“你告发我?……哦!有点莫名其妙……”
“我们要对他温和些。”富纪埃说道。
这时,他转身面向孩子,孩子仿佛完全失去知觉。
“嗨,我的孩子,”他说道,“请回答国家委员所提的问题;你拒绝澄清对你有利的事实,会使情况变得更糟;你对西蒙公民说过你母亲对你的疼爱,以什么方式爱你,以她独有的方式爱你,是么?”
路易向在场的人一一扫视了一遍,当他看到西蒙时,目光里充满了仇恨,但他绝不开口。
“你觉得难受么?”检察长问道,“你觉得住得差,吃得差,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么?你希望有更多的自由,改变生活方式,换一所监狱,换一个监护人么?你想要一匹马遛遛吗?你想和一群同龄的孩子一起玩吗?”
路易就是不作声,他只有在维护自己的母亲时才开口。
委员们都惊呆了;如此坚毅,如此聪慧,体现在一个孩子身上简直不可思议。
“哼!这些皇亲国戚,什么种啊!”昂里奥轻声咕哝道,“都是些狮虎之辈,从小就变坏了。”
“如何笔录口供?”书记员尴尬地问道。
“留给西蒙去办吧,”洛兰说道,“现在没法写,他会处理得很好的。”
西蒙向他那死对头伸伸拳头。
洛兰笑了起来。
“等那天你在袋子里(指断头台边盛人头的袋子。)打喷嚏时,就不会像这样笑了。“西蒙说道,他已气昏了头。
“你说的那个小小的过门,我不知道在你之前还是之后去履行,”洛兰说道,“我所知道的,就是轮到你的那天,许多人会笑。天主们哪!……我说天主时用的是复数!天主们哪!那天,你是多么丑陋呵,西蒙!你那时太可憎啦。”
说完,洛兰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跟在委员后面走了出去。
委员们既然无事可干,也就离开了监狱。
孩子呢,他一旦摆脱了审讯者,就在床上哼起了一首伤感的小调,那是他父亲生前喜爱的一首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