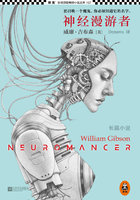第36章戴奥道尔公民
黑夜以它那灰色的大幕包住了这间硕大无比的大厅,这个大厅永远回荡着律师尖锐的辩词和诉讼人哀怜的申诉。
黑暗之中,在右首,依稀可见一根白色的柱子,它似乎一动不动地守在大厅中央,如同保护这块圣地的幽灵。
在黑暗中惟一能听到的声音,便是耗子的啮咬声,它们先是啃啮小书记员们的小隔间,然后又啃啮锁在里面的文件资料。
间或还可听到马车钻进被某个院士称之为泰米斯(泰米斯在希腊神话中是司正义与秩序之神。)殿堂的声音,以及似乎从地下钻出来的钥匙的咯咯声,但这一切仿佛都是天外来音,微弱的声响只能更增加寂静的氛围,就如远处的灯光使近处的黑暗更浓更黑一样。
这座宫殿的大厅的外墙上还沾着九月大屠杀牺牲者的斑斑血迹,就在当日,二十五个人被判以极刑的从楼梯上走下来,大厅的后面地下仅几法尺深处,便是附属监狱的死囚牢房,里面堆满了白花花的尸骸。不言而喻,此刻如有谁胆敢呆在那里,定会吓得魂飞魄散的。
然而,就在这恐怖之夜,在这几乎是庄严肃穆的沉寂之中,传来了轻微的声响。书记员的一个木质隔间的门咯咯转动了。一个比夜的幽灵更加黑的影子悄悄地钻出隔间。
那个书记员低声称之为“先生”,而他本人却自称为戴奥道尔的狂热的爱国者蹑手蹑脚地在高低不平的石板地面上潜行。
他的右手拿着一根粗大的铁橇棒,左手压着腰带上的双筒手枪。
“从那个小隔间起数至第十二块石板,”他喃喃自语道,“嗯,这是第一块的端点。”
他一面计数,一面用脚尖去碰触石板缝,年代久远,石板缝之间开裂了。
“嗨,”他停下来自语道,“我测量得准确吗?我会坚强起来么,她呢,她有足够的勇气么?啊,是的,她的勇气我素来敬佩。呵!天主啊!当我握住她的手,对她说:‘夫人,您得救了!’……”
他站着不动了,仿佛被这沉沉的希望压垮了似的。
“啊!”他接着自语道,“‘这是多么大胆而不可思议的计划啊!’那些钻进被窝,或是只是化装成仆人在附属监狱周围徘徊的人才会这样说,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我敢作敢为的气魄,那是因为我不仅想救王后,而且主要是想救那个女性。
“行了,干吧,再把步骤温习一遍吧:
“撬起石板,这没什么;让洞穴开着,这就有点儿危险了,可能有人要来巡逻……不过,不会有人巡查的。我没引起他们怀疑,因为我没有同谋,再说,像我这样心急火燎的人也无需花多少时间穿过这条阴暗的走廊吧!我只消三分钟就钻到她的住房下面了;再用五分钟,我就撬起壁炉内膛的砖块;她会听见我干活的声音的。她胆识过人,决不会害怕的。相反,她会明白,拯救她的人来了……有两个人看守她,当然这两个人要跑过去……
“嗯,不就两个人嘛,”爱国者冷冷一笑,瞧瞧腰间和手里的武器,“两个人,只需两声枪响,或是两家伙撬棍。可怜的人哪!……啊!不是还有许多人都死于非命了吗,他们并没有犯法啊。
“干活吧!”
说着,戴奥道尔公民把撬棍有力地插进两块石板的缝隙之间。
正在这时,一道强烈的光像石板上出现一条金色沟渠似的照射了进来,穹顶下回声阵阵,阴谋者掉转身子,他一个箭步,又返回蹲在小隔间里了。
不多会儿,远远地传来了微微的说话声,那是人们夜间呆在巨大建筑物里习惯压低嗓门的缘故。
他弯下身子,透过木板缝,起先看见一个穿军服的人,他那柄佩剑在石板上铿锵作响,引起了他的注意;接下,他又看见一个身穿松子色上装的人,他手上拿着一把尺子,腋下夹着一卷纸;第三个穿着宽大的花呢短大衣,头戴毛皮里子的无檐帽,最后是第四个,脚套木履,身穿紧身短上衣。
大铁栅门嘎嘎转动,套上了白天系住大门的铁链。
四个人走了进去。
“巡逻的,”戴奥道尔咕哝道,“天主保佑!如提前十分钟,我就完了。”
接着他聚精会神地去辨认执行巡逻的那几个人。
他认识其中三个。
走在前面,穿着将军服的是桑代尔;身穿花呢短大衣,头戴毛皮无檐帽的是看门人理查德;拖木履,短装装束的也许是狱卒。
可他从未见过那个穿松子色上装,手拿尺子,腋夹卷纸的人。
这个人是谁呢?晚上十点钟,公社将军,附属监狱的门卫、狱卒和那个不认识的人到法院大厅来干什么呢?
戴奥道尔公民单膝跪着,手上握着子弹上膛的手枪,另一只手把帽子戴正了,因为方才动作过于匆忙,头发散乱开来。
这四个夜巡人一直默不作声,或者说,阴谋者根本就听不见他们的说话声。
不过,这一行人走到距他藏身处十步远时,桑代尔开口了,他的声音明白无误地让戴奥道尔听清了。
“嗯,”他说道,“我们来到法院候审大厅了,现在该你指路了,建筑师公民,请别说废话;你也知道,革命使人间无奇不有,地道与人的思想一样,我们都不相信。你说呢?理查德?”桑代尔转向戴皮帽穿呢大衣的人问道。
“我从未说过在附属监狱下面有地道,”那人答道,“格拉居是狱卒,十年前就来了,因此他对附属监狱了如指掌,可是他还不知道有一条像吉罗公民说的那样的通道哩。不过既然吉罗公民是本城的建筑师他该了解得比我们多,这是他的职业嘛。”
戴奥道尔听到这些话,浑身直打哆嗦。
“可幸的是这个厅足够大的,”他心里想道,“他们要找着地道至少得花两天工夫。”
然而建筑师打开了他那一卷纸张,戴上眼镜,跪下,格拉居斯手上提着一盏灯,他就借着摇曳不定的光,仔细地研究图纸了。
“我担心吉罗公民在说梦话。”桑代尔叽叽咕咕地说道。
“你会看见的,将军公民,”建筑师说道,“你会看见我是否是在做梦;等一下,等一下。”
“嗨,我们不是在等着么。”桑代尔说道。
“那就好。”建筑师说道。
接着他就计算起来:“十二加四等十六,”他说道,“再加八二十四,除以六,等于四;除此之外,还剩下一半;对了,我们找到地方了,假如我有一法尺的误差,你们就说我不懂装懂好啦。”
建筑师说这番话时语气十分坚定,使戴奥道尔公民心凉了半截。
桑代尔不无虔诚地瞧着地形图,看得出来,他因为根本不懂而更加笃信。
“请你仔细听我说。”
“究竟在哪儿?”桑代尔问道。
“在我画的这张地形图上,喔!您看见没有?离墙十三法尺处,有一块活动地砖,我在上面标上了A记号。您瞧见了么?”
“我当然看见一个A啦,”桑代尔说道,“难道你以为我不识字吗?”
“在这块地砖下面有架梯子,”建筑师继续说道,“瞧,我在上面标上了B。”
“B,”桑代尔重复道,“我看见一个B了,可没看见梯子。”
说完,将军对自己的戏谑话,放声大笑起来。
“一旦地砖起来出来,就往下走,下到最后一级梯级,”建筑师接着说道,“然后以每步间距三法尺的跨度走五十步,再往上面看看,您发现就在登记室的中心位置上,那便是端点,而地道已经通过了王后的囚室。”
“你是说卡贝寡妇吧,吉罗公民。”桑代尔皱眉,冷冷地讥讽道。
“啊,是的,卡贝寡妇。”
“但你刚才说了王后。”
“习惯未改嘛。”
“您说,这样我们就到了登记室了?”理查德问道。
“不仅到了登记室地下,而且我还要对您说,我们要去登记室的哪个位置,是在壁炉下面。”
“嗯,是有点儿怪,”格拉居斯说道,“说真的,每一回我把木薪扔在这个地方,地砖就发出回声。”
“假如我们当真找到你所说的那件东西,建筑师公民,我得承认几何学功德无量了。”
“那么你就承认吧,桑代尔公民,因为我马上就领你到标上字母A的地点去。”
戴奥道尔公民把指甲深深地嵌进皮肉里。
“如果我看见了,如果我真的看见了,”桑代尔说道,“我就是圣徒托马斯(《圣经》里的十二使徒之一,他在摸到耶稣督的伤疤之前,不相信耶稣复活了。)了。”
“哦!你说圣徒托马斯吗?”
“哎呀,是的,就如你说王后一样,是习惯嘛;不过别人不会指控我与圣徒托马斯合谋叛变的。”
“我也不会与王后合谋。”
建筑师说完这句话,就小心翼翼地拿起尺,丈量起来,他自以为作出精确计算之后,就敲打地砖。
这块地砖恰巧就是戴奥道尔公民怒气冲冲地敲打的那一块。
“就在这里,将军公民。”建筑师说道。
“你真这么想,吉罗公民?”
在小隔间藏身的爱国者居然失去理智,他紧攥拳头在自己的臀部狠狠揍了一拳,沉沉地吼了一声。
“我坚信不疑,”吉罗又说道,“您的鉴定附上我的报告将会向国民公会证明,我没有弄错,是的,将军公民,”建筑师夸张地说道,“这块地砖下面就是一条地道,通向登记室,并且经过卡贝寡妇的囚室。把这块地砖撬起来,跟我走下地道,我就会向您证明,只需两个人,甚至一个人,在一夜间就会人不知鬼不觉地把她劫走了。”
建筑师的话验证了,这几个人之间发出了一阵轻轻的惊喜和赞叹声,声音正好传到了戴奥道尔公民的耳朵里,他似乎变成了一尊泥塑木雕。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危险,”吉罗说道,“那么现在,假如我在地道里装一道栅栏,把地道拦腰截断,我也就拯救了祖国。”
“啊!”桑代尔说道,“吉罗公民,你的主意真不坏哩。”
“你入狱吧,双料傻瓜!”爱国者怒不可遏地咕哝道。
“请把地砖撬起来吧。”建筑师对格拉居斯公民说道,他除了手提一盏灯外,还带着一根撬棍。
格拉居斯公民开始干活,不一会儿,地砖就撬起来了。
果然,地道口暴露无遗,一架梯子直伸到纵深处,潮湿的空气从里面逸出,像一股混浊的水蒸气。
“计划又一次失败了!”戴奥道尔公民喃喃自语道,“啊!上天不愿意放她出来啊,可见此事断断不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