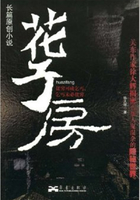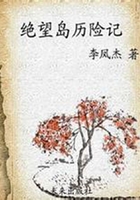第34章附属监狱 (2)
窗对面支起了一张床,窗口边上放了一把椅子,这就是王室监狱的全部家什了。
王后进入时请求把她的书和针线带给她。
狱卒把她在寺院监狱里开始看的《历次英国革命》、《年轻的阿那尔夏西斯漫游记》和她的刺绣交给了她。
宪兵们就在一板之隔的小间里安顿下来。历史留下了他们的名字,命运有时把最微不足道的人与历史上的大灾大难联系在一起,他们曾看见电光在他们身上闪耀了一下,可巨雷却把王座或是把国王本人击成了齑粉。
他俩分别叫杜谢斯纳和吉尔贝。
公社了解他们,知道他们是优秀的爱国者,所以指定了他俩,他们应该坚守岗位,直到玛丽—安托瓦内特受审为止。公社采取这个措施是为了避免因每天换几次岗而带来的几乎难以避免的麻烦。于是这两个看守便重责在身了。
从这天起,除非话题有所顾忌,非得压低嗓门才说不可的话,这两个人的谈话句句传入王后的耳朵,因此她从他们的交谈中知道了公社采取的这个措施,她既兴奋又不安。一方面,她心里揣摩这两个人大概是死心蹋地的爱国者,因为毕竟是在这么多人之间被选中的;另一方面,她考虑这样她的朋友们就会有更多机会去拉拢这两个只知呆在原位不动的看守,这总比腐蚀她身边百来个临时决定的、每天都在掉换的陌生人要容易些。
第一夜,一个宪兵在入睡前,又习惯地抽起大烟来了;烟味钻过隔板缝,包围住不幸的王后。然而恶运不仅没使她变得迟钝,反而使她更敏感了。
她很快被烟呛着,并且感到恶心。她的头因窒息而昏昏沉沉的,但她的忠于自己不可驯服的自尊原则,没发半句怨言。
夜深人静,当她在痛苦地熬夜时,似乎听见从外面传来的呜咽声凄厉而悠长,犹如令人毛骨悚然的凶兆,让人想起在狂风大作之夜,空寂的走廊里夹着风雨突然传来的唤起生命气息的人的声音。
她很快就辨别出这使她不寒而栗的声音,这痛苦而持续不断的叫声原来是一条狗在码头上的哀嚎。她立即便想到她那可怜的黑子;在她从寺院监狱被带走的一刻起,她一时把它忘了,眼下,她似乎又重温了它的声音。当时,这可怜的畜牲由于过分警觉,才失去了它的女主人的,那会儿,它悄悄地追随其后,一直跟在马车后面,直到附属监狱的栅栏前;女主人进去后两扇铁门关闭,差点儿把它轧成两半,它这才走远了。
不过,可怜的动物很快又转回来,它明白它的女主人被关进了这个巨大的石头墓冢里,便吠叫着呼唤她,在离哨兵十步远处,等待着她的温存的呼应。
王后轻叹了一声,引起看守的注意。
不过她只是叹了一口气,而且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房间里没发出其他声响,她的看守也就很快放下心来,又沉沉地睡去。
次日,曙光刚刚升起时,王后已起床,穿戴完毕。铁栅栏窗上筛下的道道蓝莹莹的日光,落在她的那双消瘦的手上,她坐在窗子旁边,看似在读书,其实思想已经从书本上飞出去了。
宪兵吉尔贝把屏风打开一点儿,默默地看着她。玛丽—安托瓦内特听见屏风擦着地板的移动声,但没回头。
她故意挑一个位置坐下,让宪兵能看见她的头完全沐浴在晨光里。
宪兵吉尔贝示意他的伙伴与他一起从缝口往里看。
杜谢斯纳走上前去。
“瞧,”吉尔贝轻声说道,“她的脸色多难看呀;真可怕!她的眼圈红通通的,表明她很痛苦,好像她哭过了。”
“你知道,”杜射斯纳说道,“卡贝寡妇从不哭泣;她不屑于此。”
“这么说,她是病了。”吉尔贝说道。
接着,他又提高嗓门问道:
“你说吧,卡贝女公民,你生病了吗?”
王后缓缓地抬起眼睛,她那明澈的目光在向他俩探询着。
“你们是在对我说话么,先生们?”她问道,语调里充满了柔情,因为她听出发问者的声调里有一丝同情的意思。
“是的,女公民,是在向你说话哩,”吉尔贝接着说道,“我们在问你,你是否生病了。”
“此话怎讲?”
“因为你的眼睛红红的。”
“而且你的脸色也不好。”杜谢斯纳补充道。
“谢谢,先生们。没有,我没病;只是昨夜我很难受。”
“啊,是的,你很悲伤。”
“不是,先生们,我一直是这么悲伤的,宗教告诫我把悲伤置于十字架下;我的悲伤哪天都一个样;不是的,我不舒服是因为我昨夜没睡好。”
“哦!房间变了,床换了。”杜谢斯纳说道。
“再说,住房也不漂亮。”吉尔贝补充道。
“也不是,先生们,”王后摇摇头说道,“对我来说,住处简陋或是华丽都无关紧要。”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
“是啊。”
“我说出来请你们原谅:我对这位先生此刻还在吐出的烟味很不适应。”
果然吉尔贝还在抽烟,他通常是烟不离手的。
“啊!我的老天哪!”他大声嚷嚷道,王后对他说话时柔声柔气的,使他变得飘飘然起来,“原来如此!你怎么不早说呢,女公民?”
“因为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妨碍你的习惯,先生。”
“那好,至少我不会妨碍你了,”吉尔贝说道,把烟斗在地砖上砸得粉碎,“因为我从此不再抽烟。”
说完,他转过身子,带走他的伙伴,把屏风又关严了。
“她有可能被割脑袋,这是国家的事情;可让这个女人受罪又有什么必要?我们是士兵,不是像西蒙那样的刽子手。”
“你的所作为有点儿贵族味儿,伙计。”
杜谢斯纳摇摇头说道。
“什么叫贵族味儿?喂,说来我听听。”
“这么说来,”吉尔贝说道,“就因为我不再用烟去呛卡贝寡妇,我就使国家受损了?行啦!你知道么,”这个正直的人继续说道,“我始终记得我对祖国立下的誓言和连队的命令,这就够啦。连队的命令,我熟记在心:‘别让女囚越狱,别让任何人接近她,切断一切她想接上或是保持的联系,坚守岗位,至死不渝。’这就是我的承诺,我一定照办不误。祖国万岁!”
“我对你说这些,并非是对你的看法,”杜谢斯纳接着说道,“恰恰相反,而是你如因此而受到牵连,我心里不好受。”
“嘘!有人来了。”
虽说他俩说话的声音低,但王后没漏听一句。囚禁生活使她的听觉倍加灵敏。
引起两个看守注意的声响是好几个人走近门来的脚步声。
门开了。
两个市政府人员走进来,后面跟着看门人和几个狱卒。
“喂,”他们说道,“女囚在哪儿?”
“在这儿。”两名宪兵齐声答道。
“她住得如何?”
“您看吧。”
说着,吉尔贝走向前敲敲屏风。
“什么事?”王后问道。
“公社来人视察,卡贝公民。”
“这个人心地不错,倘若我的朋友愿意……”玛丽—安托瓦内特心里想道。
“行啦,行啦,”市政府人员推开吉尔贝,径直走进王后的房间,“哪这么多的规矩。”
王后连头也不抬;看她那漠然的神态,别人可能会想,刚才发生的一切她既没看见也没听见,也还是在独身自守哩。
公社代表好奇地观察房间的每一样设施,敲敲木器、床,以及开向女囚院子的铁窗棂,并且再三呆嘱宪兵小心谨慎之后,走了出去,没向玛丽—安托瓦内特说一句话,而她似乎也没察觉他们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