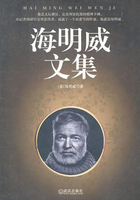第26章黑子
那个市政府人员走出去招呼他的同事,然后就阅看下班市政府人员留下的笔录了。
王后单独与她小姑和女儿在一起。
这三个人面面相觑。
公主投身到王后的怀里,紧紧抱着她。
伊丽莎白夫人走近她的嫂嫂,向她伸出手去。
“向天主祈祷吧,”王后说道,“声音放轻些,别让他们猜出我们在祈祷。”
有些荒诞的年代里,祈祷——天主赐于人的内心的自然颂歌,在有些人的眼里是可疑的,因为祈祷是希望和感激的举动。然而在看守人的眼里,希望或是感激是令人不安的根源,既然王后只能希望一件事情,那就是逃跑;既然王后只能感激天主一件事情,那就是为逃跑提供方便。
精神上的祈祷完毕后,这三人默默地呆着。
十一点钟敲响了,接着便是正午的钟声。
在最后一下钟声在铜钟上敲响时,螺旋形梯级上充斥着武器叮当声,喧嚣声一直上升,传到王后的耳中。
“哨兵换了,”她说道,“他们就要来找我们了。”
她看见她的小姑、女儿脸色变白了。
“中午到了,”塔下有人吼叫道,她掺杂着几乎恋恋不舍的感情,最后向黑色的墙,以及虽算不上粗俗,但至少相当简陋的家具扫了一眼,行了最后一个注目礼,因为这些都是她囚禁生活的伙伴啊!
第一道边门打开了,此门开向过道。过道黑乎乎的,在阴暗中,这三个女囚得以掩饰她们的情绪。小黑狗在前面跑着;可是,当她们走到第二道边门时,玛丽一安托瓦内特转移目光不愿看这道门,但是忠实的畜牲却把鼻子贴着上面的大头钉,悲伤地轻唤了几声,接下便是痛苦的长啸。王后挨着墙支撑着身子,匆匆而过,连呼唤小狗的力气也没有。
王后迈出几步,双腿发软,不得不停下来。她的小姑和女儿走近她,这三个女人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成了痛苦的一族,母亲把前额靠在公主的头上。
小黑猛然赶上了她们。
“怎么啦,”一个声音吼道,“她下还是不下?”
“她下来了,”市政府人员说道,他一直站着,对这深沉的痛苦以如此单纯的方式表现出来表示尊重。
“走吧!”王后说道。
她终于下塔了。
当女囚们下到旋梯下,面对着最生一道门时,太阳正钻过门缝,送进大束金黄的光芒,此时,只听得传来一阵鼓声,以示警戒,那沉重的门吱嘎嘎地转动着,慢慢地开启了。
一个女人坐在地上,更确切地说靠在门与石柱之间的旮旯里,她就是迪松大娘,王后已经二十四小时没看见她了,感到很惊讶,因为晚上和早上她们总要打照面好几次的。
王后已经看到阳光、树木和花园,她的目光越过以花园为界的栅栏外,贪婪地寻找着那间充当饭铺的陋屋,他的朋友大约在那里等着她;迪松妻子突然听见她的脚步声,松开了双手,这时王后看见她的一头灰发下面露出的一张苍白、失神的脸。
她的变化太大了,王后惊讶得站住不走了。
这时迪松妻子带着失去理性的人特有的缓慢动作,挨到那道门前跪下,挡住了玛丽一安托瓦内特的去路。
“您干什么,好女人?”王后问道。
“他说我得请求您的宽恕。”
“谁?”王后又问道。
“披大氅的男人。”迪松妻子答道。
王后惊讶地望着伊丽莎白夫人和公主。
“走开,走开,”市政府人员说道,“让卡贝寡妇走过去,允许她到花园里散步了。”
“我知道,正因为此我才来这里等她;他们不允许我上塔,而我又得请她饶恕,只能在这里等她。”
“为什么他们不让您上塔楼?”王后问道。
迪松妻子笑了。
“因为他们说我疯了!”她说道。
王后注视着她,发现在这个不幸的女人失神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奇特的光,迷茫的目光,这目光已经不受思想支配了。
“哦!我的天主呀,”她说道,“多可怜的女人哪!您发生了什么事情?”
“发生了……您不知道么?”迪松妻子说道,“啊不……您是知道的,因为她就是为了您才被定罪的。”
“谁?”
“爱洛绮斯。”
“您的女儿?”
“是的,她……我可怜的女儿!”
“定罪……谁定的?怎么回事?为什么?”
“因为卖那束花的是她。”
“什么花?”
“一束康乃馨……她本不是卖花女,”迪松妻子接着说道,仿佛努力搜索记忆似的,“她又怎么会卖那束花的呢?”
王后打了一个寒战,一根无形线把她所说的那个场面与眼前的现实联系起来;她明白,不该在这场徒劳的对话里浪费时间了。“好心肠的女人,”她说道,“我求您让我走过去,您以后再向我讲述这些事吧。”
“不,现在就说;您得原谅我,我要帮助您逃跑,那样他可以救出我的女儿。”
王后的脸色变得死人一样惨白。
“天主啊!”她抬眼望天,喃喃自语道。
接着,她向市政府人员转身子,说道:
“先生,请开恩把这个女人支开;您瞧他疯了。”
“走吧,走吧,大妈,”市政府人员说道,“闪开。”
可是迪松老婆紧贴着墙壁。
“不,”她又说道,“她得原谅我,好让那个人救出我的女儿。”
“她是谁呀?”
“披大氅的男人。”
“嫂嫂,”伊丽莎白夫人说道,“就对她说几句宽慰的话吧。”
“啊,很乐意,”王后说道,“确实,我以为这是最简便的办法了。”
她把脸转向疯婆子,问道:
“好女人,您想要什么?说吧。”
“我希望您原谅我因为对您的辱骂,对您举报而给您造成的痛苦;我希望您看见披大氅的男人时,命令他救我的女儿,因为他对您有求必应。”
“我不知道您说的披氅男人是谁,”王后答道,“不过,为了让您恢复平静,您如希望我原谅您所说的对我们的冒犯的话,啊,可怜的女人啊,我就真心诚意地原谅您,同时也希望受我冒犯的所有人同样能原谅我。”
“啊!”迪松妻子以一种不可言喻的轻快语调大声说道,“既然您原谅我了,他就会救出我的女儿。您的手,夫人,您的手。”
王后吃了一惊,莫名其妙地伸出手去,迪松老婆热情地抓住,把嘴唇凑了上去。
这时,宣读公告人的那嘶哑的嗓门传到寺院监狱的那条街上来了。
“听着,”他声嘶力竭地叫喊道,“受洛绮斯?迪松姑娘因犯叛国罪,被判以死刑!”
迪松老婆的耳朵里刚刚灌进这几句话,她的脸就变形了;她支起一条腿伸开双臂挡住王后的去路。
“呵,我的天主啊!”王后低语道,她听清了公告中的每一个字。
“被判以死刑?”做母亲的大声说道,“我的女儿被判决了?我的爱洛绮斯完了?这么说他没有救出她,根本不能救出她?太晚了吗?……啊……”
“可怜的女人,”王后说道,“请相信,我对您深表同情。”
“你?”她说道,双眼充血,“你,你同情我?决不会,决不会!”
“您想错了,我真心实意地同情您;可您得让我走过去啊。”
“让你走过去么!”
迪松妻子放声大笑。
“不!不!本来我想让您逃跑是因为他对我说过,假如我请求您原谅,假如我让你逃跑,我的女儿就会得救;可是既然我的女不在人世,你也跑不了啦。”
“帮帮我,先生们!来帮帮我,”王后大声说道,“我的上天啊!我的天主啊!瞧见么,这个女人确是疯了。”
“不,我没有疯,不;我知道我在说什么,”迪松妻子说道,“您看见了吗,真是那么回事,确有那么一个阴谋,是西蒙发现的,而我的女儿,我那可怜的女儿把那束花卖了。她在革命法庭招供了事实……一束康乃馨……里面有纸条哩。”
“太太,”王后说,“看在天主的份上。”
这时又传来了那人反复宣读公告的声音:
“爱洛绮斯?迪姑娘因犯叛国罪,被判以死刑!”
“你听见没有?”疯女人吼叫道,这时,她周围已经聚集了一些国民卫队士兵,“你听到么,处以死刑?这是为了你为了你,他们才要杀死我的女儿的,你听见么,为你,奥地利女人?”
“先生们,”王后说道,“以上天的名义!倘若你们不愿让我摆脱掉这个可怜的疯女人,至少得让我回到塔上去;我不能忍受这个女人的谴责,因为这些话全无道理,会把我气死的。”
王后转过脸去,痛苦地呻吟了一声。
“好,好,笑吧,虚伪的女人!”疯女人说道,“你的那束花让她付出了代价……再说,她本该料到这一着的;就这样,所有为你效力的人都死了。你带来灾难,奥地利女人:她们杀死了你的朋友、你的丈夫、你的保护者;最后还要杀死我的女儿。什么时候轮到他们杀掉你以使其他人不会为你去送死呢?”
多难的女人吼出最后几句话时,做了一个气势汹汹的手势。
“不幸的女人!”伊丽莎白夫人壮着胆子说道,“难道你忘了,你是在对王后讲话么?”
“王后,她?……王后?”迪松妻子重复道,她愈来愈神经错乱了,“如果她果真是王后,她就不准许刽子手杀我的女儿……她该宽赦我那可怜的爱洛绮斯……国王都是慈悲为怀的……好吧,把我的孩子还我,我就承认你是王后……否则,你只是一个女人,一个带来灾难的女人,一个杀人的女人!……”
“啊!行行好,太太,玛丽—安托瓦内特大声说道,“看看我有多痛苦吧,看看我的眼泪吧。”
说着,玛丽—安托瓦内特想试着走过去,她不再乞求能逃跑,而是出于本能,只是想避开这个死搅蛮缠的女人。
“哦,你过不去,”老太婆怒吼道,“你想逃跑么,维多夫人……我知道,披大氅的人告诉过我;你想去找普鲁士人……可你跑不了,”她继续说道,拽住了王后的裙袍,“我不许你这样做,哼!吊死你,维多夫人;准备战斗,公民们,前进……让不洁的血(这是法国国歌《马赛曲》中的一句歌词。)……”
这个命运不济的女人胳膊痉挛,灰白头发披散着,面色发紫,双眼充血,撕下了王后身穿的裙袍一角,翻倒在地上了。
王后惊慌失措,至少暂时摆脱了这个神经失常的女人;蓦地,只听得一声狂叫,还夹带着狗吠声和异样的喧嚣声,那些国民卫队的士兵从混沌状态中惊起,他们又看见眼下这个场面,就立即把玛丽—安托瓦内特包围起来了。
“准备战斗!准备战斗!叛变啦!”一个男人叫喊道,王后听出是补鞋匠西蒙的声音。
此人手拿着剑,守卫在茅屋门口,小黑狗在他旁边狂吠着。
“准备战斗,各就各位!”西蒙叫喊道,“有人出卖我们啦;把奥地利女人带回去。准备战斗!准备战斗!”
一个军官跑过去。西蒙对他说什么,双眼像是冒火,并向他指着小屋里面。军官也叫喊道:
“准备战斗!”
“黑子!黑子!”王后呼唤道,向前走了几步。
然而小狗没答理她,继续在狂吠。
国民卫队士兵纷纷拿起武器,向小屋冲,而市政府人员则抓住王后、她的小姑和女儿,强迫女囚们重新返回侧门,侧门随后就关上了。
“准备战斗!”市政府人员向哨兵叫喊道。
发出了子弹上膛的嚓嚓声。
“就在那儿,在那儿,盖子下面,”西蒙叫喊道,“我看见盖子在动,我确信无疑。再说,奥地利女人的那只小狗是条好狗,它没参与阴谋,它冲着叛变者叫来着,这些人也许在地窖里。啊,听哪,小狗在叫。”
果真,西蒙的叫喊声让黑子也激动不已,它叫得更加欢了。
军官勾住了盖环。两名身强力壮的掷弹兵看见他不能把盖子掀起来,前来帮忙,但还是掀不开。
“你们瞧,他们从里面拉住盖子了,”西蒙说道,“开火,打穿盖子,我的朋友,开火!”
“啊!”普吕姆大娘叫喊道,“你们会打碎我的瓶子的。”
“开火!”西蒙重复道,“开火!”“住口,唠叨婆!”军官说道,您拿几把斧子来,把木板砸开。现在,小分队作好准备,注意,一旦盖子砸开就开火。”
木板吱嘎响了一声,抖动一下,国民卫队士兵知道里面有所动作了。过了一会儿,地下传来了声响,仿佛一道铁闸门关闭了。
“加油!”军官向跑来的工兵说道。
斧子砸开板盖。二十来支枪口下移瞄准渐渐张开的洞口。可是洞里没有人。军官点燃一支火把,抛进地窖里,地窖是空空的。
大伙儿掀掉盖,这次没遇到任何抵抗。
“跟我来。”军官大声招呼着,率先冲下地窖梯级。
“前进!前进!”国民卫队士兵跟在他们军官后面边冲边喊道。
“啊!普吕姆大娘,”迪松说道,“你把地道借给贵族了!”
墙壁已穿通了。潮湿的地面上有许多脚印,一条三尺宽、五尺高的地道像一条堑壕似的通向绳街。
军官在洞里摸索着,决心追捕贵族,哪怕追到地心里也在所不惜;可是他刚刚迈进三四步,就被一道铁栏挡住了。
“停!”他对身后的人说道,“走不过去了,有东西挡着。”
“怎样,”市政府人员问道,他们把女囚关进去后,又跑出来打听消息,“有什么,说说看?”
“天啊!”军官探出身子说道,“有一个阴谋;贵族想在王后散步时把她劫走,也许她与他们暗中有勾结。”
“妈的!”市政府人员叫喊道,“快去向桑代尔公民报告,并且上报公社。”
“士兵们,”军官说道,“你们留在地窖里,谁出现就干掉谁。”
军官发出命令后,便又上来写报告了。
“哈!哈!”西蒙搓着双手大叫道,“哈!哈!谁还能说我是疯子?好黑子!黑子才真正的爱国者哩,黑子拯救了共和国。到这里来,黑子,快来!”这个土匪对那条可怜的小狗和声细气地引诱着,而当这条狗接近他时,他飞起一脚,把它踢到二十步开外。
“啊!我多么喜欢啊,黑子!”他说道,“你将让你的女主人人头落地。来这里,黑子,来呀!”
但这一次,黑子没有听从他,却叫着朝塔堡的方向奔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