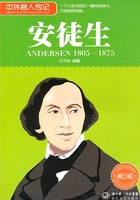第10章鞋匠西蒙
已是五月初了。澄净的天空下,一直呼吸着严冬冷雾而郁郁寡欢的人,大大舒了一口气,温暖而娇艳的阳光投射到寺院监狱那黑色的高墙上。
在花园和塔堡之间的一道边门口,站岗的士兵们在笑着,抽着烟。
天气晴朗,狱方恩准女囚可以下来在花园里散散步,但这三个女人拒绝了。王后自从丈夫处死之后,便执意呆在自己的卧室里,以免在三楼国王受拘禁的套间门口经过。
自1月21日(法王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日子。)那命中注定的一天过去之后,倘若王后有时也想透透气,爬到塔顶上去,狱方早用百叶窗把塔顶上的墙洞封死了。
值班的国民卫队士兵接到通知,这三个女人可以外出散步,他们等了一整天,期待她们能利用这次机会,但没等到她们。
将近五点钟光景,一个男人下塔来,走近值班班长。
“啊!啊!是你,迪松老爹!”这个外表看来生性乐观的士兵说道。
“嗯,是我,公民;我替你塔上的朋友,市政府的莫里斯?林代传一个口信,狱委员同意让我女儿今晚来看她的母亲。”
“你的女儿马上就要来,而你怎么倒要出去了,这不是有悖父爱的天性么?”下士长说道。
“唉!我这是迫不得已,下士长公民。我也希望看看我那可怜的孩子,我有两个月没看见她,没亲亲她了。可是现在,他们又让我出去。我有这差事,这倒霉的差事在身,不得不出去啊。我得去公社汇报。有一辆马车和两个宪兵在大门口等我,唉!恰巧我可怜的索非要来。”
“不幸的父亲啊!”下士长说道,
“对祖国的爱,
扼杀了你的骨肉之情,
一个在呻吟,另一个在祈祷,
尽心尽责才是真谛……
呃,迪松老爹,如果偶尔你找到‘ang’音的韵脚,就告诉我,我一时想不起来。”
“你呢,下士长公民,倘若我的女儿来看她那不幸的母亲,你可要放行呀,她母亲都想死她了。”
“命令已经下达,”下士长答道。这时,我们的读者大概也会猜到,他就是我们的朋友洛兰了吧,“这样,我无权干涉了;你的女儿一到,便可进去。”
“谢谢,温泉俱乐部勇敢的战士,谢谢您啦。”迪松说道。
接着,他就出门向公社汇报去了,路上他还咕咕哝哝道:
“唉!可怜的女人啊,你就要获得幸福了!”
“您知道么,下士长,”一个卫队士兵看见迪松走远了,感叹地说道,“你知道么,这些事真让他伤透了心。”
“什么事,德伏公民?”洛兰问道。
“还什么事呢?”那个富有同情心的士兵说道,“这个人铁面无情,心肠特硬,看管王后无通融余地。可是离开这里时想到他老婆就要见到女儿,而他自己却见不到,眼睛里便噙着泪水,悲喜交集。真让人揪心,说真的,有些事不能想得太多,下士长……”
“就是嘛,正如你所说,他走时眼泪汪汪的,可是他不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
“什么所作所为?”
“什么?这个女人已有三个月没看见自己的孩子了,他还粗暴地对待她。他没想到她的痛苦,只顾想自己的不幸,人就这么回事。当然啦,这个女人从前是王后。”下士长带着嘲讽的口吻继续说道,外人很难辨别出内在的含义,“别人对待王后当然不一定非得像对待一个工人的妻子那样毕恭毕敬罗。”
“不管怎么说,都是够惨的。”德伏说道。
“悲惨,但又是必须,”洛兰说道,“如你所说,最好的办法是别去想……”
说着,他又吟唱起来:
“昨日尼赛特,
在树林里踯躅,
日光晦暗,空气新鲜,
走啊走好不孤独。”
洛兰正在吟唱他的牧歌,突然,在岗哨左侧传来吵闹声,声音中杂着诅咒、威胁和哭泣。
“什么事?”德伏问道。
“好像是孩子的声音。”洛兰细听着说道。
“是的,”卫兵接着说道,“有人在打那个可怜的孩子,说实在的,在这里做事的人都没有儿女心肠为好。”
“你想唱歌吗?”一个唱得醉醺醺的人拖着嘶哑的嗓门问道。
接着,那人独自唱了起来,仿佛想起个头似的。
“维多(维多是法文“否决”的音译,这里嘲讽王后在位时老是否决新政的意思。)夫人早已许诺
让人洗劫巴黎……”
“不,”孩子说道,“我不唱。”
“你不愿唱吗?”
于是那人又唱起来:
“维多夫人早已许诺……”
“不,”孩子说道,“不唱,不唱,不唱。”
“哼,小瘪三!”哑嗓子吼叫道。
响起抽皮带的嗖嗖声,孩子疼得惨叫。
“啊!该死的!”洛兰说道,“又是那下流的西蒙在殴打小卡贝(即王子。当时由鞋匠西蒙照看。)了。”
几个国民卫队士兵耸耸肩,其中有两个人勉强笑笑。德伏起身,走开去。
“我早就说过了,”他喃喃自语说,“有孩子的人决不要进来。”
陡地一道矮门打开,王子在看守的鞭笞下,退到院子里;在他身后,响起什么沉重的东西落在石子路上的声音,那东西已砸在孩子的腿上。
“啊!”孩子惨叫道。
他踉跄了几步,跪倒下来。
“把我的鞋样拿过来,魔鬼,否则……”
孩子站起来,摇头表示拒绝。
“哦,还犟吗?”那嘶哑的声音叫喊道,“等着,等着,有你瞧的。”
说着,鞋匠西蒙从他的小屋里冲出,如同一头野兽冲出它的巢穴。
“喂!喂!”洛兰皱着眉说道,“这样干吗,西蒙伙计?”
“我要惩罚这个狼崽子。”鞋匠说道。
“为什么要惩罚他?”洛兰问道。
“为什么?”
“是呀。”
“因为这个讨饭花子不肯像诚实的爱国者那样唱歌,也不肯像一个好公民那样劳动。”
“哦,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呢?”洛兰说道,“国家把小卡贝交给你看管,可不是请你教他唱歌的吧?”
“哼!”西蒙闹不明白了,“关你什么事,下士长公民?我倒要问问你。”
“关我什么事?一切心地善良的人关心的事,我也要关心。看人打孩子,并且容忍他打下去是不配做心地善良的人的。”
“哼!他是暴君的儿子。”
“他还是个孩子,他没有参与他父亲的罪恶活动,他没罪,因此,不该惩罚他。”
“那么我要对你说,他们把他交给我就随我如何处置了。我要他唱《维多夫人》,他就该唱。”
“可是,恶棍,”洛兰说道,“维多夫人是这个孩子的母亲;您愿意别人强迫你的儿子去唱你是浑蛋吗?”
“我?”西蒙怒吼道,“啊!什么下士长,贵族胚料!”
“哦,别骂人,”洛兰说道,“我不是贵族,我……而且也没人强迫我唱歌。”
“我让人把你抓起来,保王党坏分子。”
“你么,”洛兰说道,“你要叫人把我抓起来?让人抓一个温泉俱乐部成员,试试看吧!”
“好!好!会笑的最后笑。现在,小卡贝,捡起我的鞋样,干活,要不,千刀万剜!……”
“我嘛,”洛兰脸色变得惨白,他走上前一步,紧握双拳,咬紧牙关说道,“我么,我正告你,别让他去捡你的鞋样;我么,我正告你,他无需做鞋,你听见没有,坏家伙?啊!对了,你那儿不是有一柄长剑吗,这剑与你一样吓不倒我。你敢拔出来吗?”
“啊!打吧!”西蒙怒吼道,气得脸都发青了。
这时,两个女人走进院子,其中一个拿着一张纸,另一个对哨兵说着什么。
“下士长,”哨兵喊道,“迪松的女儿,要见她的母亲。”
“既然狱委员允许,就放行吧。”洛兰说道,他不愿回转身,担心西蒙利用这间隙又去殴打孩子。
哨兵让两个女人进来了;可她俩刚刚在阴暗的楼梯上迈上几级,就与莫里斯?林代迎面相遇,他正下楼到院子里干什么。
夜幕降临,他几乎看不清她们的脸。
莫里斯叫住她俩。
“你们是谁,公民们,”他问道,“想干什么?”
“我是索菲?迪松,”两个女人中的一个说道,“我获准去看望我的母亲,现在我来看她了。”
“行,”莫里斯说道,“可只允许你一个人呀,公民。”
“我把我的女友带来了,这样在士兵中间至少有两个女人可相互照料。”
“那行,但你的女友不能上去。”
“听您吩咐,公民,”索菲?迪松说道,紧握她女友的手,那女友畏缩在墙角,仿佛受到了惊吓。
“卫兵公民,”莫里斯抬起头来,对站在每一个梯级上的哨兵说道,“给女公民迪松放行,她的朋友不能上去。让她在楼梯上等着,你们照看她,别让她受人欺负。”
“遵命,公民。”哨兵们齐声回答。
“请上吧。”莫里斯说道。
两个女人过去了。
莫里斯说罢,便飞也似地跳下余下的四五级梯级,冲向院子。
“发生了什么事,”他问卫兵道,“谁在闹?孩子的哭喊声一直传到女囚的前厅了。”
“这么回事,”西蒙说,他熟悉市政府人员的那一套,看见莫里斯,以为有了依傍,“这么回事,这个叛徒、贵族、旧党分子,他不让我教训小卡贝。”
说着,他向洛兰亮亮拳头。
“是的,混蛋!我不许他这样做,”洛兰说着从剑鞘抽出了剑,“倘若你再叫我一次旧党分子,贵族或是叛徒,我把剑刺穿你的身体。”
“吓唬谁!”西蒙大声说道,“来哨兵啊!来哨兵啊!”
“我就是哨兵,”洛兰说道,“别叫我,因为倘若我走近你,会把你宰了。”
“救救我,市政府公民,快救救我!”西蒙感到这次洛兰像是动真格的了,大声叫道。
“下士长说得对,”西蒙称之为市政府人员的那人冷冰冰地说道,“你让国家丢脸。懦夫,你在殴打一个孩子。”
“他为什么打他,你知道吗,莫里斯?因为孩子不愿唱《维多夫人》,因为儿子不愿辱骂母亲。”
“无耻!”莫里斯说道。
“你也是?”西蒙说道,“我遇到的都是叛徒?”
“呸,无赖,”市政府人员说着抓住西蒙的衣领,夺下他手里的皮带,“你试试,看看莫里斯?林代究竟是不是叛徒。”
说着,他就把皮带重重地打在皮匠的肩上。
“谢谢,先生,”孩子说道,他泰然自若地看着这一幕,“可是,他以后会把气出在我身上的。”
“来吧,卡贝,”洛兰说道,“来吧,孩子;如果他还打你,你叫救命,我们会去惩罚他的,这个刽子手!走吧,走吧,卡贝,回到塔堡去吧。”
“你们保护了我,为什么还叫我卡贝?你们明明知道卡贝不是我的名字。”
“什么,不是你的名字?”洛兰说道,“那么你叫什么?”
“我是路易-查理?德?希邦。卡贝是我一个先祖的名字。我学过法国历史,是我父亲教我的。”
“而你想教这个孩子去修鞋子?而国王教过他历史呢。”洛兰大声说道,“算了吧!”
“啊,放心吧,”莫里斯对孩子说道,“我这就去汇报。”
“我也去汇报,”西蒙说道,“别的不说,我要汇报你们为两个女人放行这件事,而只有其中一个才有权进入塔堡。”
这时,果真有两个女人从塔堡里出来。莫里斯向她们奔过去。
“喂,女公民,”他对那个在他身旁的女人说道,“你看见母亲了吗?”
索菲?迪松这时站在市政府人员和她的女友之间。
“看见了,公民,谢谢。”她说道。
莫里斯想看看那姑娘的女友是什么模样,至少听听她的声音,但她裹着风衣,似乎坚决不吐露一句话。他甚至觉得她在微微发抖。
他见她胆怯,疑窦顿生。
他急冲冲登上塔堡,走入第一间房间,透过窗户,看见王后把一件像纸条样的东西藏进衣兜里。
“哦!哦!”他说道,“难道我受骗了?”
他把同事叫来。
“阿格里戈拉公民,”他说,“你到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内室去,监视她。”
“哦!”市政府人员叫出了声,“难道……”
“我叫你进去,而且刻不容缓,分秒必争。”
市政府人员进入王后内室。
“把迪松老婆叫来,”他对一名守卫说道。
五分钟之后,迪松妻子容光焕发地走来了。
“我看见我的女儿啦。”她说道。
“在哪儿?”莫里斯问道。
“就在这里,在前厅。”
“好。那么你的女儿有没有请求看看这个奥地利女人呢?”
“没有。”
“她没有进入她的内室?”
“没有。”
“在你与女儿交谈时,有没有人从女囚的房间里走出来?”
“我会知道么?我有三个月没看见女儿了,光看她还不够哩。”
“想想吧。”
“哦,对呀,我想起来啦。”
“想起什么来着?”
“小姑娘出去过。”
“玛丽-泰雷兹?”
“是的。”
“她对你女儿说话了?”
“没有。”
“你女儿没交给她什么吧?”
“没有。”
“你女儿在地上捡起什么?”
“我的女儿?”
“不是,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女儿。”
“捡了,她捡起了她的手帕。”
“啊!坏东西!”莫里斯叫出了声。
他疾步如飞地冲向钟楼的钟索,使劲摇起来。
这是报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