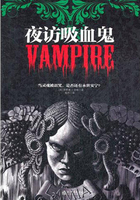过了两三天,他在城里的菜市场,在一堆堆的萝卜、蕃茄、黄瓜、青菜中间又看见了她。他闲逛着,看着那些女菜贩整齐地站在摊位后面,好像奴隶在等待买主。有几个警察一手拿着钱袋一手拿着一叠票子,挨个收钱并发给小票。一个老太婆,吃得胖胖的,手里拎着两只大篮子,大模大样地向人讨菜。大家叫叫嚷嚷:古老的秤托着绿色的菜,的的笃笃地响个不停;拖着小车的大狗兴奋地叫着。就在这喧闹中,克利斯朵夫看见了他的利百加,——真名叫洛金——她在头上戴着一张白里泛绿的菜叶,像一顶帽子,面前堆着各类蔬菜。她坐在一只篓子上啃着苹果,不停地吃,根本不在乎她的生意,不时拿围裙抹抹下巴和脖子。偶尔,她无精打采地抓着把豌豆玩。她东张西望,漫无目的,可是把周围的情形都看在眼里:凡是针对她的目光,她都暗暗地记住了。她当然看到了克利斯朵夫,便一边和买菜的顾客说话,一边皱着眉头从他们的肩上望过去,注意他。她表面上很严肃,心里却暗笑克利斯朵夫。他的模样也确实令人发笑:呆呆地站在几步外,拼命用眼睛盯着她,然后又默默地走了。?
他好几次到她的村周围游荡,他站在路上远远地望着她在院子中忙碌着。他不承认是为她而来的,其实有时也是无意中走来的。他一心一意作曲的时候,常常像梦游一样,他对着姑娘,往往被胸中乐章 搞得糊里糊涂,眼睛看着她,心却依旧沉浸在幻想中。他根本没注意到自己老想来找她。?
他这样常常露面,当然会引起别人的议论。农庄上后来知道了克利斯朵夫的来历,经常嘲笑他。可谁也不以为然,因为他并不侵犯任何人。一句话,他不过像个呆子,而他自己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那天正是村里的一个节日。儿童们扔着豌豆喊着:“君皇万岁!”村子里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克利斯朵夫向三王客店走去。客店屋顶上飘荡着一片小旗,门前吊着成串的蒜头,窗上点缀着红的黄的金莲花。他走进大厅,墙上挂着发黄的石印图画,正中挂的是皇帝的彩色肖像,四周扎着橡树叶。很多人在跳舞,克利斯朵夫认为他关注的对象一定在里面。果然,他第一个就看到了她。她一边跳着华尔兹,一边从舞伴的肩头上向他抛着媚眼,并且为了挑逗他,故意和村里的少年调情,张着大嘴傻笑,高声说些粗俗的话。在这一点上,她和一般交际场中的姑娘是相同的:被人一瞧,她们就非表现一番不可。——其实她们并不见得多么蠢,因为知道大家只是瞧她们,而不会听她们的。——克利斯朵夫胳膊撑在桌上,双手托着下巴,看着她装腔作势。从眼里流露出他的热情与愤怒:他脑子还算清醒,不至于看不出她的伎俩,但还是上了她的当;所以他时而愤愤地咕哝,时而又耸耸肩膀,笑自己受人愚弄。?
此外还有一个人在注意他:那是洛金的父亲。他矮胖、大脑袋、短鼻子,光秃的头顶被太阳晒成了暗红色;四周只剩下了一圈头发,从前一定是金黄的,如今变成一个个浓密的小卷儿,像丢勒画的约翰;胡子剃得很干净,神色十分镇静,嘴中衔着一根烟斗。他慢腾腾地和别的乡下人说着闲话,不时瞟一眼克利斯朵夫的表情,不由得心中暗笑。他走过来挨着克利斯朵夫坐下,克利斯朵夫极不高兴地回头看了看他,正碰上那双狡猾的眼睛。老人却衔着烟斗,很随和地和他搭讪起来。克利斯朵夫以前就认识他,认为他是个老杂种,可对他女儿的好感使他对父亲也爱屋及乌了,甚至和他在一起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狡猾的老头儿看透了这一点。
他先说了一阵天气,然后说到了那些俊俏的姑娘,又提到克利斯朵夫的不去跳舞的办法很聪明,坐在桌前把杯独酌不是更舒服吗?说到这儿,他毫不客气地向克利斯朵夫讨了一杯酒。老头儿一边喝,一边谈到他的小买卖,抱怨生活艰难,百物昂贵等等。克利斯朵夫听了完全没兴趣,只在鼻子里随便哼几声,眼睛始终没离开洛金。老人等了一会儿,等他回答,他根本不理睬,老人又可以不慌不忙地说下去了。克利斯朵夫心里琢磨这家伙来跟他套近乎,说那些话,究竟有什么意思。结果他明白了。老人抱怨完了,把话锋一转,把他庄上的蔬菜、家禽、鸡子、牛奶,夸了一阵,然后问克利斯朵夫能否把他的产品介绍卖到爵府里去。克利斯朵夫听了大吃一惊:“怎么他会知道?……难道我认识他吗?……”?
“当然啦,”老人说,“我什么事都会知道的。”?
他心里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尤其是我亲自去探听的时候。”?
克利斯朵夫漠然地告诉他,虽然他什么事都会知道,但他们还不知道他最近已经跟宫廷闹翻了,即使他的话当初在爵府的总务处和厨房里有点作用,现在也没用了。老人听到这儿并不灰心,过了一会儿,又问克利斯朵夫能不能给他介绍某些家庭,接着就说出一些和克利斯朵夫有来往的人家的名字,因为他在菜市上详细地打听了一下克利斯朵夫。他想到老人尽管那么狡猾还是上当了,不由得想笑出来,要不然,克利斯朵夫对这种间谍式的行为早就气得暴跳如雷;因为对方根本想不到,克利斯朵夫的介绍不但不能替他招来新顾客,反而会使他连老顾客都会保不住的。因此克利斯朵夫听凭老头儿枉费心机地耍些无聊的小手段。但那乡下人死盯不放,最后竟以克利斯朵夫和鲁意莎为对象,硬要推销他的牛奶、牛油和乳脂;他早就盘算好了,既使找不到的别的顾客,这两个总是肯定的。他又补充说,既然克利斯朵夫是音乐家,那每天早晚吞一个新鲜的生鸡蛋是保护嗓子最好的办法:他自夸他能供给刚生下来的,还带着热度的,最新鲜的鸡蛋。克利斯朵夫一听老人把他误当作歌唱家,不禁哈哈大笑。老头儿趁机又叫了一瓶酒。然后,觉得在克利斯朵夫身上再下功夫也毫无意义,便掉头走了。?
天已经黑了。舞场里人越来越多。洛金毫不在乎克利斯朵夫,只忙着向村里一个富农的儿子献媚,所有的姑娘都争着讨他喜欢。克利斯朵夫观察着她们这种竞争;女孩子们彼此嘻笑着,手舞足蹈,乐不可支。克利斯朵夫忘了自己,一心希望洛金成功。但当洛金真成功时,他又有点儿伤感。他立刻责怪自己。他既不爱洛金,那么她喜欢爱谁就爱谁,与他有什么关系呢?那些人都为了利用他才关心他,过后还会嘲笑他。洛金因为把她的情敌气坏了,格外兴奋,人也显得更漂亮了,克利斯朵夫叹了口气,望着她笑了笑,准备离开了。已经九点了,进城还要走好几里路。?
他刚站起身,忽然闯进来十几个兵。他们一出现,全场的空气顿时凝结了。大家开始议论纷纷,几对正在跳舞的伴侣停住了,担心地望着那些新来的客人。站在大门口的几个乡下人故意转过身子和自己人谈话,虽然表面上显得若无其事,暗中却小心翼翼地闪出一条路来。——整个地方上的人和城市四周炮台里的驻军已经明争暗斗了。大兵们烦闷得要死,常常拿乡下人出气,很下流地嘲笑他们,侮辱他们,把乡下的妇女当作属地上的女人看待。上星期就有一批喝醉的士兵去邻村的节会上捣乱,把一个庄稼人打得半死。克利斯朵夫知道这些事,和乡下人一样气愤。此刻他便回到原位,静观事态发展。?
那些兵根本不理会大众的愤怒,乱哄哄地奔向坐满客人的桌子,硬挤下去。大半的人都咕噜着离开桌子。一个老头儿让得慢了点儿,被他们把凳子一掀,摔在地上,他们看了哈哈大笑。克利斯朵夫很气愤,站起来正要去干涉,没想到那老人费了好大劲儿从地上爬起来后,不但没有一句怨言,反而连声道歉。另外两个兵走向克利斯朵夫的桌子,他握着拳头看着他们过来。可是他根本不用这么紧张,那不过是跟在坏蛋后面,想狐假虎威一下的两个孬种罢了。他们被克利斯朵夫严肃的表情镇住了;他冷冰冰地说了一声:“这儿有人……”他们就赶紧道歉,缩在凳子的一头,惟恐激怒了他。他说话颇有主人的气势,而他们天生是奴才料。他们看出克利斯朵夫不是个乡下人。?
这种屈服的态度使克利斯朵夫的气缓和了一些,观察事情也冷静了一些。他一眼就看出来这些大兵的头头是个班长,——目露凶光的小个子,斗牛狗似的脸,下流无耻的混蛋,就是上周日闹事的主角之一。他坐在克利斯朵夫旁的一张桌子上,已经醉了。他凑到人家面前,说着不三不四的侮辱的话,而那些受侮辱的人装做听不见。他特别盯着跳舞的人,用下流的话嘲笑他们,引得同伴哈哈大笑。姑娘们红着脸,眼泪都快流出来;年轻的汉子气得咬牙切齿。恶棍的眼睛慢慢地把全场的人挨个看了一遍;克利斯朵夫看他的目光扫到自己身上,便抓起杯子,握着拳头,如果他一旦说出一句侮辱的话,就把酒杯摔过去。他心里也很矛盾:?
“我简直疯了,还是走掉的好,否则我会被他们把肚子都切开的;再不然,也得被他们关进牢里,那可真是没必要了。还是趁他们没来惹我之前走吧!”?
但他骄傲的性格却不让他走,他不愿被人看出他害怕这些流氓。——对方那恶毒的眼睛盯住了他。克利斯朵夫浑身紧张,气愤地瞪着他。那班长把他打量了一会儿,克利斯朵夫的脸引起了他说话的兴致,他用胳膊撞着同伴,一边冷笑一边让他看克利斯朵夫,正要开口讥讽他。克利斯朵夫积聚浑身的力气,预备把杯子摔过去了——正在千钧一发的关头,一件偶然的小事救了他。醉鬼刚要开口,却被一对跳舞的冒失鬼撞了一下,把他的酒杯打落在地上。于是他愤怒地转过身去,把他们狗血喷头地大骂一顿。他的视线转移了。他完全忘了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又等了几分钟,看见敌人无意向他挑衅,便站起来,慢慢拿着帽子,慢慢地向大门走去。他眼睛一直盯着军官的桌子,想要他知道他决不怕他。可那醉鬼已经把他忘得干干净净:再没人注意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