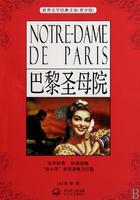斯佳丽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只觉得自己气得脸都红了。
“喂,说话呀。”
她还是什么也不说,恨不得摇摇父亲,让他住口。
“他在家,还好心地问起你,他几个妹妹也问了,还说希望你明天没有事的话就去参加宴会呢。我敢说你绝对不会有什么事,”他精明地说,“行了,女儿,你和阿希礼到底怎么回事?”
“没事,”她马上说,一面使劲拉着他的胳臂。“我们进去吧,爸。”
“这会儿是你又要进去了,”他看看她,“我可要站在这儿弄个明白才行。现在我想起来了,最近你一直有些古怪。是他一直在玩弄你?他向你求过婚吗?”
“没有。”她马上说道。
“他也没向你求婚。”杰拉尔德说。
她火了,但杰拉尔德挥挥手,让她安静。
“别啰嗦了,小姐!今天下午约翰·韦尔克斯悄悄跟我说了,阿希礼要娶玫兰妮,明天就要宣布了。”
斯佳丽的手从他胳臂上滑了下来。原来这事是真的!
她的心顿时像被野兽的尖牙猛地啃了一口,感到了深深的刺痛。这会儿,她感到父亲的眼睛一直在望着她,神情有些怜悯,也有些烦恼,因为他碰到了一个不知怎么解答的难题。他虽然爱斯佳丽,但她硬要他回答些傻里傻气的问题却使他感到不舒服。埃伦知道所有的答案。斯佳丽应该把自己的心事去对她说才是。
“你这不是一直在出自己的丑——也在出全家的丑吗?”他又像往常激动时那样提高嗓门吼道,“县里哪一个花花公子你弄不到手,偏偏去追求一个不爱你的男人!”
她顿时来了气,觉得伤了自尊心,一下子痛苦竟消除了几分。
“我没追求过他。只是一直是感到惊讶。”
“你撒谎!”杰拉尔德说,说罢盯着她那张痛苦不堪的脸,接着又突然和蔼地加了一句:”对不起,女儿。但你毕竟只是个孩子。爱你的人多着呢。”
“母亲嫁给你的时候才十五岁,我都十六了。”斯佳丽压低嗓门说。
“你母亲可不一样,”杰拉尔德说,“她压根儿不像你这么轻浮。得了,女儿,打起精神来,下星期我带你到查尔斯顿去看你尤拉莉姨妈,他们那儿正在庆祝苏姆特堡大捷,不出一星期你就会忘掉阿希礼了。”
“还把我当小孩呢,”斯佳丽想着,既悲痛又愤怒,连话也说不出了。“只要在我面前晃一晃新玩具就行了吗?”
“行了,别犟嘴了,”杰拉尔德警告说,“你要是有点头脑,早就嫁给塔尔顿家的斯图特或布伦特了。好好想想,女儿。嫁给这兄弟俩中的一个,两家庄园就可以并到一起了。我与吉姆·塔尔顿会给你们造一幢好房子,就在两家庄园接界的那片大松林那儿,还有——”
“别把我当小孩了!”斯佳丽嚷道,“我不要到查尔斯顿去,也不要房子,也不要嫁给这兄弟俩。我只要——”她马上住了口,但已经来不及了。
杰拉尔德的声音平静得出奇,说话时不慌不忙,仿佛尽管他平时难得动脑筋,这番话倒都是经过细细斟酌后才说的。
“你只要阿希礼,偏偏又得不到。就算他愿意娶你,凭我和约翰·韦尔克斯的交情,我要答应也放不下心。”看见她神色惊讶,他又接着说:“我要自己的女儿幸福,你跟了他是不会幸福的。”
“哦,我会幸福的!会的!”
“你不会的,女儿。只有情趣相投的人结婚才能有幸福。”
斯佳丽突然忍不住想大声顶撞父亲,“你不也是幸福的吗,可你和母亲没有相同之处啊。”但她忍住了,生怕自己太放肆,他会扇她耳光。
“我们跟韦尔克斯家的人不一样,”他一字一句地慢慢说道,“韦尔克斯家跟我们的邻居们都不一样一跟我认识的哪一家都不一样。他们是怪人,他们还是表亲通婚的好,把这些怪毛病都传给他们自家人吧。”
“喂,爸,阿希礼不是——”
“别闹,丫头!我没说那小子的坏话,因为我喜欢他。我说怪,不是说疯。他不像卡尔弗特家那么怪,把全部家产都拿去赌马,也不像塔尔顿家的人总是烂醉如泥,也不像方丹家,都是些火急火燎的怪物,自以为受到怠慢就随便杀人。这些坏毛病当然容易理解,如果不是上帝保佑,我杰拉尔德也会有这些毛病的!我倒不是说你做了阿希礼的妻子,他会对你不忠,也不是说他会打你。要是他那样你倒会快活些,因为至少你会理解这种怪异。但他怪得与别人不同,让人一点也摸不透。我虽然喜欢他,但他说的话十句倒有八句让我摸不着头脑。得了,丫头,你说实话,他说起书本、诗歌、音乐、油画和那些荒唐的废话,你懂吗?”
“哎,爸,”斯佳丽不耐烦地喊道,“如果我嫁给他,我会改变一切的!”
“呸,你以为你改变得了?”杰拉尔德恼火地说着,一面狠狠地瞪了她一眼,“那你对天下的男人了解得可太少了,更别说阿希礼了。没有哪个做妻子的可以改变丈夫一丝一毫的,这点你要记住。至于说要改变韦尔克斯家的人一那更没门儿,女儿!他们一家人向来都是这样,以前这样,也许将来也一直是这样。我跟你说他们生来就有股怪劲儿。瞧他们那德行,一会儿冲到纽约,一会儿又冲到波士顿,不是听歌剧,就是看油画。还从北方佬那儿订购成箱的法文书、德文书!他们就坐在那儿看啊,幻想啊,不知在干什么。照我说还不如跟常人一样把这些时间用来打打猎、打打牌呢。”
“全县骑马谁也比不上阿希礼,”斯佳丽听他把阿希礼糟蹋成这个样子,不由得火了,就说,“除了他父亲没人比得上他。说到打牌,上星期在琼斯博罗,阿希礼不是还赢过你两百块钱吗?”
“卡尔弗特家的小子又在瞎说了,”杰拉尔德无可奈何地说,“否则你不会知道具体数目。阿希礼骑马能得第一,打牌也能得第一一这是我说的,丫头!我不否认他要是喝起酒来连塔尔顿家的人也喝不过他。这些事他样样都行,但他的心思不在这儿。所以我才说他怪呢。”
斯佳丽沉默了,心里一沉。她想不出什么话为自己辩解,因为她知道父亲是对的。这些寻欢作乐的事阿希礼虽然样样都行,但他的心思确实不在这上头。别人感兴趣的事,他都是出于礼貌才装出感兴趣的样子。
杰拉尔德见到她沉默不语,便拍拍她的胳臂,得意地说等着瞧,斯佳丽!你也承认我说的不错了吧。你要阿希礼这样的丈夫干吗呢?韦尔克斯家的人个个都疯疯癫癫的。”他接着连哄带骗地说:“我刚才提起塔尔顿家并没有把他们推给你的意思,那兄弟俩都不错,不过要是你以后看上了凯德·卡尔弗特,对我也完全一样。卡尔弗特家都是好人,尽管老头儿娶了个北方婆娘。等我死了——乖孩子,听我说!我就把塔拉庄园留给你和凯德——”
“我才不要你把凯德放在银盘上送给我呢,”斯佳丽生气地说,“求你别再把他推给我了!我不要塔拉庄园,什么庄园也不要。庄园有什么了不起,如果——”
她正要说“如果没有你想要的男人”,但杰拉尔德早已气坏了,他把塔拉庄园看成天底下仅次于妻子的心爱之物,他要把它送给她,她竟对这份礼物不屑一顾。他气得吼道:
“斯佳丽·奥哈拉,你竟敢当面对我说塔拉庄园一这片土地没什么了不起·”
斯佳丽倔强地点点头。她痛心极了,顾不上父亲是不是火了。
“天底下只有土地才是最了不起的,”他大声嚷嚷,气得将两条粗短的胳臂乱舞着。“因为天底下只有土地才是经久不变的,你别忘了这一点!只有土地值得你去出力,值得你去战斗一值得你去拼命!”
“哦,爸,”她不耐烦地说,“你这话就像个爱尔兰人!”
“你以为我对此感到羞耻吗?不,我还引以为荣呢。而且别忘了,你也是半个爱尔兰人,小姐!对任何一个有一滴爱尔兰血液的人来说,他们生活的土地就是他们的母亲。此时此刻我倒替你感到羞耻。我把除了故乡米斯郡以外,天底下最美的一块土地送给你,而你,竟然还看不上!”
杰拉尔德越说越来劲,刚要大嚷大叫,见斯佳丽愁容满面就打住了。
“不过,你还年轻。将来你就会对土地有这种爱了。如果你是爱尔兰人,你就摆脱不了这种爱。你还是个孩子,又在操心情人的事。等你大了,你就明白这一切了……好了,你是打定主意要凯德呢,还是要那兄弟俩,还是要埃文·芒罗家的少爷,等着瞧吧,我会把你好好地嫁出去的。”
“哦,爸爸!”
这会儿,杰拉尔德已经不想再谈下去了,他感到腻味了,对这个难题竟落到他身上也烦死了。此外,让他感到委屈的是尽管自己把县里几个最佳人选供她挑,还要把塔拉庄园送给她,她还是一副可怜相。杰拉尔德喜欢的是别人对他的礼物拍手叫好,深表感谢。
“行了,别赌气了,小姐。你嫁给谁都无所谓,只要他和你情投意合,门当户对,人品又体面就行。对女人来说,结了婚以后才有爱情。”
“哦,爸,那都是老掉牙的老观念了。”
“可这观念很好!鬼混啊,恋爱结婚啊,这套都是奴仆、美国北方佬之流干的玩意儿!最美满的婚姻是父母做主的婚姻。因为像你这样的傻瓜怎么分得清好人和坏蛋?得,就瞧瞧韦尔克斯家吧。他们怎么会代代相传、人丁兴旺呢?原因就是跟他们的同类人结婚,跟他们家一向看中的表亲结婚。”
“啊!”斯佳丽叫道,父亲这番话让她深切感到事实终归是事实,这情况也在所难免,不禁又悲伤起来。父亲见她低着头、步履蹒跚。
“你不是在哭吧?”他问道,笨手笨脚地摸摸她的下巴,想托起她的脸蛋,他觉得心疼,不由得也愁容满面了。
“是的。”她扭开身子,拼命叫道。
“你在撒谎,但我倒感到得意。我很高兴你还有自尊心,丫头。而且我要看到你在明天的宴会上有自尊心。你对人家一片痴情,人家除了把你当朋友,根本就没把你放在心上。我可不要县里人因此说你的闲话,取笑你。”
“他心里才有我呢,”斯佳丽想着,心里十分痛苦,“哦,放在心上的时候多着呢。我知道他把我放在心上的。我看得出来。如果时间允许,我知道我能让他开口——只要韦尔克斯家别老认为他们一定得跟表亲结婚就行了。”
杰拉尔德挽起她的胳臂。
“现在我们得进去吃晚饭了,这事你我知道就行了,可别对人说。我不想让你妈为此操心一你就别说出去了。把鼻涕擤擤,女儿。”
斯佳丽用块破手绢擤了擤鼻子,他们手挽着手走上黑黝黝的车道,那匹马在后面慢慢走着。走近屋子时,斯佳丽本想再说什么,却见母亲正站在门廊中朦胧的阴影里。她戴着帽子,披着围巾,还戴着无指手套,黑妈妈站在她身后,紧紧绷着脸,一只手提着个黑皮包,包里是埃伦给奴隶看病常备的绷带和药品。黑妈妈的嘴厚厚的,往下耷拉着。碰到她生气时,那下唇更会比平时拉长一倍。这会儿嘴唇又拉长了,斯佳丽猜想黑妈妈碰到什么不称心的事了,正在火头上呢。
“奥哈拉先生,”埃伦见父女俩从车道上走来就叫道一她这代人讲究规矩,尽管她嫁人已经十七年,生过六个孩子,但仍讲究这一套一“奥哈拉先生,斯莱特里家有人病了。埃米的孩子生了,快死了,一定得受洗礼,我和黑妈妈这就上那儿去,看看能帮着做点什么。”
她询问似的提高了嗓门,仿佛在等待杰拉尔德的意见,尽管这仅仅是个规矩,但杰拉尔德心里还是很看重它的。
“我的天啊!”杰拉尔德咆哮道,“那些穷白佬为什么偏偏在吃晚饭时来叫你,我正想告诉你亚特兰大一带传说的有关打仗的消息呢!去吧,奥哈拉太太。如果外边出了什么事,你不去那儿帮帮忙,晚上也睡不踏实的。”
“她晚上尽忙着护理黑人和那些能照顾自己的穷白佬,哪里睡得踏实啊。”黑妈妈嘟嘟囔囔道,一面走下台阶朝等在车道边的马车走去。
“吃饭时你替我照看一下吧,乖乖。”埃伦说着,手轻轻摸了摸斯佳丽的脸蛋。
斯佳丽强忍住泪水。母亲的这一抚摸使她感到母亲魅力无穷,闻到她窸窸窣窣的绸衣服里隐隐散发出的美人樱香囊的香味,她激动不已。对斯佳丽来说,母亲真是个奇人,奇就奇在跟她同住在一幢房子,既让她害怕,又让她陶醉和抚慰。
杰拉尔德扶妻子上了马车,他让马车夫小心赶车。托比替杰拉尔德照管马匹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听到有人吩咐他怎么干他的老本行,闷闷不乐地噘着嘴。马车上路了,黑妈妈坐在托比身边,两人都板着面孔。非洲人就是这样噘起嘴赌气的。
“要是没有我给斯莱特里家的那些穷鬼这么多帮助,他们就得在别处花很多钱,”杰拉尔德怒气冲冲说,“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把他们那可怜的几亩沼泽洼地卖给我,他们也就可以离开这个县了。”说完,他想到可以再来次恶作剧就又快活起来。“来吧,女儿,我们去告诉波克,我们没把迪尔西买下来,而是把他卖给约翰·韦尔克斯了。”
他把缰绳扔给站在路前的一个黑孩子,走上台阶。他早已忘了斯佳丽的伤心事,一心只想捉弄一下他自己的贴身男仆。斯佳丽跟在他身后慢慢走上台阶,脚步沉重。她想,她和阿希礼结为夫妻总不见得比她父母之间的关系更别扭吧。她平时也常在想,父亲这种吵吵闹闹、生性迟钝的人,怎么会娶上母亲这样的女人,因为这两个人无论出身、教养和性格都相差甚远。
埃伦·奥哈拉三十二岁,按那时的标准,她得算是个中年妇女了,生了六个孩子,活下来三个。她高高的个子,比烈性子的小个子丈夫还高出一头,可是她走起路来优雅轻盈,裙摆款摇,身材就不那么显了。脖子露在黑色塔夫绸紧身衣领口外,圆圆的,细细的,皮肤白皙。脑后那堆罩在发网里的秀发沉甸甸的,压得她的头似乎老是稍稍向后仰。她母亲是法国人,外祖父母是1791年法国革命时逃到海地去的。她母亲给了她一双弯眼梢的黑眼睛,乌黑的睫毛和一头黑发;她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士兵,给了她挺直的鼻梁和方方的下巴,配上线条柔和的脸蛋倒不乏柔美。不过埃伦脸上那矜持而谦和的神情,以及她的优雅庄重、不苟言笑,是多年生活磨练出来的。
如果她眼光里有一点热情,笑容里多一点亲切,在家人和仆人听起来美妙动听的声音里带点自然流露的味儿,那她早就算得上是一个绝色美女了。她说话带着佐治亚州沿海一带那种柔和含糊的口音,元音吐得柔和,辅音发得亲切,还带有一点点法语腔调。吩咐仆人或责备孩子时从来不提高嗓门,但在塔拉庄园里,听到这声音无不服从照做。她丈夫又吼又叫,大家听了反而都默不作声,不理不睬。
从斯佳丽记事时起,母亲就一直是这样,不论是夸奖还是责怪,她的声音总是柔和悦耳。尽管乱糟糟的家里每天都有紧急的事情,但她总是不慌不忙,应付自如。她情绪稳定,总挺着胸抬着头,连三个儿子夭折的时候都是这样。除了吃饭、看护病人,或者给庄园记账,斯佳丽从来没看见母亲在椅子上靠过,也从来没看见母亲手里不做针线活儿而闲坐着。如果有客人在场,就干精巧的剌绣活,其它时间就忙着缝杰拉尔德镶褶边的衬衫,缝制女儿的衣服或是奴隶们的衣服。斯佳丽很难想象母亲手上不戴金顶针,绸裙窸窣的身边没有那个小黑女孩的身影会是什么情景。这黑女孩的职责就是替她拆线头,为她拿黄檀木的针线盒。她跟着她从这间屋子走到那间屋子。母亲四处走动,指挥下人做饭、打扫卫生以及组织庄园上下忙大批大批衣服的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