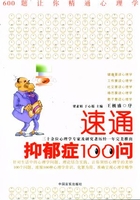宝钗将一些数据账目交给弘昑核算,弘昑方走,这边云儿便问宝钗‘可有空’,宝钗心中略起疑惑,却听其神秘兮兮地说道:“才去找落夕,听林姑娘和她在屋里说了几句话,我在窗下听到了,觉得古怪,特来告诉姑娘知道。”
宝钗忙问何话,那云儿便凑近前来,将黛玉二人谈话小声地说了,宝钗便蹙眉问道:“你可听仔细了?真是这样说的?”
云儿眯着眼睛笑道:“哪敢骗姑娘?确有此话,要不是那狗儿发出声音,让林姑娘起疑,想必她二人说出更多来,也未可知。”
宝钗便凝神痴目,细细思索,别的尚可,只是回想其方才说的‘乔装易容’,‘别人伺候’几个字,心中也大觉古怪,生出无数疑问,因思道:若云儿所言非虚,这落夕似不是逃荒来的,该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姑娘才是,只是奇怪,她为何到这府里做一个丫头?况她旧日如何景况,那颦儿又如何知道的?
是以越想越疑,只觉得这落夕内里复杂,忽然想起一事,如电光火石,在心中一闪而过,便暗暗思道:是了,我且先这般问她,试她一试,她若照实答了,也算诚实之人,也算没看错她,如若不然,他必是心中藏奸之辈,以后可要防着他些了。
思量既定,便叫云儿去叫落夕出来,云儿遂应命去了一回,只说‘姑娘有事审你’,因其用了一个‘审’字,兼其满面得意之状,似手握大把柄一般,弘昑顿觉奇怪,狐疑出来,见到宝钗,也不言语,宝钗也不知云儿是怎么说的,尚云淡风轻地笑道:“也没什么别的,不过想问问你,你来府中之前,和林妹妹认不认识。”
此问一处,弘昑本能地就要冲口而出‘并不认识’,转念一想,顿觉此回答着实大谬大误,且不说别个,单说那日宝钗等人从他包袱中得画一事,如不认识,怎能给黛玉作画?岂不是摆明了撒谎?
遂迟疑着点头道:“识得。”
宝钗便看他,问:“你二人怎样认识的?你又是谁家的姑娘?”
弘昑忙在脑海中想了无数对答,最后说道:“我和姑娘,是同乡。那时我们家和姑娘家只一墙之隔,每常一块顽,所以认识。”
宝钗又问道:“那你为何不家里呆着?乔装改扮到贾府来?”
弘昑一听‘乔装改扮’四字,心中顿时大悟,便知道了定是云儿偷听得他二人谈话,回来学舌,思道:我说那丫头神色古怪,又说要‘审’我,原来玄妙在此!
便故作纳闷,笑道:“姑娘此话奇怪,我如何‘乔装改扮’了?”
宝钗点头笑道:“好,好,好个丫头,云儿都告诉我了,你还装憨呢!——只实说了罢!”
弘昑假装脸色大变,嗫嚅着说道:“原来是那时的话,这里也有个缘故,姑娘有所不知了,——我若说了,只恐姑娘说出去。”
宝钗便笑道:“什么缘故,你且说来,我自是不告诉人的。”
弘昑看看云儿,吞吞吐吐,欲说还休。
宝钗会意,便让云儿出去,云儿少不得应了。宝钗便道:“你可说得了罢?”
弘昑这才笑道:“既如今成了姑娘丫头,姑娘便是落夕头等重要的人,有些话,也不瞒着姑娘,我和姐姐小时候常一块儿顽的,那时也算还好,我爹爹本在林老爷手下做事,后来一次,林老爷犯了点事儿,皇上欲要怪罪,林老爷竟巧立证据,将一起过失都推在我爹爹一个人身上,这内里详情,我也不需细说,我爹爹妈妈气不忿,一病之下,竟死了。”
宝钗有些疑惑:“林老爷害你爹爹?这不能罢?”
弘昑忙道:“我起初也断未想到这层,后来还是我家中那个瞎眼的外祖母说了,我才知道,此时林家早已经搬走,我虽年岁不大,因外祖母每日向我灌输报仇之思,我不可或忘,也将她林家恨得无可附加,便拜在一个高人门下,习武学剑,外祖母想念我娘,几年以后,也撒手人寰,独独剩下我一个,我见武艺初成,遂变卖了家当,去寻林家,岂知那林如海和贾敏却都已亡故——”
宝钗听得入神,忙说道:“还有林黛玉呢。”
这一句‘还有林黛玉’,听得弘昑顿时心中生寒,暗暗思道:想不到她这般温柔娴淑的外貌,却包着如此肮脏狠辣的心肠,她这意思,若我能剑伤姐姐,报了家仇,定是她心中一大快事了!怪道人说‘最毒不过妇人心’,果真如此!
便忙道:“冤有头,债有主,既然害我全家者是林如海,我便只找他们去,我虽心中也恨林姑娘,然她再怎样,也罪不致死,若能得到一星半点机会,我只好生折磨了她,也就是了,所以才谎言我父母并没有死,对她只说是‘乔装打扮,出来玩的’。”
说到此,冷哼几声,笑道:“她倒也单纯,听说我这么说,倒每日家只让我回去,我看她每日七病八痛的,料她也不能久长,倒也没急着怎样。——今儿这话除了姑娘,我若对第二人说起,也敢起个誓来!我知道姑娘素来和林姑娘好,你若告诉她,我也无法,大不了将我抓了,送交官府,只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爹娘的冤屈,早晚有天道给拨正平反——”
说到此,弘昑眼圈一红,竟哭起来,此番肺腑之言,其实细细思量之下,不难听出漏洞,只是宝钗得知她竟和林黛玉有家族之仇,又见她演的说的逼真,不忧反喜,暗暗思道:想不到颦儿竟还有这番劫难,也是天意,又怪得谁来!
便款款拿出帕子来,为她拭泪,口中柔声说道:“你也痴了,你如今既已经成为我的丫头,只要你对我忠心,我凡事必是多护着你些,岂有害你之理?”想了想,又觉疑惑,便问:“只一则,你既如此恨她,怎么还巴巴地给她画了一张画?还题上那一首诗?这又是何故?”
弘昑心中又是一惊,脑中一转,忙道:“我第一日来时,遥遥见了林姑娘一面,只觉心中又跳,又有些眼熟,也不敢上去问,还是回去问她们,才知是她,便凭记忆画了一幅,每日看着,警醒自己,‘莫忘家恨,对仇人手软!’,因怕人起疑,这才随便题了一首诗,后来偏生又丢了,想她如今已经刻我心里,倒也罢了。”方说完,又瞪目看着宝钗,疑道:“姐姐怎知有这画的?难道是姐姐拿去了?”
宝钗本要问她,不想倒把自己给你绕进去了,忙笑道“你这丫头,我拿你东西作什么,那日本是莺儿看到一眼,回来说你画的好罢了。”
弘昑便笑道:“是呢,我说姑娘这样端庄的人,定不会作出此事,这定是那起没脸的王八羔子偷拿去了,姐姐不知道,那几日秋纹碧痕等人常常找我麻烦,行事就要使绊子,防都防不过来。”
宝钗一听这话,便臊得有些脸红,气也不是,怒也不是,窘了一窘,便唯唯说了句‘票据都弄得怎样了?’
弘昑回过神来,笑道:“弄出一些了,姑娘还得略等等。”
宝钗点头,说道:“去干活罢,我今晚要的。”弘昑便答应着下去了,走到门口,又犹犹豫豫说道:“方才那番话,姑娘不会告诉人罢?”
宝钗微微一笑,说道:“你看看我,可像那么坏的人?——你就放心罢。”弘昑这方展颜而去。
话说弘昑过了这一关,心中也长出一口气,知皆是云儿告密引起,便暗暗厌之,知同来的另一个丫头也不是善类,遂连她二人一起防备起来,——‘若得机会,一并报复!’知值此事之后,宝钗必将更信任自己,倒也欣然,只当‘因祸得福’。
不一时,票据皆妥当了,数目皆对,宝钗不禁有些疑惑,便拿着一径家去,彼时薛姨妈正卧榻上躺着跟小丫头说话,宝钗见了,便问:“妈今天觉得怎样了?”
薛姨妈道:“好多了,只是心口还闷得慌,有时喘不上气。”遂遣走了丫头,叫宝钗近前,在脸上细看了一回,点头笑道:“见淡了,这可好了。”
宝钗微微一笑,说道:“妈看看这个,方叫丫头给算完的,我说有亏损,妈只不信。”
薛姨妈忙要过来看了一回,并不甚懂,只说道:“数目果真都和他们报的一样?不是丫头算错了罢?”
宝钗道:“妈放心,是落夕算的,她倒好才学呢,不是一般的丫头,妈可看着可如何是好,该想想办法才是,再这般下去,天长日久,必有后手不接之日。”
薛姨妈叹息一声,说道:“我的儿,也难为你了,照说不该让你插手,你那混账哥哥不在,那些人我又信不过,着实无法,咱家如今这般境况,你也见了,自从上次拿钱赎你哥哥出来,生意就屡作屡赔,如今有三家店铺大没人了。”
宝钗笑道:“妈也别急,我问过金二,咱家生意不好,主要是附近有了新的店面出来,一样的东西,却比咱们更好许多,——咱家再不该只图便宜,卖那些旧东西了。”
薛姨妈道:“我何尝不知道这些,要好的东西,就要拿钱来,咱家现在哪里寻那些钱去?”
宝钗便也发愁,须臾,笑道:“妈也别急,现我倒有一法,弄得钱来。”薛姨妈忙问,宝钗笑道:“颦儿前段日子得了遗产,听说那两个古董很值些银子,咱们何不借了来,暂解燃眉之急?左右她现在也用不着。”
薛姨妈倒也觉此法可行,只是犹豫道:“好是好,只怕我们贸贸然说了,况那是林老爷留给她的,照她那性子,未必就肯借。”
宝钗笑道:“我们自是不方便说的,只将现在的难处告诉姨妈知道,让姨妈对她说,想她寄居贾府的,见姨妈出面,定然不好拒绝。”一时悄然商议一回,遂定了,薛姨妈便要次日一早去和王夫人说,也不话下。
不说那边,且说这日黛玉因日前之约,特会了探、惜两个去瞧迎春,谁知赶了个热闹,迎春的奶娘正和司棋等人吵呢,正不可开交之时,猛然见他们姐妹等人来了,奶娘便忙先住了口,赶上前来陪笑问好,探春碍着她是迎春奶娘,也不能怎样说她,只点点头进去,司棋等忙打帘子倒茶招待,知道黛玉怕冷,又独给她一个手炉,迎春此时正倚在桌前阅读,好气定神闲的模样,惜春便笑道:“姐姐好定力,这外面吵的昏天黑地,你竟浑然不觉,若我及得上姐姐一半,将来可不必愁正果不得呢?”说完,姐妹们便笑,迎春便笑道:“她们吵她们的,我看我的,两不相扰,岂不好?”
众人皆点头笑,探春问司棋道:“怎么回事?”
司棋巴不得探春问这一句,说道:“嬷嬷偷拿了姑娘的金钗去顶赌债,我们不过白问了两句,她臊了,倒跟我们大吵大嚷的。”
探春知这不是小事,便叫人‘让王嬷嬷进来’,一时到了跟前,便问缘故,王嬷嬷只垂目陪笑,并不承认是偷的,只说是‘借’,司棋忙冷笑道:“你倒乖,看着三姑娘在这里,你怕她,所以不敢承认是偷的,若果真是‘借’,怎么我们姑娘一点都不知道?还反问我们哪儿去了?问了一圈,皆说不知,你还赖呢。”又对探春笑道:“姑娘很该好好问她,素日我们姑娘好性,凡事由着她们胡闹去,今儿竟偷起东西来了,想必偷了这个,就定然偷了别的,也该审审清楚,不然我们都成了贼了,大家不干净!”
王嬷嬷不由得红了脸,忙道:“你别混赖人,谁又偷什么来?这次不过是急着用,才暂且拿着,打算回来告诉姑娘的,从前我们也常暂借姑娘的东西,姑娘也让,你们又挑什么刺儿?”
探春便说道:“你们也不用在此嚷,我已经明白了。”便对王嬷嬷说道:“这事本是你的不对,我也不多说,赶快将金钗拿回来还了二姐姐是正经,若不然,我便回了二奶奶,只一条酗酒聚众赌博的罪名,你就现吃不了的亏,连老太太也是最厌这个的,你这么大年岁,不说规劝着点别人,反倒自己去犯法,如今又拿主子的东西抵债,岂有此理?”
王嬷嬷见探春眉立,知其恼了,便唯唯答应,也不敢太言,一时去了,司棋等人都满面笑色,都说探春说得好,探春微微一笑,道:“我身边若有这样人,我早撵了,二姐姐也太纵容她们了些个!”
迎春便说道:“她毕竟是嬷嬷,我又能将她如何?不如由得她去,视若无睹,也少了许多是非,岂不两下相安?我也闹个心净。”
黛玉一直在旁默默坐着,——知皆是别家的事,她不便开言,此刻听迎春此说,便悠悠上前,看了一下她所看的书,竟是佛书,便掩口笑道:“你们听听她这话,才四丫头才说完她,她又做此超脱之言,我还道是为何,原来却是引经说法,真的开悟了!”屋中人都笑,并迎春都笑了,姐妹们见她尚好,说笑一回,便出来了,探春欲邀黛玉去秋爽斋喝茶,黛玉因说‘要回去吃药,改日再去’等语,也就罢了,这边念红便搀扶黛玉回去。
念红见四下无人,便说道:“姑娘可知二姑娘定了哪日出嫁?”
黛玉道:“说是明年罢?确切日子就不知。”
念红说道:“我听人说,是明年春天。”黛玉便点点头,暗暗叹息一声,心中也不知是何滋味,忽见弘历迎面来了,看着她笑道:“怎么才出来,你们‘闺阁之言’也够琐碎的。”
黛玉便知他一直在外等着了,遂淡笑道:“有事?”
弘历笑道:“凤丫头给拿来了山竹,说东府孝敬的,我想着你爱吃,没舍得动,站这儿专等你去呢。”
黛玉听了,尚未怎样,念红先笑道:“今儿是怎么了,又是有人请喝茶,又是有人请吃果子,我们姑娘几时这么受待见了?——要我说,四爷竟也不必费心,既是稀罕东西,第一层老太太、太太得,第二层便是四爷和姑娘得,二奶奶必早派人送来潇湘馆了,四爷若不信,便请跟我们家去瞧瞧。”
弘历也心知肚明,却故意笑道:“别说大话,我是客,方才能得,我就不信你们也有。”
念红忙拍手笑道:“这可正好,不如四爷和我赌一场,若你输了,便一日不许委派思萧事儿做,只让她跟我顽!”
弘历哈哈笑道:“甚好,这个赌注很妥当,反正她每日家也只是到处逛玩儿!”黛玉只说他们‘胡闹’。
遂一起回去,还没进去,便见紫鹃出来笑道:“姑娘回来了。”
黛玉便问紫鹃道:“我走了,家里可有人来?”念红,弘历等都在黛玉身后抿嘴笑,紫鹃也不知何故,愣愣地说道:“才二奶奶派人来问姑娘身子,又送的东西,我放桌上了。”
念红便笑道:“怎样,我赢了罢?我说我们姑娘可今非昔比了,四爷还只不信。”黛玉便淡淡一笑,看念红一眼,道:“不过为的那些虚名身份,又不是真的为我,就至于这么高兴了。”念红遂一吐舌头,不说话了。
紫鹃又道:“太太处才也过来个小丫头,也问一回姑娘的病,还说太太找姑娘,若回来了,叫去一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