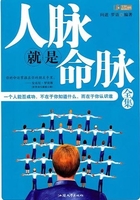话说宝钗去看黛玉,也不知怎地,就将雪狮惹得勃然大怒,不但咬掉其一只绣花鞋,更是一口扯裂了宝钗的裙子,这一下直让宝钗魂飞魄散,死命地挣脱了,便光着一只脚,穿着亵裤,四处乱躲乱藏地逃命,这边探春等并丫头们正听紫鹃讲述‘见闻’,待听到了院中声音,不觉惊愣,丫头出去一瞧,惊回道:“院中一只绣花鞋,雪狮没了。”众人皆微微变色,探春道:“可别是宝姐姐罢?”忙出去四处找寻,又见门口一条裙子,都道:“可不真是宝姐姐么!”黛玉跺脚道:“这烈犬,真真给我惹祸了!”忙让紫鹃等人唤雪狮回来,众人慌地四下去找,找了半日,方在花园东头的假山上寻到了宝钗,——也不知是怎么上去的,正蹲缩在两个石头缝中间,衣不蔽体,缺鞋少袜,哆哆嗦嗦,等人来救呢,黛玉等人忙命丫头去取裙子鞋来,一顿折腾,方将宝钗穿得周全了,却早引得一群丫头远远的偷看,皆暗暗嬉笑,黛玉自是一番赔罪道歉,宝钗见当着这许多姐妹们,又被许多丫头看去了,心里又惊又臊,也不好说什么,只一声不吭,含羞忍气地回去了。
待到了家,回思方才之事,又是后怕,又是气闷,又觉没脸,勾起近日许多不顺心来,便伏在被上暗暗哭泣,丫头忙跑去告诉薛姨妈知道,薛姨妈便来问何故,宝钗更觉伤心,遂一五一十地说了,那薛姨妈虽平日是宽容好性儿的人,此刻听了宝钗一番主观臆断,添油加醋的话,道是‘黛玉知那狗烈,却故意瞒她一个,听见狗儿咬她,只闷在屋中不理会,半晌方出’,不觉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只当是黛玉故意让宝钗没脸,想起前面‘干贝汤’一事,越发涨红了脸,浑身哆嗦,气道:“这林丫头如今认真要和我们作对!三番五次地生事弄景,今儿又纵狗咬你,长此以往,我们娘们还不被她害死了?也欺人太甚些个!”便气得要出去,宝钗忙拉着,泣道:“妈别找她理论去,她牙尖口利的,你必说她不过,况那狗着实凶得很,再伤了你,如何是好。”薛姨妈气道:“我不去她那,你只别管了。”便抽手而出,一路气势汹汹,直奔王夫人处来,彼时王夫人正念完了经,忽见薛姨妈红着眼圈进来了,进门便哭道:“姐姐须救救我们娘两个!”丫头们一听,知有情况,面面相觑,都忙避出去了,薛姨妈也不等王夫人问,自己将这前因后果尽数说了,又道:“便是她如今多么尊贵,再没有这么祸害人的道理,宝丫头素来蠢蠢笨笨的,害人的心一点没有,却总是三番五次着她的道儿,今儿是躲得及时,若非不然,可不定怎么样呢,她若真有个好歹,我索性也让那林丫头纵狗咬死我,我陪宝丫头去罢!”王夫人只听她一面之词,自然甚是大怒,便要去找老太太说,薛姨妈拦着不让,拭泪说道:“罢了,找了老太太,未必能行,我刚才也是一时情急,失了方寸,你是知道的,我通共身边这么一个省心的,今儿那情景,也算得上生死一线,我听了,如何不急?如何不哭?你也不必找老太太去,只寻机点一点那林丫头,叫她也别太为难我们孤儿寡母的,遇事高抬贵手些,也就成了,我们宁可吃这个哑巴亏。”王夫人气怔怔的,想了一回,冷哼数声,便道:“你放心,这事儿我必给你撑腰,如今这府里我还说了算,我不信就这么没王法了!——今儿就我们姐妹在这,我有话直说,你不知道,如今老太太也糊涂了,前儿赵姨娘央求讨袭人去伺候环儿,她竟应了,还说‘可怜袭人服侍一场,只要不在宝玉房里,这倒也好’,那袭人因何被我撵了?如今哪能竟眼巴巴地看着‘放虎归林’,又成什么道理?我不过白阻了两句,以为老太太明白的,岂知她竟就恼了,说我白吃斋念佛的,竟没有半点慈善心肠,噎得我没话说,这几日虽照旧去请安,早一句旁话不与她说了。——不是孝不孝顺的话,而是心里窝火。”薛姨妈听了,便点头叹道:“你也够为难的,且熬着吧,索性也用不得几年,就出头了,我也知道你这苦处,今儿这事儿,宁可不叫老太太知道,我们怎样还倒是末的,别又叫你惹气。”王夫人冷笑道:“正是因了这事,要向老太太讨个说法呢,我看看她老人家且怎么说,还向着她那孙女不了!她平日也是‘礼’不离口的,这样一个诗书大族,再没有这么大喇喇的欺负起亲戚来的理儿,想必老太太也必不会自己打嘴!”再不顾薛姨妈的阻拦,只拗着性子去了,彼时贾母身边只有紫鹃几个丫头伺候,正嫌没趣儿,叫请三春来陪说话,王夫人见贾母淡淡的,倒也不敢太露气焰,仍旧敛声屏气,只说道‘林丫头纵狗,将宝丫头伤了,这会儿子哭呢,姨太太来找我说,意思叫林丫头将狗拴着些,我想这也不是小事,特来请示老太太。’贾母听了,先唬了一跳,便问宝钗现今如何,王夫人道:“她跑得还算快,倒没受伤,听说丢了衣服鞋子,弄得好大没脸,这会儿子在家哭呢。”老太太听说没事,便放了心,回思一回,看王夫人气色口风,便知道了八九分来意,先派了个丫头到宝钗处去,‘只说我说的,替林丫头跟她赔不是,这是林丫头错了,改日我说她,叫她别哭。’又让人去告诉紫鹃拿链子栓狗,王夫人见只三言两语就打发了事,如何肯依,便又绕到‘纵狗’‘得罪亲戚’的话上去,此时探春,惜春等姐妹们都来了,听了几句,探春碍着王夫人,并好不说什么,惜春年小单纯,便道:“太太想必误会了,林姐姐当时跟我们说话呢,并不知道院中何事,何来‘纵狗’之说?再说,我们都没事,只宝姐姐有事,想是她将那狗惹恼了,也未可知。”王夫人心中不觉有气,面上点头笑道:“我也正在这纳闷呢,你们都没事,怎么偏偏宝丫头有事?况每次都是她有事,怎么就这么巧?我倒不解。”惜春也听出话外音来,也不好说话了,只敛声屏气,暗暗撇嘴,探春,迎春更是无语,贾母扫一眼王夫人,便道:“林丫头在我身边长大的,她怎么样儿,我很知道,断然做不出这样的事来!况姑娘们都作证了,只一口咬死林丫头欺负亲戚,也太武断了些!说起来,不是我偏袒哪个,护着哪个,若说起亲戚,那宝丫头是亲戚,林丫头就不是亲戚了?那狗终是蠢物,既宝丫头没伤到,这是万幸,好生安慰了她,再将狗栓上,也就是了,你这样气不忿的来了,又说上那些,难道是让林姑娘偿还过来,让狗再咬一番林姑娘不成?可是这个意思?”王夫人见贾母声重,且话也说得有点不像了,便也不敢再多说,只唯唯陪笑道:“老太太这是什么话,我不过白纳闷两句罢了,又不是认真生气,那宝丫头到底也有错处。”贾母这方点头,说道:“你这样想,倒是好的,那林丫头也是通情达理的孩子,素日又极小心谨慎,今日这事,还不定怎么愧呢,她无父无母,投奔了来的,又多病多痛,咱们凡事宁可多担待些,也就是了。”王夫人只得说‘是’,站了一会儿,贾母便叫她下去,这边王夫人一路闷着回来,薛姨妈问道‘怎样?’王夫人道:“忍罢!”将那满绣芙蓉的大团扇向桌上一摔,气呼呼地坐下,越想越辱,越想越气,便说道:“这事儿且记着,我就非不信这个邪,小小年纪,要成这里的东风,也未必能够!便她是玉皇大帝的干女儿,这家还是我当!”薛姨妈听了这话,不过叹息一声,反倒劝她,也不消烦记。
且说林黛玉经了今天这事,知是自己之过,对宝钗好大愧疚,午后又去探视一番,丫头只说宝钗惊了,谁也不见,少不得又回来,落落寞寞,茶饭不动,至于晚间,弘历来看视,隔着窗子,见黛玉独自一人在灯下和雪狮说话,似有郁郁叹息之状,便问紫鹃何故,紫鹃遂说了原委,又道:“我们姑娘正伤心呢,只说‘今儿有这事,姨太太那边不定怎么恼我,连并太太都要惹恼了’,我们也劝不好,可巧四爷来了,好歹劝劝我们姑娘罢。”弘历笑道:“我一日不在家,竟然有这好笑的事,这当了什么?要为此伤心,可真真不值了。”遂悄悄进了屋,见黛玉正蹲在地上,以手抚弄雪狮毛发,口中默默自语,皆是自怨自艾,感怀身世之辞,忽觉有人,见是他,便不说话了,弘历笑道:“又蹲着,待会儿必定头晕,还不好好坐着呢。”黛玉也觉有些麻酥酥的,便默默依言去坐,这边弘历摸着雪狮身上,笑道:“好狗儿,好狗儿,果真能通达体贴上意,你倒说说,今儿你是如何羞辱那厮的?”黛玉嗔他道:“人家正为这个烦心,你倒来取笑!”弘历笑道:“有什么烦心的,这样很好,有它在,以后这潇湘馆也少进来些混账人!”黛玉只不理他,只叫来紫鹃,让拿钱去厨房要熟肉来喂雪狮,紫鹃便拿钱让念红去了。
这边黛玉因问:“你今儿一天去哪了?”弘历笑道:“去探点情况,且先不告诉你。”黛玉哼道:“你爱说不说,我也没心情知道,只一句,那‘甄老爷’,你打算如何?看着他怪可怜的。”弘历笑道:“巧了,今儿正是为探这个去的,见了许多的人,我现越发有些怀疑,那甄士隐,恐就是香菱失散的爹爹。”黛玉道:“你才怀疑,我早就想到了,是或不是,让他二人见一面,不就都明白了?”弘历有些犹豫,黛玉便知何意,微微笑道:“我知道了,找个日子,我邀她出来就完了。”弘历道:“这是一则,我还想着,假若他二人真是父女,牵涉的事情可就多了,只怕到时惹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来,一时不好收场,况我也不想让你趟这个浑水。”黛玉道:“这是什么话?你做这些,也都是为我,我倒万事袖手旁观了,哪有这理?”弘历笑笑,半晌,方道:“你知道我是为你,已经足矣,你现在这境况——”一语未完,止住不说,黛玉听了,正触动心事,又感又伤,便也一言不发,两人便皆垂首静坐,竟半声也无,心中却都是千丝万缕,思绪不止,一时也无可为记。
且先不说这里,只说念红拿了银子钱去厨房要肉,还没进去,可巧看到柳嫂子家的四儿,念红便和她聊了几句,四儿见她拿着许多钱,便笑道:“你们姑娘今儿请客不成?便是请客,也不用拿钱来,我妈定乐得搭上呢。”念红笑道:“哪是姑娘?是那个雪狮,姑娘怕他吃的多,才让拿这些来,说先放着预备,不够再给。”四儿听了,怔怔片刻,忙把念红拉扯到一边,问道:“你说的雪狮,可是今儿惊了宝姑娘的大犬?”念红说了声‘是’,便问怎么,四儿忙道:“既如此,我劝你倒别进去了,你不知道,太太今儿让人来说,林姑娘若要给那狗买肉,只说没了,不许给,让姑娘到外头买去,还有好些不好听的话,火气大的很呢,你幸是遇到了我,若这么进去了,她们不知轻重的胡乱一回,你必然生气,倒像她们刁难不给,倒不好,今儿就索性这样,这几日你们就且先外面买着喂罢,等太太的气消了,你再来要。”
话方说完,见柳嫂子家的在屋里叫她,她忙答应着进去了,念红这边略略回思,便知是王夫人因今日宝钗一事,借着狗撒气,顿时憋闷,待要回去,又不知拿什么和黛玉交差,——若和她说了实情,必惹得她伤心,待要不回,王夫人令下,她还能进去抢肉不成?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反反复复,心中忽生酸涩,不觉泪下,强忍了半晌,到底回了潇湘馆,回说‘熏肉没了,只有些残剩的,柳嫂子说怕狗儿吃了肚子疼,所以没给’,黛玉听了,只得罢了,紫鹃便道:“怎么眼圈红红的?”念红强笑,道:“才四儿踩了我新鞋,和她拌了几句嘴。”紫鹃便笑:“这点小事,就至于哭了。”念红当着黛玉等人,也不答言。
一时弘历离了潇湘馆,正要回落英阁,走至半途,忽又折身拐去了厨房,柳嫂子等人都不在,只有两个媳妇在那里偷做东西吃,见他去了,忙把锅盖上,弘历也不理会,只问今日念红取肉一事,其中一个明白的,便将王夫人的话滴水不露的学了,弘历边听边笑,点头说一个‘好’字,转身就走,一路衣衫鼓鼓生风,方到了落英阁,便大声叫斗儿,浣纱,绣儿等都不知何故,一时斗儿来了,弘历说道:“明儿你去买三十头牛,三十只羊,鸡鸭各一百只,另聘些人,给我敲锣打鼓地送进来!银子去凤姐那去要,就说我说的!”浣纱忙问:“要这些活物做什么?”弘历道:“喂狗!太太不让厨房给肉呢,我自己买,总行罢?”浣纱又道:“那也不必买这么多,还敲敲打打,弄得万人知道的。”弘历突然看她道:“我就是要弄得万人知道!”回头喝斗儿道:“就按我说的办!”斗儿忙一叠声地说‘是’,忙下去了,这边弘历双手插着腰,来回踱步,冷笑道:“素日就是我顾虑的太多了,做事缩头缩尾,如今索性一切摆在明面上,谁要和我对着干,就尽管来!”浣纱二人鲜少见他生这么大的气,皆面面相觑,不敢则声,半晌,浣纱方小心翼翼地笑道:“好端端的,太太为何不给那雪狮肉吃?必有缘故,——是了,定是因为今儿宝钗一事,你这样张扬,岂不是摆明了和太太作对?我劝你消消火罢,如今我们住在人家,何况——”未等说完,弘历断然喝道:“住他家又如何!我吃用都是自己出,又没占他家一分一毫,难道就矮了一截?就该凭空低三下四?便不提这些,我这身份,难道不配住在他家不成!”浣纱忙笑道:“四爷今儿是怎么了,我不过说说,你就这么大气,脸都红了。”绣儿端来一盏茶,说了一句‘四爷歇歇’,弘历方坐在椅子上,喘息半晌,说道:“我以为福晋认了妹妹做干女儿,便万事大吉了,看来我还是低估了这些人,许是想着‘远水解不了近渴’罢?才敢这样!”绣儿便道:“要我说,就是因为林姑娘没钱,若是因什么‘远水解不了近渴’,他们为何不欺负四爷?”弘历冷笑道:“不欺负我?那是你们不知道罢了,现就有例,我那些钱,都在凤姐那里往外放呢,一月可生出好些银子,我不过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再有,你们知道林妹妹上百万的家产,都哪去了?我一则不太在意那些钱财小事,二则也是看凤姐算个人才,对我也还过得去,不想太狠弄了她,本要放放,若这府里真把人往急了逼,也就说不得要办点惊天动地的事了!”浣纱早吩咐小丫头将大门关了,这会儿听到这些,不免有些心惊肉跳,生怕弘历性子上来,做出什么糊涂事,——可又不敢劝,一时也是无可奈何,唯有暗地里叹息祷告罢了。
谁知那斗儿也真是忠心听话,第二日下午,果真照数弄了许多的牛羊鸡鸭来,直将小半条巷子弄满了,另有十数个吹拉弹唱的,也跟着应和,一时鼓乐声与家禽,牲畜叫声交乱混杂,不绝于耳,早惊动了贾府,众人尚以为是东府那边给送来孝敬的,还有出言庆幸‘有鲜牛羊奶喝’者,谁知得回‘不是给人吃的,是四爷买来,专门喂狗的’,一时成为新闻,消息传到王夫人耳朵里,又见这大张旗鼓的景况,便猜定了内里详情——‘必是林丫头因我不许厨房给肉,气不忿,告知紫历知道,他二人才故意做给我看的’,不觉大为光火,只因是弘历买的,虽然着恼,并不好说什么,只能又暗恨在心,面上装不理会罢了。黛玉听了这事,却不免责怪弘历多事,弘历只笑道:“这不是多事,反是懂事,这狗本是咱二人养的,原该咱们准备肉食,如此一来,不也省去了他们嚼舌?”黛玉方不言语了。
闲话少说,且说自从甄士隐来了,每日只盼和女儿见面,弘黛二人皆知其心急,只是弘历不便和香菱见面,黛玉又因宝钗与她新增嫌隙,不好出面,是以暂且耽搁了两日,紫鹃知二人为难处,自思她和香菱甚好,且这又是香菱大事,便要代他二人行事,屡屡寻机,这天好容易得见,只说引她‘去见一人’,使其假借学诗名义去潇湘馆,香菱虽不知何人何事,倒也来了,这边黛玉且让她好生先喝茶,那边又巧立名目,叫了甄士隐去。
不一时,香菱见弘历来了,后跟着一个五十多岁,穿着青蓝褂子,胡须头发花白的老人,便要想避,黛玉笑道:“谁都避得,独这人避不得,你且看看可识得他。”念红,紫鹃等人便半推半送将她弄了出去,那甄士隐也是修行数年之人,微有道行,一见香菱,那心中便如火烙灼过一般,滚烫难受,念想顿异,许久之前的事,如今竟如重新放过一般,一幕幕看见,触手可及,只抖着说不出话来,那香菱看见甄士隐,便也生出一种怪妙之思,虽自认从未见过,却如至亲至近之人,只觉眉眼唇鼻,甚为熟悉,如心底勾勒出来的一般,一时也怔怔的,却不知泪早留下,正是:
至亲万里心有应,陌人咫尺眼不觉。
那紫鹃早关了门,黛玉等见她二人此状,不忍相看,便扭头回屋去了,黛玉一走,弘历也忙跟着进去,却见黛玉径直入了里间,泪珠滚滚而下,弘历笑道:“好好的,你又哭了。”黛玉便拿帕子拭泪,哽咽说道:“是人皆想承欢膝下,香菱尚有一父可认,独我父母双亡,孑然一身,今番见了此景,叫我怎不伤心?”弘历忙笑道:“又来了,你尚有一祖母疼爱,又有这园中许多姐妹,如今还有一福晋做额娘,况还有我这个哥哥,何谓‘孑然一身’?何必每日只做‘司马牛之叹’?快别难过了。”好劝歹劝,黛玉方略略止住了悲,却见紫鹃来叫,弘历忙携了黛玉出去,香菱眼睛桃儿一样的,又是喜,又是悲,又有些惴惴不安,甄士隐说道:“今日父女相认,全赖四爷,无以为谢,唯特此一拜。”便牵着香菱,齐齐拜下去,弘历忙扶了,笑道:“甄老爷别说这话,我可是有求于你,才帮你的,难道你竟忘了不成?”甄士隐一听,忙从怀中将那串莲花项链拿出来,笑道:“这个就是四爷要寻的那味灵药。”弘历听了,大感诧异,忙问:“这个坠子,不是香菱姑娘一直戴着的?如何竟成了灵药?”甄士隐便笑道:“四爷有所不知,小女满月的时候,曾遇一跛足道人,执意要化了我的女儿去,说她‘有命无运,累及爹娘’,我自然不从,那高士便给了我这一坠子,命我带了女儿身上,说‘或有失散,他日遇到奇人,再见莲花,便是父女团聚之时’,又说这莲花乃是‘绝世奇药’,我本不信,岂知万事万物,皆难逃于定数,人力再不能强之,直至今番,我方初悟。四爷今朝已得了此药,再得两味便可,那雪山奇葩,着实难寻,不提也罢,剩下两味,大可打听你那朋友知道,四爷乃不凡之人,想必那两味也不难得来,若三味均得,只需研碎,再寻庵庙各八处,采集其门前初冬之雪一钱,共十六钱,溶于一处,封于古坛,深埋地下,每周取出一些,以温水冲了服用,不出半年,即可去了林姑娘这先天不足之症。”弘历认真听了,心中大快,连忙称谢,黛玉也盈盈而拜,甄士隐只略微谦辞,看了一眼黛玉,便皱了眉,似有欲言又止之意,许久,方说道:“士隐虽只入道数年,阴阳乾坤之理尚不甚通,好歹也略解些皮毛,此刻心中还有一言,与四爷关系甚大,不知四爷可愿一听?”弘历听了,忙问何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