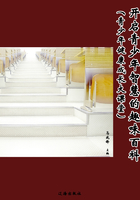一路只在她耳边说些笑话,又时而贴近细看帕子有没有缝隙,行了约十数里,黛玉已经有些不耐烦,才听弘历笑道:“就是这里了。”遂引她下了车,黛玉便听见耳外有水流娟娟,鸟雀啾鸣之声,遂说道:“可以拿掉了罢?”弘历方笑着为她解开帕子。
一时间,黛玉早已怔住,只见两壁万仞,峻如刀削,直入云峰,峭壁缝隙无数朵诡异之花,下一碧潺潺溪水,清可见石,蜿蜒游弋,却不知流向何方,再见自己,原是置身这苍崖边一道细细的石子路上,漫漫长风,悠悠小道,寥寥几人,不知何所归往,一只马儿,唯有原地茫然地踢踢踏踏,配着这震人心魄的山水之景,直让黛玉竟不知说何是好,千种情绪,万般情思,只独独汇聚成‘震撼’二字,点了点头,不知为何,眼眶竟红了,半晌,才悠悠说道:“素来高山大川,峭壁悬崖之流,只能凭借书中无数华丽辞藻想象,且不知人说‘纵穷其笔墨,亦难描画,穷其言辞,亦难形容’究竟何意,如今见了此情此景,我方明白了。”弘历便笑道:“此处景致还是其次,你可知它名头?”黛玉看他道:“有何名头,你且说来。”两人遂沿着水流蜿蜒向上而行,弘历笑道:“此处乃当日伯牙子期相遇之处,千古知己,就此而成。”黛玉忙道:“果真的?”歪头想了想,噗嗤笑道:“好不知羞!欺我孤陋寡闻不成?那可再不是这里的。”自己抿嘴笑着先走,弘历跟着笑道:“书上或有谬字,以此讹传,也是有的。”黛玉侧头笑道:“既如此,若见伯牙掩身的巨石,子期所弹的古琴,我就信你。”正说说笑笑之时,水流忽然折了弯,却见水流对面却有一凹进去的石壁,几个青白石阶,遍布杂草青苔,通一小亭,亭子中却是一方木桌木凳,桌上果有一古琴,凳上一方绒垫,弘历忙笑道:“这回你可信了罢?”黛玉先奇了一回,疑道:“这如何真出来一只古琴,定是你安排的罢?”弘历笑道:“我安排它做什么,这原是春秋以来就在这里的,别人都说这是子期留下的,只你不信。”黛玉嗔笑道:“你就唬我罢!那琴若在,也不叫高山流水了。”虽如此说,自己倒被此情景提起兴致来,摇摇至古琴边,以手抚弦,弘历再三让她弹一曲,黛玉方红脸羞目地坐下了,弘历便道:“此绝美之音,若无搭配,倒可惜了的。”遂从腰后变出一支萧来,靠着亭柱,只望着黛玉笑,等她先弹,黛玉也看着他,等他先吹,两人笑望片刻,黛玉忽然别下眼睛,盯着琴弦,忽以手速速抚动,却是一阵急促之音作始,弘历抿嘴一笑,说了一句:“纷乱急躁,琴如人心,难道是等我安抚不成?”便捡了黛玉一句音尾,以萧凑口,悠悠吹起,一琴一萧,便在这峭壁残流中两相应和,初时百鸟无声,过了片刻,长风渐渐急涌,溪流躁然,崖顶凡鸟乱飞,啾鸣相撞,原来这弘历和黛玉本有仙界宿缘,如今心灵相合,作此弹奏,便如凡世忽见天音天语,自惹得红尘万物躁动不安,难以自控,而弘黛二人却浑然不觉,唯彼此互现心事,如问如答,不一时,便见崖顶飞来两只彩羽大鸟,一只紫红,一只青黛,两相追逐,若即若离,怪崖嶙峋,双鸟虽有羽翼,却每每险些撞上,琴萧之声渐止,双鸟最终却是两相并肩,比翼南去,翩翩不知飞往何方了。
且说两人弹完一曲,黛玉凝目而坐,弘历默然擦萧,两下竟然都没了声音,然不知为何,彼此心中似如一股暖泉涓涓而去,流于至深之处,虽彼此未置一词,却似乎曾有千言万语一般,甚觉慰藉,许久,还是弘历先笑道:“走罢。”黛玉略微点头,起身跟着他。
两人一路也不说话,弘历倒是甚为悠哉,捡起路边的石子投水,捡起一个,投掷一个,不一时,见小路渐窄,溪水渐阔,崖肩却低了许多,对面一小壁绿藤,弘历忽然说道:“你饿不饿?”黛玉道:“还罢了。”弘历便上下衣襟摸索个遍,黛玉疑道:“找什么呢。”弘历道:“看能不能给你找点吃的。”黛玉便道:“别弄景了,你这身上还能寻到吃的呢,我并不饿。”弘历遍寻不果,唯见手中一个彩色小石头,便叹一声,道:“既没吃的,只能靠它了。”黛玉掩口一笑,道:“如何靠它?你能吃了它?”弘历只笑笑,对黛玉指了指对面绿藤,一时看准,猛然将小石子遥遥掷了过去,却听极其清脆的一声,片刻之后,绿藤之后忽有石门打开,声音沉重古朴,内里黑黝黝一片,黛玉不觉笑怔了,只看着弘历,弘历笑道:“怎样?老天再不负我的,咱们且过去看看。”黛玉见溪水甚宽,中只铺就一溜石头而已,便有些不敢,弘历便先跳上其中一块,把手伸给黛玉,黛玉红了脸,小声道:“我自己走。”弘历只盯着她,笑道:“石头滑,不是顽的,来。”只盯着她看,手也只伸着,黛玉犹豫半晌,两下相持良久,黛玉方递过手去,弘历面上笑意顿时荡漾开去,如绽开春阳,心中美不自禁,忙小心翼翼扯着她,好容易过河。
原来藤条后面原是一处山洞,一时进去,黛玉见石洞很是宽敞,四壁打磨的光亮,壁上八处烛台,均已燃上蜡烛,烛下却是一石桌,桌铺白席,席上八菜两汤,皆是自己家乡口味,碗筷具备,酒已斟满,一时顿知原委,心中不禁百感交集,温情弥漫全心,暗叹思道:我还只道陪他出来顽,他却万事只为讨我开心,这奇山峻岭,怪洞嶙峋,如何能没半个人?必是他花了心思,连并早事先安排好的!——长亭古琴,家乡之宴,这等苦心,竟让我说什么才好。面虽微笑,不觉间泪意萌出,却强忍着,并不再强问此席来处,只当不知,遂和弘历同桌而食,弘历见她只不开言,笑道:“今儿既出来,索性抛开家中那些繁文缛节,别只闷头吃饭,倒是边聊边吃的好。”便引她说话,黛玉倒也不拘此节,一时两人提到黛玉家乡,遂提到当日入贾府,至于府中众人身上,黛玉不免又郁郁止口,弘历自知她心,想了想,笑道:“若我说,皆是你素日太轻看自己了,你想,二妹妹并不是正方太太养的,大老爷又不讨老太太的好,三妹妹又是庶出,四妹妹不过是那边珍爷的妹妹,其他如宝妹妹,云妹妹之流,更是歪三拉四,不足一提,而你却是老太太亲外孙女,你亲娘可是她至亲骨血,若谈身份,谁比得上你?你倒每每只当自己是最末等的,我竟不知为何。”黛玉道:“你知道什么,人家都是有根有基的,哪像我,既没父母,又没家业,一穿一用都是他家的,便再是至亲,也难不受人口舌。”弘历便道:“若照你这么说,如今我也该哭去了,我在府里,一个亲人都没有,倒还不如你呢。”黛玉忙道:“你怎能跟我比?你吃穿都是自己的,何况还有堂堂亲王撑腰,哪像我,谁给我撑腰。”弘历断然道:“你吃穿也是自己的,你不是没家业——”说到此处,觉此话先且不宜说出,忙又道:“何况,你也并不是没撑腰的人,你有老太太和我,这还不够么?”黛玉起先还凝神听着,一听后面,咕哝了一句‘谁用你撑腰来’,顿时低下头来,一声不吭,弘历也有些脸热,便讪讪笑笑,闷头吃饭,方才两人争论,石室便有嗡嗡的数重回声,这会儿两人不语,一时顿觉静寂,竟听见岩壁滴滴答答的水声,不绝于耳,好半晌,黛玉悠悠轻叹道:“遍府之人,唯有老太太一人疼我,我虽知道,却半点报答不得,也是心中一桩憾事。”弘历听了,不觉一笑,也不说话,两人饭毕,弘历却不将黛玉从原门带出,却是引到后面,却见又是一个小石门,通一隧道,黛玉笑道:“今儿可有趣,这又是去哪的?”弘历笑道:“出去便知。”两人便一前一后,微微弯身而行,行了有半截香之久,方见前头簌簌点点的亮光,近了,却是一丛绿枝掩映,打开一瞧,入目一片漫天花野,艳阳高照,天畅地阔,又与方才之景大不相同,花中一道芳径,通向遥遥一处盘旋的高山,有陆续不绝人影沿山而上,山顶微露一古庙,悠悠似闻钟声,弘历忽道:“今儿是初几了?”黛玉惊羡未定,魂不守舍,只看他道:“什么初几?”弘历笑道:“傻颦儿,今日可是十五呢!”黛玉道:“那又怎样?”忽然恍然大悟,跺足说道:“正是,你说带我去求灵佛的,可是扯谎呢!”弘历笑道:“可这仅仅一日,如何到得了滕州?”黛玉一时语结,想他一路周全,凡事早有准备,便道:“你必有办法的罢?”弘历见她痴痴怔怔的样子,甚是柔美可爱,心中忍俊不禁,假意长叹,笑道:“我又能有何办法?——不过昨儿累了一夜,将滕州的金斋庙搬到这来罢了。”黛玉一听,知山中古庙便是金斋庙了,可见路上滕州一说全是逗她的,一时哭笑不得,便恨恨地锤他一下,嗔道:“就会编谎骗人!别让我再理你!”自己扭身,沿着花中芳径一路去了,弘历忙笑跟着,说道:“妹妹且先不能不理我,那灵物奇特,须得从方丈处得来,方丈乃是得道高僧,旁人想见甚难,还得我帮妹妹引荐。”黛玉笑道:“你又夸大其词,这次再不信你。”弘历道:“别的能骗,这次可再不能骗的,你若不信我,必拿不来那灵佛,岂不虚走一遭?”黛玉听如此说,方信他了,只道:“最后一次,若拿不来,看我不拧你的脸!”弘历忙唯唯笑着答应。
一时好容易到了山下,黛玉早已香汗淋漓,喘不自禁,弘历心中不忍,便要让她坐抬椅上去,黛玉因说有碍诚意,执意不从,弘历拗不过她,只得由着,这一路停停歇歇数十次,走了大半日,才至山顶,弘历虽并不觉什么,黛玉却坐在一处石上,背靠着树,早已娇喘细细,难以禁持,弘历见她此状,倒后悔起来,忙递给她手帕,又要去为她讨水喝,黛玉强笑道:“你歇会儿罢,虽累些,却是我甘愿的,一生不过这一遭罢了。”弘历也不知说何才好,只道:“你放心,这事包我身上。”黛玉点头微笑不语。
忽见御剑大步流星过来,及至跟前,弘历道:“妥当了罢?”御剑冲弘历摇摇头。弘历假意看山下风景,小声说道:“多给他们银子。”御剑又是微微摇头。弘历不觉有怒,道:“好容易上来的,再没下去的理,若都不行,就露身份。”黛玉便弱弱地问:“什么事?”弘历忙笑说‘没事’,便对御剑使眼色,御剑左右为难,只得贴耳说道:“卑职已经尽力,只怕我们今天遇到大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