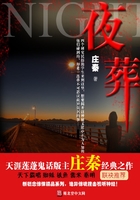弘历为免黛玉伤心,深夜跳墙,一路纵马向白日的城边小店去了,他只道无人察觉,岂知方才远远的正有一个巡夜的婆子,看似这边有一个黑影一晃,忙‘哎唷’叫了一声,再定睛看去时,哪里还有影子?思索一回,深知贾府这样的深宅大院最怕外贼潜进的,毕竟不敢独专,忙跑了来寻管事媳妇,寻了半晌,只遇见个来旺家的,便啰嗦唠叨了半日,只道‘也没看真切,恍惚见个黑影,大包小揽的跳墙出府去了’。
来旺家的也吃了一跳,忙问:“在哪看见的?”老婆子指东指西的,一会儿说是稻香村那边的,一会儿说夹道老树那边的,来旺见也问不出个什么,忙跑了来告诉凤姐,此时凤姐正和平儿笼帐,听完,先忙遣人告诉太太去,又道:“别慌手慌脚的!也别嚷!平儿去,多打几个灯笼,叫两个媳妇来跟着,挨个姑娘们屋子里巡查慰问一遍,若有丢失物件的,就记下来,告诉宝玉林姑娘等人都把门闩好。”又特特嘱咐平儿‘只不必到薛大妹妹房里去。’平儿应了,自带着众媳妇到大观园挨个嘱咐。
此时迎春,黛玉等人都躺下了,见来了这些人,都不免小小惊动一回,少不得各自查看半日,都说没有丢失的,唯雪雁插口道:“我们姑娘那会儿把一块翡翠掉在湖里了,不知二奶奶能不能叫人给找找。”黛玉便看她,嗔道‘你又多嘴,说那些不相干的做什么。’平儿忙问,黛玉只得说道:“不过是我不小心,掉湖里去了,倒很不用为此周折。”平儿忙笑道:“姑娘且别伤心,回头我定然告诉二奶奶,二奶奶近几天事情多些,等忙过这阵,必先找人给你捞去。”黛玉只得告诉‘劳烦’,一时平儿等又去探春,李纨等处查看,不提。
且说这黛玉本是个体虚身弱,缺觉少眠的,不意受了这一扰,更是走了困,便叫紫鹃把个大绒的软垫子立在床边,自己靠了,又叫拿书来,紫鹃直把被子给她掖到腋下,笑道:“日里喝了汤药,这才咳嗽的好些了,不说好生休息,又看书,今儿偏不依你。”黛玉便道:“我又睡不着,不看书,难不成白坐着呢?”紫鹃便笑道:“既然如此,看书也是劳神,不如我们说会子话罢。”黛玉想了想,笑道:“也罢了。”便自己往里面挪了挪,让紫鹃也进被子中来,两人靠着一个垫子,挨着肩膀,起先一阵静默,黛玉便笑道:“怪了,不是要说话么?”紫鹃抿着嘴笑,拿肩膀撞了一下黛玉,道:“你先说。”黛玉也拿肩膀撞了一下她,说道:“你先说。”紫鹃捂着肩膀,笑道:“呀,咯的我好疼。”两人唧唧咯咯笑一回,紫鹃便道:“姑娘若让我说,可别在中途拦我的话。”黛玉便哼了一声,道:“那得看你说什么了。”
紫鹃压着声音笑道:“今儿绣儿来,都跟我说了,我都知道了。”黛玉问:“知道什么?”紫鹃说道:“姑娘何必弄憨,若姑娘真把我当知己,就早该对我挑明,连那绣儿浣纱都知道了,姑娘还只瞒我,倒让我好不伤怀。”便别过头去,黛玉倒不由得一怔,心道:他的心事,竟然不瞒着别人!真真可叹可惧。又嗔道:“自己在那胡啰嗦些什么呢,我可不想跟你打哑谜。”
紫鹃便又转过身来,瞪着黛玉的眼睛,笑道:“人家都为你跳湖去了,你还想瞒谁呢,还不招来。”就要去胳肢黛玉,黛玉素来怕痒的,便笑得了不得了,忙求饶,一时罢手,黛玉喘息半晌,方道:“今儿我破个天例,不恼你,只快收起你那些歪心邪话罢!”紫鹃便道:“这里又没别人能听见,好姑娘,我的心事,你就听听又何妨?”黛玉一听,便拿双手捂着耳朵,紫鹃只一笑,便自顾小声说道:“我只是想着,姑娘自小是个孤苦无依的人,遍视府中,真心疼爱姑娘的唯有老太太一人罢了,倘或老太太有朝一日归了西,那时,姑娘好不好,又有谁真个挂心呢,虽有一个宝玉,姑娘也知道的,别看他平日对姑娘百般依顺,竟毫无半点魄力雄心,若真到了紧要关头,他必然是做不得主的,到时候就是为姑娘哭出一缸眼泪来,做出多少挽诗,又有什么用?”黛玉放开手,别过头去,说道:“你还提他!东西都烧了,还拿他比喻什么。”
紫鹃忙笑道:“我知道,只是说这话罢了,俗语说‘未雨绸缪’,姑娘只不去想以后的大事,若真到了墙倾树倒的一天,姑娘没了倚靠,又没个亲友惦记的,又没家产,到时候可怎么着呢?莫若趁老太太还健朗之时,做定了大事要紧。”紫鹃边说,便看黛玉光景,见她只是面朝里,用手捻弄着被子,虽不插话,以与从前之状大不相同,知其时听进去了的,便又笑道:“谈及这四爷,不怕姑娘笑话,我起初可并不喜欢他呢,做事张扬任性,眼睛长到头上去的,我只道又是个惯坏了的大家公子哥,便是看出了他的心意,也为姑娘存着一份忌惮,谁知这段日子仔细观察,倒越来越看出他的好处来,头一则,四爷肯为姑娘放下身段,处处为姑娘着想,担心姑娘的病,不说平日送的名贵东西,单说特特为姑娘请太医来,这份心思,就难得了,二则,那四爷为了姑娘,真真把自己的性子收敛多了,虽浣纱和绣儿知道,那都是他心腹,自是不瞒着的,再就连紫烟二人都不知道,人说本性难改,四爷能做到这步,自属不易,再细细回味,四爷从来没宝玉那些虚头巴脑的话,却办的都是实事,丢翠之事,便可看出他的心真意浓,远非别人可比的,这些都是我的小心思,我知姑娘心里也都明镜一般,只是藏在心里头,不说罢了。”
紫鹃说完,只等黛玉回应,黛玉却不语,屋子霎时寂静无声,只闻得窗外竹音窸窣,直过了半晌,黛玉方才悠悠长叹了一口气,道:“说完了罢?我乏了,睡罢。”紫鹃只得笑道:“也是该睡了。”便要为她铺被子,忽听得外边一片吵嚷喧嚣,乱成一片,两人都怔住了,便叫来雪雁,让去看看何事,一时回来,激动得不得了,又跳又说道:“真是新闻了!薛大爷翻墙,被人抓到了呢!”紫鹃忙道:“今儿正抓贼呢,难道是那薛大爷?”黛玉心中本自伤感,不期凭空出这一幕,倒觉好笑,便向雪雁道:“你再去看看,到底是怎么着——这会儿闹到这样,一会儿再唱一出《义妹救兄》,咱们就真真别想睡了。”雪雁巴不得出去瞧热闹,忙答应着跑出去了。
原来弘历日里厌恶薛蟠为人,存心要治他,便故意让他在婆子们巡夜的时间翻墙,又告诉他走哪条小巷,穿哪个胡同,皆是有人仔细守着的,心知他必上套,岂知弘历也着实高估他了,这薛蟠个子本生的矮,身子又胖,方拿砖运石的爬到墙上去了,好生不易,谁知竟下不来,但见下面黑黝黝的,也不知深浅,只得骑在墙上,一点点往下蹭。
也合该他倒霉,正值平儿等刚从李纨处回来,把他逮了个正着,夜黑风高,也看不清楚是哪个,先大叫大喊的找来几个男丁,七手八脚上前给薛蟠拿下,待要捆他,薛蟠直撕扯着嗓子大叫‘我是薛蟠’,平儿等人都有些疑疑惑惑,待凑近一看,不是他是谁?一时众人都暗生疑惑,平儿忙让下面的别声张,岂知经过这一嚷一闹,大观园竟然都被惊动了,彼时不说下人都来凑热闹,连带宝玉,李纨等也都来了,竟是围了水泄不通,不一时,连王夫人也扶着个丫头过来,口中还直问:“抓住贼了?怎么不绑上!”忙有人告诉‘是薛家少爷’王夫人倒给了说话人一巴掌,直说‘胡说’待见到果真是薛蟠,其状其景,竟是语言描摹不得的。
早有人告诉薛姨妈,宝钗等人,只说‘薛大爷在那边翻墙进来,被人当贼抓住了,府里一群人围着,不知怎么样呢。’薛姨妈唬了一惊,忙问:“那孽障头里不是说这几日要跑外面,回不来的?又跑这里翻什么墙来!”忙让打灯笼拿衣服,宝钗也跺脚道:“哥哥也太作的不像了!”又担忧薛姨妈,忙过来劝道:“妈妈别慌,也别恼,大家都知哥哥必是淘气,我们这等人家,什么没有?怎么会拿别人家东西?何况还是姨妈家——等会儿问明白原委,大家好好的说明白了,自然见得分晓。”嘱咐一回,陪着薛姨妈过来了,薛姨妈见人影幢幢,自己挤着进去,彼时薛蟠身带酒气,眼睛乜斜的,怀中还抱着两壶好酒,见自己妈妈妹妹也来了,似有了底气般,倒自己在那大嚷大叫,薛姨妈不禁气得满面通红,浑身发抖,先冲上来打了一个嘴巴,恨道:“孽障!你死在外面也罢了,跑这里闹什么!”李纨等人倒忙劝,皆说道‘他小孩子家,原是玩玩的,也不过一场误会’乱着一阵,好歹把薛姨妈等人都劝回屋子去了,又把下人都遣散,王夫人又让人去告诉:“明儿谁在老太太跟前提这话头,先打一顿板子。”大家都心领神会,口里答应着,私下少不得回去一番窃笑,无须多述。
且说薛姨妈经了这一番事,觉得好大没脸,待回了屋子,遣走下人,又把薛蟠叫近身来,不免又是一顿训骂,又问缘故,那薛蟠已是一番沮丧,只道脸已丢了,若说出原委来,叫人知道是弘历叫他来的,明儿再不待见他,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便拧着脖子不说,薛姨妈恨得了不得,便拿着宝玉比他,说他这样不好,那样不好,薛蟠便渐渐红了脸面,说道:“罢,罢,快别说了,那宝玉就是天上的神,我是地上的土,何如?何苦来!成日家只是羞辱我,我竟一文都不值的,见到那宝玉来了,便又是摩挲,又是体贴,不知如何是好了,难道等妈妈百年之后,归了西,那宝玉能顶着您老上五台山不成?何必只褒贬的这般不堪,让人寒心!”宝钗听他此言,见薛姨妈又气得眼睛发怔,忙断然说道:“哥哥老实些罢!也不怪妈妈说你,哥哥也闹得太过火了,今儿正查贼呢,偏你就往枪口上撞,我们原是客,暂居这里的,且不说那些下人们如何说咱们,若是让老太太等人知道了,又怎么想?还怪妈妈羞辱你,你只做哪些讨羞的事,连带家人都跟着没脸,我都看不下去了,你自己想去。”
薛蟠听了这话,自知无可回复,急怒攻心,不禁冷笑几声,也不管想到什么话,也不管当说不当说了,接着一股酒劲,索性咬牙道:“罢了,好妹妹,你也不用说那些话堵我的口,难道我不知你的心思?从前你听人说,你那身上的金锁该有玉来配,便留心了,动不动便把金锁拿出来显摆,弄的众人皆知的,好都说你和宝玉是天生一对!前段儿时候看这府里又来了紫历,模样,人品都比宝玉好,又是十三王府的,便忙把金锁藏起来了,整日家费尽心思接近四爷去,又叫我满世界的买药材,好给人家颠儿颠儿送去,你只道别人不知你的心意,其实大家心里都明明白白的,难道就你聪明?就只有你算计别人的?我也劝妹妹收收心罢,你既自封为贤良淑德,正该每日在家做做女红刺绣才是,也不枉费了这虚名,那才是闺房女儿该干的事,何必每日这样机关算尽的,且天下之不如意十之八九,我看那四爷也是个精明人儿,未必就吃你这一套的!”
不知宝钗听了这番话,是何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