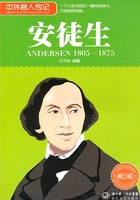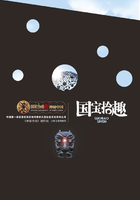弘历遣绣儿至黛玉处去借《诗经》,岂知等了许久,彼处半点动静也无,不免心灰意冷,只道终究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他自问不是伤春悲秋的戚戚之人,独这一回,心底竟生出缠绵无尽的悲哀凄凉,竟是从来都未曾有过的,自己也暗暗纳罕,岂料绝望之时却有峰回路转,竟有黛玉的小丫头雪雁送书来,虽并未多言,弘历却已经惊喜交集,好半天方怔怔地信了,此时心情,远非言语所能名状也。
这里浣纱伺候了弘历躺下,因他说要读书,便没有熄灯,弘历见她走了,便把那书小心翼翼地拿过来,躺在床上一遍遍抚摩着,又细闻书页之中,幽幽然似有一缕清香,只觉心神俱荡,美不能抑,至于抱书于怀,整晚笑意微微,仿若平生之最快人心之事莫过于此者。
且不说他,那林黛玉此刻虽已躺下,亦是意绵情漾,思绪难平,因思如此轻易便露情于他,丝毫不顾嫌疑之防,是觉可惧,又思两人虽此刻互有情意,然长辈之意终是未知,又觉可忧,及思自己客居人家,无依无靠,而彼亦是为人养子,疏落在此,又觉可悲,如此悲喜交加,忧惧互生,是以这一对痴男怨女,虽一个在芭蕉摇曳的怡红院,一个在竹影森森的潇湘馆,竟均是辗转反侧,彻夜未眠。
自次日清晨,凤姐处派人来知会落英阁已打扫收拾完了,问几人可搬过去,又依贾母吩咐,给弘历带来了两个丫头,一名紫罗,一名烟罗,乃是贾府新买的一对孪生姐妹,如今十三岁,弘历早觉与宝玉等人同居怡红院多有不便,如今自有宅所,倒也欣然,只是派人去回了凤姐,不要丫头,凤姐再三不肯,又说‘老祖宗吩咐的,怕哥儿丫头不够使,且屋大物多,恐绣儿浣纱或有打理不来之处’等语,弘历见这紫、烟两个丫头面憨性迟,少言寡语,又想既是长辈之意,何必只是处处违拗,倒也罢了。
这落英阁本是与潇湘馆等地同时起建,约有八九间房屋,前厅后舍俱全,三面皆是花树,因到了春暖花开之季,院中莺歌婉转,落英缤纷,故命为落英阁,只是虽有名字,却一直空着,未曾住人,弘历见此处碧围翠绕,鸟语花香,且屋院琴棋武具一应所需俱全,令其玲珑而不流于媚气,雅致而不失于新意,自然喜悦,一时看管着小厮搬了半日,方想起到贾母处来请安,顺便看视黛玉。
彼时贾母处正有黛玉,惜春,探春,宝钗并宝玉,凤姐等人在身旁,凤姐正哄着贾母开心,贾母见他来,因问病得可怎么样了,又问落英阁可好不好,又说‘有什么短缺之处,只管跟凤姐要去’,弘历少不得说都好了,便把落英阁夸赞一回,一并道谢,早有宝玉插话进来:“几时搬的?怎么我不知道?”,众人都笑,凤姐便道:“昨儿你在老祖宗这里吃了酒,今日人家搬的时候,你还睡觉呢。”宝玉便有怅然若失之感。
弘历与人闲话,不时看黛玉形容,黛玉只是不看他,也不与他说话,倒像似昨晚之事从未发生过一般,弘历只得闷闷坐在一旁,蹙眉凝思不语,忽见惜春推他,笑道:“四哥哥,你想什么呢?——大家问你,你只听不见!”弘历恍过神来,忙问何事,惜春抿嘴一笑,道:“才大家谈戏,我和三姐姐正说到《清夜月》这出,都说里头那个红锦不好,二哥哥却不觉得,所以问你呢,谁知你只不理我。”弘历只得略思一回,问道:“可是与柳生青梅竹马,终却又负心抛弃柳生的那个女子?”宝玉便笑道:“罢,罢,何用问他,你们听他这话,也该听出来了!自是和你们一个阵营无疑的了。”探惜二人都笑。
谁知这时,黛玉却悠悠说道:“要我说,还是柳生愚笨,枉他自命为红锦的知音,却根本不解她的苦衷,想她一个大家深闺中的女儿,种种束缚,终又能如何?柳生不解她心,还只误她,又怎叹两人有缘无分?”宝玉见黛玉如此说,自是心中大快,忙拍手对探惜二人说道:“如何,我说不过你们,自有明白人说得过你们罢?”
弘历听她倒似话里有话,心中一怔,便看黛玉,黛玉又去和探春说话去了,贾母从未听过这戏,不解她姐妹们所说,便问何名,座中唯有宝钗不曾加入众人谈论,只在一旁淡笑听着,见贾母问,忙先告诉她,贾母又问内容如何,宝钗便笑道:“这也不是什么有趣的戏文,怨不得老祖宗不知道,不过是讲一对男女璧人本是一同长大,日久生情,终又分开的故事罢了。”贾母听了,便点头道:“我道你们说的那么兴起,原是说的这个,你们女孩家,不比那些男孩子们,终该多看些热闹冶情的戏,这般戏文,只需看个囫囵便也罢了,过后倒还是忘了最好,若日日姐妹们一处,只是论这些个东西,不但移了性情,叫别人听见,出去说嘴,倒叫那起有心的人笑话咱们。”众人听贾母这么说,各自都羞红了脸,忙噤声不谈了,凤姐忙笑道:“老祖宗且别怪她们,与她们不相干,这话头原是我提起来的,我还正想请老祖宗示下,前儿甄府请咱们吃饭看戏,咱们还没有回的,如今这园子现放着那些唱戏的,况四兄弟来咱们府上也有时日,何不就此也搭个戏台子,热热闹闹置办一场,把甄府那些太太媳妇们都请来,也一并让四兄弟跟着乐一日,老祖宗看着如何。”
贾母听了,忙点头笑道:“你说的很是,还是你想得周到,既如此,你就去张罗下帖子去罢。”凤姐忙一迭声答应着下去了。
且说这众人之中,独宝玉最是个喜欢热闹的,听说要搭台唱戏,竟是手舞足蹈,便问弘历爱看何戏,弘历略微一想,因摇头笑道:“你一时问我,我倒难说明白,我从小看的戏原也很多,只是后来很多都只记得大概,名字却全都忘了。”宝玉忙笑道:“现放着许多明白人,何怕你忘,你只管挑你爱看的说来,我们不知道,还有那些唱戏的姑娘们呢,她们定是知道的。”
弘历听他说的‘现放着许多明白人’,心中忽有算计,便笑道:“比如有这一场戏,戏文,曲子色色皆妙,讲的是书生张珙与同时寓居在普救寺的已故相国之女的故事,真真让人荡气回肠,回味无穷,我只记得有个婢女叫红娘的,连那小姐叫什么都忘记了,你们又如何能知道名字。”
宝玉、黛玉等一听,倒都愣住,皆不知他所说何戏,宝钗却在旁说道:“想那小姐是叫崔莺莺罢?”弘历不等她说完,正中下怀,忙拍手笑道:“正是,还是宝妹妹知道的多,可不就叫崔莺莺呢。”
宝玉,探春等都忙问宝钗,宝钗回过神来,忙指着他对众人笑道:“你们这就该罚他!我还以为他说的哪个,原来竟是说的《西厢记》,才老祖宗还说不让看这样的戏文呢,偏他又说与你们。”
别人尚未说话,弘历便先冷笑道:“原来这是《西厢记》,我竟不知道,还是妹妹看过的戏文多,既然如妹妹这般安分守己的人都看得,其他姐妹必定也是看得的了。”
一席话,直说得宝钗脸红心跳,坐立难安,回也不是,不回也不是,只得唯唯说道:“我不过是听闻别人说了一两句,就记住罢了,何曾真的看过那些。”弘历才不过见她装腔弄景,引得贾母说出那些话,让黛玉等人难堪,心中对其厌恶,便想治她一治,因想到‘说人是非者,必是是非人’,深知她所知者必是众姐妹之最,方能道人长短,这才想出此计,此刻待又想挖苦她几句,见她面红耳赤,情难以堪,况当着这么多人,若只一味揪其短处,倒叫别人说他刻薄,便冷哼一声,就此罢了,只是从此对其更加疏远,再难挽回,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