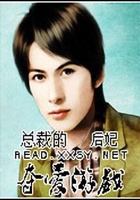黛玉得知弘历为其绝食相抗,便去闻钟阁看他,彼时弘历衣衫单薄,背窗而坐,一动不动,头微微歪斜,凝望另一侧,那里是金粉绣帘的床帏,床上小木栏垂下一绳,绳上系着一只七彩纸鸾,正是其临别时黛玉送的那一只。
风肆无忌惮地从窗子涌进去,哪里都肆虐到了,床帏上的纸鸾在风中摇摇晃晃,飘飘荡荡,仿佛将要断线的风筝,倍显孤单无助,一下一下撞击着床棱。
黛玉只觉这几日不见,仿佛隔了几个春秋,久得令人发颤,再看到弘历,虽只是一个背影,还是温暖亲切,不觉微微一笑,眼泪却也流落下来,方开口叫‘四哥哥’,谁知嗓子是哑的,不过留下了一个轻若无闻的声音,只自己听得见。
谁知弘历却仿佛听到了天外传来的呼唤,近在咫尺,异常熟悉,令其身心一颤。
只是略顿了顿,便猛然回过头来。
黛玉纤手握着木条,笑着叫道:“四哥哥,我来看你。”
弘历一怔,以为是梦,待分明看清就是黛玉,忽然跌跌撞撞从地上起来,动作太急,方一起身,又险些摔倒在地,忙扶着桌子喘息半晌,却望着黛玉一笑,许久,才扶着桌子蹭过来,沙哑着声音叫‘妹妹’,又幽然说道:“看到你真好。”
黛玉闻他此言,泪更是坠如雨滴,见弘历头发微乱,满面颓然,嘴唇如脸色一样苍白,周身神弱气迷,心便如针扎的一般,弘历忙为其拭泪,没有帕子,只得用手,一时动作有些笨笨的,小声笑道:“傻瓜,哭什么,我是做戏,又不是真的。”
黛玉怔怔望其半日,垂下头去,虽强忍不哭,仍是哽咽,越是这极力压抑的凄苦幽咽声,更让人心中揪紧难过。
弘历将大手紧紧覆盖黛玉的手上,连并木条握得紧紧的,脸上孩童般的憨笑,也不知说些什么,不一刻,忽然想起一事,面上生疑,忙问道:“是了,你怎么会来的?谁带你来的?”
黛玉道:“额娘。”
弘历如释重负,点点头,黛玉这方抽泣道:“你吃饭罢。不要再拗圣上。”
弘历微微一笑,道:“他不答应我,我就不会妥协,——实在不行,还有一死呢。”
黛玉又惊又怕,忙道:“不行!”
弘历柔柔一笑,颤颤地伸手,抚摩黛玉缎一般乌发,苦笑道:“若没你,就算佳丽三千,江山万丈,也没半点意义,便是活到千万岁,也是行尸走肉,又有什么趣味。”
黛玉不禁泫然,痴痴望着弘历,弘历也笑看着她,许久,黛玉幽然一笑,哽咽说道:“四哥哥,你要好好的,只有你好了,大家才都好,我还记得你那日对我的承诺,你是大丈夫,不能说了不算,你说会努力习学本事,终有一日,让别人仰望,你说当别人再不能左右你的时候,你会来接我。”
弘历一时凝眸。
黛玉眼中蓄泪,轻声说道:“绝食相抗,永远都是可怜人所为,那不该是四哥哥,我不要你向人低头乞怜,你要站着,要好好的,我还可以等,等到别人对你低头,到那时,你要来接我。”
黛玉声音轻柔细弱,一字一句,却如惊累骇浪一般,震撼着弘历的心胸,弘历反复咂摸思量着黛玉的话,心中渐升光亮,痴痴说一声‘妹妹’,喉咙几起,再无声音。
黛玉自擦干了泪,笑道:“这么多珍馐佳肴,不吃岂不可惜?”便将筷子拿起,送到弘历手中,弘历怔怔地拿着,终于一笑,缓缓端起饭碗,挟菜入口。
黛玉直微笑望了半日,见紫鹃小小在门口叫一声,黛玉只觉不过片刻,其实已经在里面待了近半炷香时候,此时知该去了,不知为何,才压抑的泪意瞬间又出,咬牙强忍,笑说一句
‘四哥哥,我这就走了’。
不等弘历回答,便微笑扭头走出去,临近出门,方听弘历一声‘妹妹’,黛玉如若不闻,略停不停。
方一出门,身子似乎脱了力气,忽然一软,靠在门上,紫鹃忙去搀扶,黛玉面上还笑着,轻说一句‘不碍’,便幽幽对图儿说道:“告诉齐妃娘娘,让她大可放心。”
图儿也不知什么意思,听黛玉直对紫鹃说要家去,一时错愕,笑说道:“姑娘不别娘娘,就这样家去,只怕于礼不合。”
黛玉微微一笑,道:“如今娘娘如愿,便是我失了些许礼数,她也不会计较的了。”便只自顾走,图儿不好不管,少不得先叫人准备马车随从,送其出了宫门方回来复命,齐妃闻言,果然开心,忙向裕妃和圣上邀功去了,不提。
话说黛玉一路坐车回来,脑中翻江倒海,想到齐妃一言一语,虽尖刻刁难,却也句句是实,心中渐渐转悲,因自道:只叹你为何当初只属心与他?岂不知世间多少凄苦,皆是由‘齐大非偶’几字得来?如今人是龙凤,你为草芥,勉自结合,又怎生了局?莫不如今后两相淡忘,倒更好些。
谁知心中虽作此想法,却仍是牵牵念念,反复煎熬纠结,一时也难摹其心。
原来黛玉对弘历所劝,无非是心疼其绝食自虐,不得已而为之,意在使其振作,或能就此有所进益成就,也未可知,与弘历说时,口中信念满满,其实自己心中也难不自问:若两人就此长隔,这期间莺歌燕舞,花团锦簇,便是日后他果真功成,当日承诺,还记得几分?
虽反复告知弘历要坚持至‘不能被人左右的时候’,却也悠悠自问:这样一天,何时可来?
是以一路思绪纷繁,不可或止,始终有两个声音在心底左右相吵,一面令其坚持,一面劝其后退,一面唯情至上,一面以理为格,使黛玉不得片刻安宁,只默默车中暗伤。
行至半途,见亲王府又派了车马,福晋亲自来接,黛玉才略收了悲,福晋询问,黛玉也不过说齐妃‘邀请赏梅’罢了,福晋见黛玉眼睛桃儿一般,便知其哭过了,一时心中疑窦丛生,又觉有气,便定心要哪日宫中去一回,且先不言。
因宫中一去,黛玉心中自此便藏一股忧郁,每日神情寡淡,落落不言,又不能对外人说其心事,便见消瘦,福晋见黛玉较之从前更弱,自是不让回去,黛玉遂于亲王府住下,每日与湘儿一处伴着耍玩,或和福晋说话解闷,亲王知其爱看书,便特许黛玉自由出入自己书房,如此每日,倒也宁静祥和。
此时弘昑并不在家,因于半年前应亲王之荐,拜访那位昔日为官,今朝退隐的三朝老臣,一时聊了三日三夜,浑然忘倦,只觉其胸中似容纳百川,藏有宇宙,大为震动,便一心下志要拜其为老师,同其学习天地之阴阳理数,以及为人之德,为臣之道。
此一去消息鲜有,别人倒也罢了,因湘儿自小就在弘昑屁股后打转,这一次长别,自是大不自在,原听说要去三年,未过一年,便熬不住,每日催促亲王将弘昑接回,亲王自然不听,湘儿无法,知弘昑对黛玉不同别人,便背着众人,偷偷以黛玉的名义书信一封,放于小鸟腿上,使其给弘昑捎去,便家中每日等着,也不知如何。
且先不说她,因亲王府距皇宫不远,况亲王常宫中游走,自是得知许多消息,黛玉听闻弘历已敛性沉心,凡事谨随圣意,每日请安问好,谦恭守时,闲时用功刻苦,体上恤下,大得人缘,文武百官无不称颂,心中且喜且叹,稍觉安慰。
圣上本有立其为太子之心,只是中间多一‘绝食’一事,未免耿介,这时见其已回心转意,况众声也齐向弘历,兼弘历品学才思,远非其他阿哥能比,那点往事也不过当做小孩子家的一时冲动罢了。
此时的圣上已经人到暮年,国事繁忙,渐觉力气不支,心中难免不多想一些,便每每使弘历随身学习,如何处理朝中繁琐之事,如何应对朝外大小状况,弘历日渐得知‘读书万卷,不如躬身亲试’一句之意,也至此时,方知为君之不易,——非君王管制天下,而是天下管制君王耳!便将昔日狂傲跋扈的性子逐渐褪去,一年之间,已见沉敛成熟了许多,对圣上则更多了几分体贴之意,每临其身子不好时,便亲为其煎水熬药,以示孝道,圣上虽不多言,心中对其更喜。
这日乃是元年八月,值早朝时,圣上与文武百官之前宣已‘密书一封’,并说上有‘他日掌印之人’,因说道:“因前朝有两废两立之事,便不欲将太子公布天下,且先暂定,其后观之,若得以重用,自有人代为宣告,若有不妥当之处,也可再改之。”此言一出,朝中不免小小纷乱,很快又归于平静,密令太子为谁,似乎大家早已经心照不宣了。
只是圣上之心究竟何意,无人能够揣度,便是弘历,因那一句‘若有不妥当之处,可再改之’,不免小小忧心,不知圣上意思为何。
话说自那日与黛玉相别,弘历再未谋其面,一切两人消息物件,都不过是通过湘儿暗中转送转达,弘历每每安慰鼓励黛玉,以坚其心,虽如此,还是对其想念日深,这日是二月十二,乃是黛玉生日,弘历一早请示去亲王府‘拜见十三叔’,可巧宫中接待西域藩王,圣上便不准,弘历无奈,只得将给黛玉的礼物悄悄托付了一个小太监,命其拿自己的腰牌出门,交给黛玉贺岁。
亲王府那边今日也是有意要为黛玉庆生,连亲王都将许多冗事推脱了,福晋更是吩咐厨房‘好生做一桌的饭菜’,弘晓先弘皎回来,已住了几日,这日早晨齐至黛玉房中,彼时紫鹃,念红正给黛玉梳头,黛玉这日心情也好,尚跟着湘儿等人说笑打趣,忽听人说:“六贝勒回来了。”
众人一怔,湘儿忙先笑道:“可回来了,想死我了。”便抢先跑出去,黛玉,弘晓等人也都出门去看。
此时弘昑方进院不久,尚未拜见亲王,福晋等人,正命小子们放好东西,只见其一身浅青色金袖短褂,藏青长裤,浅色高底长靴,个子较之去年又高了一截,头发高竖,面容皎白,褪了几分昔日的青涩羞赧之气,眉眼间多了几分凌厉坚定,举手投足间豪爽随性,已有大丈夫之风,喜得湘儿先冲上前去,一下跳上弘昑的身子,弘昑便背着她旋风般转了几圈,放下了时,不禁笑道:“十四五的大姑娘了,怎么还这样顽皮,看明儿嫁不出去。”
湘儿笑道:“嫁不出去才好,跟六哥混一辈子。”
弘昑抿嘴一笑,道:“你要跟我混,也得我愿意才好。”
忽抬眼见黛玉走来,便柔柔一笑,露出一排洁白贝齿,笑道:“姐姐也在。”
黛玉莞尔一笑,道:“不是说要去三年的,怎么一年多就回来了?”
弘昑脸色微微一红,道:“师傅让的。”黛玉便微笑点头。
弘昑见黛玉一年之间,越发出落得婀娜飘逸了,只是清瘦了许多,眉眼间似多添了几分愁绪,喉间一动,便冲口想问‘这一年可好’的话,见许多人都在,却又咽了回去,也只微笑点头。
那边湘儿听了弘昑的话,又看其形容举止,不禁噗嗤一笑,刮脸道:“还撒谎呢,不知羞。”
弘昑便道:“撒什么谎?”
湘儿便摇头晃脑,笑道:“若不是我以姐姐名义飞鸟传书,你怎么会回来这么快?”
弘昑瞪目说道:“什么飞鸟传书?我怎么不知道。”
湘儿见他不像说谎,忙道:“怎么会不知道?我一月前把信件系到飞鸟上的,让它跟你传信回来,你这不就回来了?”
弘昑一听,便‘哎’的一声,笑说道:“你这丫头,怎么行事还这么鲁莽,我那边离这里多远,你又没训练过它,就那样巴巴的放出了,天地这么大,它上哪找我去?”
湘儿忙道:“你既没收信,怎么这么巧,就回来了?”
弘昑脱口说道:“那是因为我记得姐姐生日,想家里一定会把她接来过,才回来了,什么鸟儿,我连影儿都没见到。”话方说完,想起方才还和黛玉说是‘师傅让回来的’,这会儿自相矛盾,顿觉尴尬,忙又说一句:“你也不必挂念了,那鸟儿只认得潇湘馆,此刻八成是在林府呢。”
一语说完,想起‘只认得潇湘馆’一句,又觉不妥,本是要掩饰方才一语,不想倒更尴尬了,便将俊脸浮上一抹嫣红,可巧亲王处来叫弘昑去,弘昑便借机辞了黛玉等人,说‘一会儿额娘处见’,忙整衣去见亲王,黛玉这边见他去了,便也和湘儿等上福晋处说话。
亲王叫弘昑也无别事,不过问其原因,也借此机会考验他这一年所学罢了,见弘昑思绪广阔,大不似从前,对答如流,可见胸中见识多了不少,也很是喜欢,便笑道:“虽有小成,不可骄傲,你二哥那边也是名师,且看你俩到时谁更胜一筹罢了。”
弘昑忙笑着答应,见亲王喜欢,犹豫了犹豫,便趁机问弘历‘现今如何’。
亲王若有所思,想了想,说道:“现跟圣上每日处理国事,圣上已经密令储君人选,估计是他。”便悠悠啜一口茶。
弘昑秀眉一皱,思索‘密令’二字,问道:“圣上可是因前朝两立两废一事,所以密令?”
亲王微微一笑,道:“对大家是这么说的,——其实是不放心你四哥。”
弘昑忙问:“这是为何?”
亲王稍有犹豫,似乎是在考虑当不当说,半晌,还是悠悠叹息一声,说道:“圣上确是一心想立你四哥为太子,只是尚不知他是否全心为政,不耽情事,意欲观察他罢了。”
弘昑细细想了想亲王的话,心中生疑,便静静问道:“阿玛,圣上是不是公然反对了林姐姐和四哥哥一处?林姐姐是不是一年没和四哥哥见面了?”
亲王不语,只闭上眼睛,许久,方说道:“你先去罢,我歇一歇。”声音听去有些疲惫,似叹幽幽。
弘昑只得悄然退出,心中却如灌了铅一般,渐渐沉重,一时独自在抄手长廊迎风站了许久,脑中纷繁错乱,思绪万千,忽见福晋处一小丫头来找,这方想起还没有到福晋处见面,忙将乱麻一般的心绪暂且收敛,一径到福晋处来。
彼时上房异常热闹,福晋见弘昑来了,忙叫丫头拿个杌子来,使其身边坐着,细细问了弘昑一回冷暖,弘昑恭谨答了,话语不多,福晋只道其远途累了,便让吩咐厨房早些开饭,这边和其他人说笑一回,便见一个小丫头来说:“宫里来人了,说给林姑娘送礼物的。”
黛玉心中一惊,见其手中捧着一个粉红色的小锦盒,上面小心系着一个玉带蝴蝶,忙起身拿过来了,也不多问,只叫紫鹃拿银子打赏,紫鹃忙笑着去了。
且不说这边见了礼物,各自如何,单说门外小太监为弘历送礼物前,已得了弘历几两银子,这会儿又得了赏赐,自是欢喜,一径回来宫中,未进中门,便见一个小公公早歪在墙边等着了,见他回来,微微一笑,只说‘圣上等着问话’呢,便径直将其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