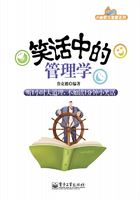话说亲王府因惦念黛玉,此日特派红珠与几个老婆子来接黛玉,正待要走,却见另一伙车马来,也是要找黛玉。
门上人见来人打扮不俗,气势凛然,显然不是一般人,一时有些发愣,红珠因有福晋嘱托在先,路上万事都要关护黛玉,且又比她年纪大,见其问起,便先悠悠然上前,看她笑道:
“你找林姑娘可有事?”
那丫头上下看了红珠一眼,又看了看身后轿子,小厮,这方说道:
“我来接林姑娘进宫的。”
此语一出,众皆讶然,念红忙对黛玉道:“真来接姑娘了。”黛玉心中便登时突突乱跳起来,亦疑亦喜。
念红声音虽不大,还是让丫头听了,不由得看黛玉,见入目一个十五六岁姑娘,如画里走出来的一般,周身仙风仙气,貌美倾城,先暗暗叹了一番,待开口问明,果真是黛玉,这方笑道:
“你既是林姑娘,就跟图儿宫里去罢。”另一边自有人掀起轿帘子,叫图儿的丫头便上前来搀扶黛玉,口中说‘请罢’,红珠忙道:
“且等等,我们是亲王府来的,福晋亲自吩咐要将姑娘接去,这会儿被你们接走了,福晋岂不说我的?况我如何得知你们是不是宫里的人?若出了差错,可不是小事,好歹姑娘是亲王府的干格格,咱们可不能就这样让去了的。”
图儿听说是亲王府的,态度稍稍好了些,却也所让不多,吩咐身边人将进出腰牌拿出来,在红珠眼前晃了晃,笑说道:
“姐姐看仔细了,这也能是假冒的吗?我只知道应命接林姑娘进宫,其他的也理会不得,若有得罪福晋,唐突了姑娘之处,自有人赔罪,不干我事。”便请黛玉上轿。
这边黛玉微微生疑,因思:若是弘历叫来接的,该是让绣儿,浣纱来才是,怎么巴巴派来一个外人,况这趾高气昂的模样,也不像伺候他的。
虽纳闷疑惑,只因弘历宫中,若进了宫,自是有机会见他,也觉喜欢,见红珠又要和图儿缠论,恐两下相僵,便道:
“她们既有牌子,想必并没扯谎,我就同她们走一遭就完了,姐姐只回去回了额娘阿玛,免得他们担忧。”遂命紫鹃跟着。
红珠听黛玉此言,方才罢了,却也不敢另路回家,且跟在众人身后,一路亲见将黛玉送至皇宫,才回亲王府告诉,不提。
话说图儿原是齐妃处的丫头,受了齐妃所命,方来接黛玉进宫,也并不知原因为何,连并行止,态度等,也是齐妃特特吩咐了如此,她才刻意照办的,黛玉听闻齐妃找她进宫,心中自觉有些古怪,却也不多言语,一路两相宁静,只是途中不少小丫头驻足凝望黛玉,悄然望其议论不止,黛玉只默然跟于图儿身后,直至齐妃处,并无别话。
此次齐妃似乎和上次判若两人,见黛玉来拜,也不过用鼻子‘嗯’了一声,让坐一边,叫左右下去,黛玉方坐了,齐妃笑道:
“一年不见,玉儿越发出落得飘逸超尘了,连我看见玉儿的模样,都忍不住心疼呢,别说他人。”
黛玉闻声度意,微微警觉,小声说道:
“玉儿凡姿俗貌,娘娘笑话了。”
齐妃想了想,笑道:“可还记得我上次引你游逛时,同你说的那些话?”
黛玉凝眸一怔,想起长廊细语,许多旧妃之事,睫毛微簇,复又垂下,道:“记得。”
齐妃便笑道:“许多话,我并没有明说,我以为你是个玲珑剔透的,必然明白,所以不过点一点你罢了,现在看来,莫不如当初直接对你说明了,倒更好些。”虽笑着,语气却有些生硬,凝望黛玉不语。
黛玉心中大疑,因思及上次齐妃暗中之意,无非是叫其离弘历远些罢了,现在两人已是远远隔着,两难相见,该遂了心意才是,又巴巴地把她叫来说上这些话做什么?
见齐妃语气生硬,不知为何,心中忽生起一丝倔强之意,一时蹙眉,声音虽幽然娇柔,却有一股自尊自矜之气,说道:
“当初裕妃娘娘叫娘娘领我逛逛这宫里,我便当了真,实在不知道娘娘醉翁之意不在酒,若没体会到娘娘意思,还望恕玉儿迟钝之罪罢。”
齐妃本当黛玉怯怯弱弱,行事多思多虑之人,经她提示,心中必然退缩千里,岂知其颜容却忽然变了,和所想大不相同,一时痴怔,‘你’了一句,也不知说什么好,脸色便有些红了,索性单刀直入,冷笑道:
“你真明白也好,不明白也罢,想必现今你也知道,弘历乃是当朝四阿哥,非一般人,你打算怎么办?且说来我听听!”
黛玉便明白了,依旧垂目敛容,说道:
“玉儿一女子,能力卑微,又能如何?唯有一切听任天命,顺其自然罢了。”
齐妃见黛玉不卑不亢,毫无畏惧退缩之意,兼话已至此,若再不明说,自己也没甚言辞,也少不得定了定神,说道:
“你好歹是亲王府认的干女儿,这些话,我本碍着亲王,福晋面子,不想说与你,谁知你这般愚钝,也怪不得我言语伤人了,我知你面上虽柔弱,内里却是个有算计的,这原也难怪,你父母双亡,贾家又趋于败落,你自是想寻一个好靠山,好为自己将来筹谋打算,只是你这算盘也拨的太离谱了些,历儿乃是当朝阿哥,正宗的皇室血统,何样门第人家的姑娘配得上他,我不多说,想你心里也有数,当初不知道时也就罢了,后来知道了,怎么还不收敛些?”
遂又冷笑道:“——我竟不知你使了什么勾魂摄魄术,用了什么伎俩,竟叫历儿铁心就要你一个,历儿在皇子里是个出众的,若我看他,将来不但能册封太子,还极可能隆登大宝,成九五之尊,你这样出身,别说皇后,妃嫔了,便是一个贵人,答应,也要几重关卡才可定能否通过呢,难道为你一个,后宫绝人了不成?我今儿话重了些,却也是实话,我自知这话得罪了福晋,哪日我自会邀姐姐来,好好和她赔个礼,你若是明白人,这些话,就请细想。”说完,且看黛玉反应。
这一席话,将黛玉说得脑筋嗡嗡作响,心中又惊又怒又悲,又觉羞臊,不由得将俏脸涨得殷红,自觉为此生以来最不堪一刻,心底却也因这大震莫名愤然,渐渐浓郁,眼泪虽在眼眶中漾动,却强忍不令其坠出,一时悠然站起身来,玉牙暗咬,纤手微颤,一字一句,含笑说道:
“玉儿出自凡家,生性简愚,自长这么大,见过的人有限,经历的事有限,每日或与花草相伴,或姐妹们一处经营琴棋针线等事,从来没想过许多,娘娘乃大风大浪过来的人,心思细密,卓越不群,胸中自有大慧,方有今日这些话,真真是让玉儿受教了!”
齐妃听了,顿时一噎,面色便有些难看。
方要说话,黛玉又笑道:“娘娘埋怨玉儿拙笨,上次没有理会得娘娘意思,玉儿自唯有赔罪的份儿,只是说我为找好靠山,别有用心,却真真冤枉我了,四阿哥到贾府上,以的是王爷义子的身份,想必连娘娘都不知道贾府中‘紫历’的身份,我又焉能知道?既不知道,又哪来的那些‘离谱的算盘’?此一则,二则,玉儿承蒙福晋抬爱,认作女儿,自此便和四阿哥成了一家兄妹,难道兄妹之间,还要处处远着不成?至四阿哥身份解开,也是后来的事,自宫中将四阿哥接回,玉儿一直未曾与其谋面,娘娘今番突然把玉儿找来,数落一番,又是‘勾魂摄魄术’,又是‘伎俩’,我竟不知何故。”
齐妃一时语结,讶然看了黛玉半日,想了想,态度稍稍缓和下来,笑道:
“我是一时没主意了,才有些慌不择言,既是我冤枉了你,也好,你只先从此发誓再不与历儿纠缠,我就放心了。”
黛玉不由得脸红,一时蹙起柳眉,说道:“玉儿是一女子,左右不得自己命运,所以才有‘顺其自然,听天由命’一话,退一步说,纵是玉儿和四阿哥有何牵扯,操心者该是圣上和我阿玛,额娘才是,娘娘为何执意要越俎代庖?——是瞧不起我阿玛,额娘,还是瞧不起圣上?”
齐妃大怒,脸上立时变色,立眉说道:“你好大胆子,便是你额娘,也要敬我三分,你跟我这样说话。”
黛玉也不知自己何以这般凌厉,自觉一句一言,一容一行,皆是由衷发出,极为自然,毫无半点瞻前顾后之思,如今已知未必能和弘历见上,且兼齐妃恼了,方低头敛容,说道:
“玉儿不会说话,得罪娘娘了,今日本是额娘思念来接,谁知中道被娘娘叫了这里来训斥,出来得久了,恐额娘惦记,若娘娘责怪完了,还乞放回家去。”
齐妃见黛玉要去,脸色微微一变,原来此责任乃是裕妃所担,裕妃嫌自己口拙,遂交与她,今日一切,皆是齐妃自己筹谋安排,她见黛玉乃是一多愁多病之身,凡事多虑多忧,便意欲先严词一番,让其自惭形秽,知前意皆是妄想,定下远离弘历之心,她好行此后之事,谁知其自以为天衣无缝,却经却全然不如所想,黛玉话语虽柔,却是柔中有刚,一句一行,毫不妥协,一言一止,尽出人意表,竟让她心中微微生寒,心底自相告诉:这不是木婉纯,也未必就是第二个吉嫔,——或许真错想低看了她。
此刻戏已近尾,黛玉身后毕竟是亲王府,其立意要走,自己又不能硬留,更不能把她怎样,因生一思:今日若不事成,岂不负了圣上,裕妃姐姐所托?心底便有些慌了,遂有些后悔初时刁蛮言行,只是齐妃久居宫中,变脸也快,一旦想通,忙堆上满脸的笑,一时下来,走至黛玉身边,携着她手,扶其扶至主座,黛玉再四不肯,无论齐妃如何相让,其还是只自己找了个边上的位置,齐妃方一坐下,便笑道:
“玉儿别气,我方才也是一时心急意乱,说话不择方式,略重了些,你且看我与你额娘素日还算有交,别和我计较才好。”
黛玉见状,只得垂头别首,淡淡说道:“玉儿地位卑下,娘娘这话言重了,我禁不起。”
齐妃便看了黛玉半晌,长叹一声,竟忽然把眼泪流下来,说道:
“这里只你我二人,说话也不必太多避讳,四阿哥属心于你,我不是傻子,自然看得出来,——若不然,他又怎能因你一人,将满皇宫都惊动了,甘愿与圣上相拗,以死威胁?”
黛玉一听‘与圣上相拗,以死威胁’几字,顿时如当头击了一棒,只觉脑中嗡响,心头乱跳,便怔怔看着齐妃,问道:“以死相胁?”
齐妃幽幽轻叹,说道:
“妹妹有所不知,历儿自回来之后,圣上特将所有阿哥集结一起,查验各人功课本事,其中数历儿最为出色,圣上龙心大悦,说要大赏,历儿便趁此机,和圣上说了你二人之事,说‘不要赏赐,只求圣上下旨,立玉儿为福晋’,圣上不肯,历儿便整日在圣上面前苦求,好话说尽,圣上却仍不为之动容,历儿便动了左性,放话说,此一生只娶你一个,并威胁圣上,‘若不答应,甘愿绝食自尽’!”
黛玉只呆呆的,一声不出,目光痴凝。
齐妃又道:“圣上听他只娶一妻,本就生恼,更兼他以绝食威胁,越发大怒,一时愤然,命人将他关押在西头闻钟阁,不准出阁楼半步,就在几天前,圣上还在文武百官面前对历儿大加褒奖,转眼变脸,便将其关押起来,勒令严加看视,朝中上下自是大为震动,纷纷议论,直至今日,已过三天,这三天来,历儿水米未进,便是钢铁之身,只怕也难撑多久了。”便用帕子拭泪。
黛玉只觉身子发飘发软,眼前人事渐渐模糊,满脑噪乱,忽然只是不断重复的一句‘三天水米未进,只怕难撑多久了’便不由自主站起了身。
忽幽幽说道:“闻钟阁在哪儿?”声音漂浮不定,有若梦呓。
齐妃眼睛一亮,随即又假装黯然下去,说道:
“玉儿若去,打算说什么?”
黛玉何曾知道要说什么,只是心中如有人催,要马上见了弘历才好,听齐妃此问,自己也不知如何,便悠悠看她,齐妃遂低声问道:
“让他坚持绝食下去,和圣上对抗?还是让他暂且妥协,再想其他好办法?”
黛玉更是痴痴落落,一语难发。
齐妃见事有可为,便说道:
“我知道玉儿出自书香之家,自小深明大义,是个极懂事的,你且细想,历儿如今乃阿哥之尊,以他品学才能,将来极有可能是太子,前途可谓难以限量,如今却因你如此开罪圣上,甚至于绝食相威胁,若其真有闪失,你一女子,如何担得起这罪名?便是退几步说,圣上果真妥协,册封了你,也最多不过是一侧福晋,历儿身为皇子,还将有许多妻妾,你见过哪个阿哥只有一个福晋的?”
又道:“你们只求一生一世一双人,奈何与皇家礼法相悖,那时你又当怎样?——左右看来,你二人一处,不是幸事,只是祸害,与其到最后弄得各人皆伤,不如及早放手,才更好些,你细细想想,我这些言语,可有道理?”便看着黛玉,见其神色凄然,大为动容,知时机已到,这方顿了一顿,柔柔小声说道:
“历儿现在是人难劝,唯有你能劝得动她,我这才将你请来,好玉儿,你该明白我的苦心,我不只是帮他,也是想帮你呢,你是亲王府格格,还怕将来没了好归宿不成?何必只纠结历儿一人身上?”
黛玉似乎没有听到齐妃的话,心中初时翻江倒海,又渐渐归于平静,只是鼻子渐渐发酸,泪意肆虐,止都止不住,一时屋中静极,仿佛过了几世之久,方听其哽咽说道:
“娘娘的意思,玉儿明白了,四阿哥现在何处?”
齐妃心中舒了一口气,硬的不行,软的终究管用了,一时忙叫图儿。
一时丫头来了,齐妃便笑道:“把林姑娘带到闻钟阁去,守卫若问,就说裕妃娘娘让的。”
图儿忙答应着,这边引着黛玉出去,紫鹃见黛玉出来,忙跟着。
短短一程,如有千里,黛玉脚若踏棉,身子似不是自己的,一时直走到西头,见几棵参天枯树下罩着一个独落小院,紫朱漆的半圆门,高高围墙,内里森然寂静,门口几个守卫在有些寒冷的风中微微瑟缩,图儿和其悄然细语几句,守卫便点头,一人回身铿然开锁,只放黛玉一人进去。
里面的门锁着,只一扇窗子大开,寒风汹汹涌进屋子中去,使得温暖的阁楼冷如监牢,窗上被横着钉了几个粗木板,间隔只有大半掌,勉强塞得进盘碗,窗下一张青木百花桌子,桌上许多珍馐佳肴,细白米饭,满满一桌,一筷未动。
弘历背对着窗,坐在冰冷墙壁上,身上只穿一件单薄的白夹衫,风涌进来,吹得白衫簌簌飘动,弘历只环抱着膝,头靠板壁,默然不动,恍若一座石化了的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