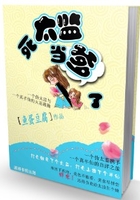凤姐来交权,将一切琐碎事宜都还给黛玉管理,解释许多,弘历初一听凤姐之言,立时便知她的意思了,且不言语,只看黛玉如何。
黛玉向来清高,甚不喜欢被这些俗物缠身,当即忙笑道:“好嫂子,你且饶了我罢,若谈诗论画,我还支持得一时半刻,若说理家,我可是一万个不行的,回头把府里上下还弄乱了呢。”便不肯。
凤姐笑道:“谁一开始就知道轻重的?我开始时候也乱呢,后来慢慢熟了,也就好了,再说妹妹有什么不懂,我多告诉你些就完了,妹妹向来是个聪明剔透的,若不是素日身子不好,还轮得到我在那儿丢乖露丑的?如今可推脱不得了罢?”
黛玉还是谦让不受,弘历这方说道:“既二嫂子身子不好,你又何苦只拗她?况且如今你是这府上主人,你不管谁管?若我看来,就应了也罢了。”便看黛玉。
黛玉见弘历也这样说,又直看她,不好再怎样,凤姐本是来卖个乖,她也知黛玉不爱理会这些琐事,此次定然推脱,她此后管家,于众人面前也理直气壮些,谁知竟应了,也没奈何,只得忙叫身边小红将身上钥匙都交出来,挨个说与黛玉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的,那个是做什么的,如数家珍,又似蹦豆一般,说完,笑道:“我说得快了,姑娘若没记住,我再说一遍。”
黛玉笑道:“差不多了。”便也依样说一回,竟半点不差,惊得小红和凤姐二人直愣。
一时又说一回闲话,凤姐又笑道:“此是一事,还有一事,须得请求你们两个。”
黛玉因问,凤姐笑道:“大姐儿到现在还没有个像样名字呢,我想了几个,终归俗气,想到你二人是个有墨水的,今番特来求你二人商量给起一个名字,好歹以后有个叫的。”
弘历便摇手笑道:“男孩子倒罢了,若女孩子,还是别找我,让她起罢。”
黛玉笑道:“这倒不是难事。”
遂歪头想了半日,忽笑道:“就叫‘篱娇’也罢了。”
弘历便问有何寓意,黛玉笑道:“我最讨厌名字非有意义不取,冬日生的,就离不开‘雪,梅’等字,春日生的,都要叫得与春有关,连并桃,杏,紫,红的,真真俗死了,我也没多想,也不过是心头忽然现出一句词来,就截了两字罢了。”
弘历笑道:“你取名就取名,何必稍上别人?——‘篱娇’二字,又出自何词,怎么我不知道?”
黛玉先时听他说‘何必捎上别人’,方想到‘紫,红’二字,将他和小红二人都稍上了,一时脸红,忙笑道:“我口快了,也不过举个例子罢了。”
见弘历问出处,便忙笑道:“连这两字出处都不知道,明儿连赵钱孙里都忘了呢,‘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是哪个的词,你自己想去!”
弘历这方一拍额头,笑道:“真真是我迟钝了,连大文豪都忘了,只是你也截得忒古怪些,难怪我一时想不起来。”
黛玉忙笑道:“这话奇了,难道截字也要守何章法不成?”
凤姐那边笑道:“我也不知道什么文豪不文豪的,这名字听来很好,以后就叫这个罢。”遂逗引大姐儿叫自己名字,大姐儿咬舌头,只不断叫‘篱妖’,弄得大家都笑。
待凤姐告辞去了,弘历方看着黛玉抿嘴一笑。
黛玉会意,笑道:“我虽知道她是做戏来,只奇怪一则,既是做戏,为何不早来,这许多个月都过去了,才巴巴想到交权来?”
弘历笑道:“你不知这内里缘由,必是她放钱出去,有一年,半年,几月还款的,若早交权,人家还钱来,岂不露馅?这会儿都暗中还齐了,她才来弄这一出戏。”
黛玉点点头,淡淡笑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话是有的。”
弘历冷笑道:“还不是掐准了你是个清高人,不计较?换了一个,也未必由她,这会儿交权了,财政大任都落你肩上,她再想有何手脚,可也不容易了。”
黛玉忙嘘一声,又摇手,原来凤姐虽去了,篱娇还在,此刻正窝在黛玉怀里弄九连环,这会儿见弘历声音大了,便看他说话,黛玉不想让篱娇听去什么褒贬,是以作势让弘历止口,便哄逗篱娇玩儿,笑语软软,慈目柔柔,又伸出纤纤玉手为其整理衣服领子,宛然就是一副慈母模样,看得弘历痴痴的,心思早不知飞到何处去了。
且说如今贾府大权落于黛玉身上,黛玉自是少了许多清闲,府中虽大多是女眷,没了许多外头繁冗之事,琐碎还是许多。
是以每日睁眼起,便有许多人回事,檐柱斑驳了,小桥断了一块,家养的鹿生病,时令将过,是否要给姑娘们做衣服,谁要请假,谁要支银子,新到果苗谁管,派谁去采办,且新年将至,或有姐妹生日等等,大事小情无数。
黛玉虽柔弱不禁,却不肯让人笑话了去,为减疏漏,便早和平儿细细询问,商议办法,初时生些,过了一段日子,便也渐渐好了,黛玉又不比别人,纵理家事多,并不肯让自己全然埋没其中,每日与人读书,下棋,或一时闲来下棋,赏景作诗,用其话说:
‘俗事终究是俗事,便是多么重要,也全然可‘举重若轻’,若被它拘住了,便不是‘我理家’,倒成‘家理我’了,岂不没趣儿?’遂雅兴照旧,说笑如初,每日却也能将所有杂事处理妥帖,而其干练精细之处,竟半点不比凤姐差了,众人无不称赞。
那弘历初时极力怂恿黛玉理家,固然有不放心凤姐之处,然主要还是因为平日早察觉黛玉之能,正好借助此机,试探一番,果见黛玉不悖所想,心中因思:
‘由一叶可知秋,虽是小小一府,倒也能见其胸中沟壑几何了’,心中竟莫名兴奋,也不知何因,如今既已知黛玉之能,见其每日操劳辛苦,心中又不忍,方过了一月,便无论如何不肯再让她管事了,极力推荐探春,黛玉也觉疲累,便就听弘历所荐,将林府内外事宜复又托与探春管理,不提。
此后每日悠然安静,姐妹间相处温馨和谐,并无甚事可记,转眼大年将至,亲王府本要将黛玉,弘历二人都接去过年,可亲王因思节日之时,家中必少不得招待许多前来讨好卖乖的官员,若弘历家中,只怕多有不便,遂暂且不让他来。
黛玉虽想念亲王府众人,只是弘历不去,她如何肯去?便也以与姐妹们一处伴着为由相辞,湘儿已在林府玩了许多日子,每日和探春,惜春,黛玉等人相伴,又有宝玉身前身后陪着,自觉比在家要好得多了,一时乐不思蜀,便说‘要这边陪着林姐姐’,也不回去,福晋便也由得她。
虽如今林府上上下下仍有上百人众,只是较之从前还显冷清许多,黛玉并不愿多管,便将一切都丢给探春,凤姐等人操办,尽管及不上从前每次,倒也还算热闹,余者也无需多述。
这日大年初四,李纨自掏钱做东,请弘历,黛玉及园中众姐妹饮酒,席间行令拈阄,罚酒作诗,一时间觥筹交错,倒也热闹,至散时,各自都有了几分酒意,因湘儿第二日便要回府,这日便多喝了几杯,晚间入睡时分,早分不清东南西北,丫头给铺好了被褥,她见黛玉看书不睡,自己便也不睡,见屋中只黛玉和她二人,便将头倚靠在黛玉身上,笑道:“心头跳得很,姐姐。”
黛玉微微一笑,翻一页书,说道:“睡着去,一会儿就好了。”
湘儿不去,仍旧黛玉肩头躺着,过一会儿,说道:“姐姐,你会在这府里住一辈子吗?”
黛玉心头一动,笑道:“怎么忽然问起这话来?住一辈子如何,不住一辈子又如何。”
湘儿便道:“我只是想着,若姐姐不在这府里住了,这府自是要散伙的,那些姐妹们怎么办?——她们什么时候嫁人?”
黛玉推她一把,笑道:“快快那边睡着去吧,跑到这儿瞎担什么心?”口中说着,却果真因湘儿的话怔住,只望着字里行间,眼神痴凝,一时也思绪不止。
湘儿痴痴笑一回,复又回来,又靠着黛玉道:“姐姐说宝玉哥哥可好笑不好笑,父母皆不在了,每日倒高兴许多,若有人说他,他就说‘有失必有得,虽父母去矣,然得和姐妹们一处守着,一处说,一处笑,一处顽,再无挂念和约束,倒也不失为好事一件。’怪道人说他是个呆子呢。”
黛玉不言。
湘儿忽又说道:“宝玉哥哥没了父母,谁给他的婚姻大事作主呢?可是姐姐?”
黛玉听湘儿作此言语,心中便纳闷疑惑,幽幽笑道:“哪有妹妹给哥哥做主婚事的?长嫂如母,自是大嫂子了。”
湘儿口中便重复着‘大嫂子’几个字,便点点头,乜斜着眼,说道:“不然就让圣上伯伯下一道旨,让宝玉哥哥永远不许娶妻,只当我小厮,每日身前身后伺候着我,也罢了。”
黛玉便觉好笑,心中又有些狐疑,见湘儿眼睛渐渐沉了,显是困倦,便不再多说,只将其扶于被中,给盖了个严实,自己又想了一会儿心事,方也睡了。
次日将湘儿送走,果见宝玉痴痴送至门外,湘儿也似有依依不舍之状,两厢都并无多少言语,黛玉见湘儿去了,方将自己心头所疑告知弘历,弘历一直倒并没太在意,听黛玉说起,不禁惊诧,忙道:“不行!若是这样,以后再不叫湘儿来了,他一个纨绔子弟,从小叫人酿坏了的,半点钢骨都没有,湘儿乃是一个正牌格格,岂能屈尊下顾,和他有什么牵扯?纵阿玛,额娘同意,我也是一万个不同意。”
黛玉又好气又好笑,又有些脸红,便道:“我又并没说她二人怎样,也不过是转述湘儿的话罢了,你又抽什么风?别说湘儿和二哥哥未必这么想的,便是真两情相悦,你又管得了什么?你再大,须大不过人的父母去。”
弘历便说道:“我不是非执意要阻止她二人,只是。”话说到此,忽然顿住,弘历本想说‘只是实在不相信宝玉干净’,又恐黛玉听了刺耳,继而恼他,便改话道:“只是湘儿单纯,宝玉又最喜在女儿丛中厮混,阿玛定然不喜欢这样人的。”
黛玉便一时沉默不言,自此也便不提这事了,那边弘历却当此甚为重要,恐湘儿深陷,到时候不好收场,便暗中偷偷告知弘昑此事,使其看住湘儿,不令她再来,谁知湘儿倒果真再没来过,也不知是弘昑功劳,还是另有他因。
自此林府各自相安,弘历仍旧苦学勤思,待将亲王所推荐论著遍读弄通,一年疏忽已逝,秋去冬来,转眼冬日又将行远,日子只如流水,一旦逝去,再不回头。
遍府上下,除了弘历,便只黛玉知道三年之约。是以日子每临近一日,便没来由地惶恐一分,劝慰似乎再没有用,恐惧宛如三月痴长的草,一日日的水漫船高,弘历一切都还照旧,连浣纱都开始疑惑,每每与绣儿生语:“林姑娘近日可有些古怪,早起便来,四爷看书,她便旁边守着,一语不发,许久才走,也不知何故。”饶是浣纱聪明,也不能猜透黛玉心思。
此刻黛玉心中乱麻一般,自己尚理不得,旁人又焉能明白?犹记上次也是如此依依不舍,毫没来由,未过几日,弘历便引兵边疆,只留她深闺熬守,每每也会自相疑惑:莫非此次亦为预见?
只可叹浣纱尚有一疑半语,弘历却半丝感觉不到黛玉的心事。
这日下了一日小雨,黛玉一日足不出户,话也不说,只独自一能够人窗前郁郁坐着,心中说不清是喜是悲,是哀是怜,弘历一日外出有事,至晚间方回,彼时雨也停了,渐渐云散月出,便听小丫头来潇湘馆告诉,黛玉方悠悠叹息一声,半晌,方问紫鹃‘院中可曾积水?’
紫鹃以为黛玉要出去,回说:“不曾积水,只是稍凉些,须穿了外衣再去。”黛玉便命丫头将素日常用的小桌放于院子中秋千旁,放两个小杌子,又亲将自己留着的两个小青玉杯,拿出来,一边一个摆了,继而将青玉壶交与紫鹃去沏茶,看了一看,方微笑命小丫头道:“将四爷请来喝茶。”
黛玉从未曾主动请弘历来此喝茶,今番此举,不免令众人纳闷疑惑,又极诧异,一时却也只能依言而行,弘历这一日心中也是极古怪,方到家中,便要立时要来潇湘馆,可巧听黛玉请她,忙忙地穿衣来了,彼时半月挂天,窗内灯光映出来,弘历见黛玉正于秋千旁一小桌边静静啜饮,旁边一个丫头也无,便笑道:“怎么大晚上的,突然想起请我喝茶来了。”
黛玉幽幽笑着,将弘历茶杯斟上,说道:“兴致来了,何分白日晚上?况今日这一饮,原和每日不同,本该聊个通宵,以作纪念。”
弘历一时怔住,便看黛玉,笑道:“为何‘今日这一次,和每日不同’?”
黛玉看他一眼,笑道:“明日什么日子?四哥哥可还记得?”
弘历想了想,笑道:“又是谁的生日不成?”
黛玉不禁微微摇头,笑道:“可见四哥哥果然进益了,满脑都是御兵之法,治国之道,再装不下旁的。”
弘历痴痴然半晌,忙笑道:“好妹妹,我心粗,你且告诉我,明儿什么日子?”
黛玉冷笑道:“蠢才,蠢才,再过几个时辰,四哥哥就可离开这府上了。——这么大喜日子,你竟不知道?”
弘历顿时一愣,忙道:“这么快?不是的罢?”
黛玉沉默半日,方小声笑说:“三年前的明日,四哥哥初来贾府,那时四哥哥比现在要矮一些,满面桀骜不驯之气,方一进来,便给老太太跪下道好,舅母要认你作干儿子,你却拧着不依,那日也是我第一次和你见面,彼时情景,仿佛昨日发生的一般,我都记着,还以为你也记得,原来并不是。”
弘历怔怔说道:“明儿是一月十八?”
黛玉点点头,笑道:“是一月十八了。”
弘历便垂头喝茶,默然不语,渐渐将眉头蹙起,半晌,幽幽说道:“明儿是一月十八了,我竟不知道?——怎么这么快?”
黛玉淡淡一笑,声音极轻,说道:“过了今日,我不知还能不能叫你为‘四哥哥’,还能不能和你这样月下饮茶饮酒,落英阁还去不去得,若去得,还去看谁?我长着么大,只有今日,对明日全无概念,一丝一毫,只能凭借猜测,或许明日会有人来,若有人来,一定震撼非小,所有一切,定然全然不同,——明日虽不是生日,其意义之大,比生日尤重。”
说完,脸色一红,忙低头垂目,将手中半盏茶悠悠饮下,弘历见黛玉虽笑,手却是微微抖的,话语虽柔,一字一句,却让他心中隐隐生疼,如有针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