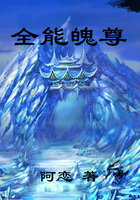“什么赌?”徐寒眉头一耸,望着她的眼中满是戒备。
凌靖雪为他瞬间冷淡的神色所刺激,唇角上勾:“怎么?堂堂三品中州别驾,领兵打仗的将军,怕了我一个弱质女流?”
徐寒明知她故意相激,亦忍不住生气,横眉侧挑:“你尽管说!”
“我能一句话让恬姐儿笑,一句话让她哭,一句话让她追着我跑,你信不信?”
他思索了一会儿:“如果我不信呢?”
“如果我赢了,你得为我做一件事,绝对不牵扯到徐家利益,如何?”她眼中闪着狡黠的光芒,歪着头笑道。
“如果你输了呢?”他不甘示弱。
“那你可以随便问我一个问题,如何?”她胸有成竹。
徐寒缓缓点头,饶有兴致地看着她绕到徐恬身边,轻声说了一句话。徐恬瞬间又惊又喜,笑容止不住从脸上溢出。真有几分本事!他不禁讶然。
紧接着她又补上一句,徐恬盛放如花的面庞刹那间变了。眼眶泛红,嘴唇颤抖,虽然没有哭出声,但泪水马上就要落下来。徐寒惊讶莫名,凌靖雪却依旧神态自若,挑衅般朝他的方向扬了扬下巴。
趁着无人注意徐恬的异样,她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徐寒眼看着徐恬面色通红呀了一声,娇羞地作势要打凌靖雪。两人嘻嘻哈哈闹了一阵,凌靖雪脸颊红扑扑的,喘着气十分得意:“怎么样?愿赌服输吧。”
他无可抵赖,不甘心地追问:“你和她说了什么?”
她神秘地眨着眼睛:“女孩儿家的秘密,哪能告诉你!”一副诡计得逞后的俏皮。
徐寒无话可说,抖抖衣衫摆出大义凛然从容就义的模样:“你尽管说!”
凌靖雪却不答话,反而指指太夫人的方向:“老太太和大嫂要走了,咱们先去送。”
他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犹豫了一下还是跟着过去。徐庭仪处理公务已经走了,太夫人拉着大奶奶的手谆谆嘱咐,徐严在旁一个劲点头。二夫人笼着手恭顺立在太夫人身边,颇显冷淡。
徐恬附在徐岭耳边说了句什么,他果然叫嚷起来:“娘,我累了,要睡觉!”
二夫人愣了愣,大声吩咐丫鬟:“四少爷困了,你们还磨什么?”
大奶奶就算再没心眼,也听得出二夫人的话对她而发,脸上一红,娇娇怯怯对太夫人道:“时候不早了,老太太早点歇着,改日我再过来看您。”
“有空我也过去瞧大嫂,”凌靖雪笑语盈盈往他们的方向走了两步,忽然脚下打滑,“啊”地一声惊叫,左手顺势乱捞,正扯住了三奶奶的衣裳。三奶奶亦是连声惊叫,冷不防被她扯到,堪堪压在身下,做了人肉垫子。
众人猝不及防,眼睁睁看着她二人摔倒,不及救护。徐梧最先冲上去,却见凌靖雪压在方四娘身上,不好伸手搀扶,急得团团转。徐寒目瞪口呆,并没有扶她的意思。凌靖雪瞧得分明,暗恨在心,将方四娘压得更紧了。
方四娘几乎喘不过气,哎哟哎哟直叫,凌靖雪配合着呻吟。荷澜好不容易绕过众人,与徐恬一边一个搀起她,徐梧才解救出了方四娘。
凌靖雪半坐在椅子上,眉头紧皱,咬着嘴唇,右手捂着脚腕,扭得很严重的样子。荷澜急得团团转:“这可怎么好?隔壁永康侯府刚刚遣人来说车子不够用,老爷把府上的全派出去帮忙了,公主可怎么办?”
凌靖雪没料到这一出,不过俗话说得好,赶得好不如赶得巧。她半闭着眼睛,气若游丝道:“那还不容易,随便找谁把我背回去就是了。”
她本是金枝玉叶,寻常人近不得身。众人面面相觑,目光转来转去,最后不约而同落在了徐寒身上。他一个激灵,本能地想拒绝,话在嘴里绕了几绕,最终没有说出口,却听她续道:“难道还要麻烦驸马不成?”
此言一出,不麻烦也得麻烦了。二夫人虽然心疼儿子,也别无他法,唯有反复叮咛:“天黑路滑,慢点走。”转而觉得走得越慢徐寒越累,改口吩咐跟着的小厮们:“你们好生侍候,别让二少爷失了脚。”
她躲在徐恬身后,得意洋洋对他眨眨眼睛,食指竖在唇边,仿佛奸计得逞的小孩。徐寒哑然失笑,无奈地俯下身。
凌靖雪觉得舒服快意,时不时晃荡几下身子,徐寒怄得恨不能将她扔到地上。但君子一诺驷马难追,太夫人她们眼神再怪异,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起初他还故意颠簸了几下,算是报复,无意间却对上她柔情似水的眼神。
她再凌厉嚣张,只是个小姑娘罢了,他轻叹一口气,心不知不觉变得柔软,步子也变得轻盈。她吐气如兰,呼在他的耳际,痒痒发麻,仿佛春日微风拂过。
凌靖雪趴在徐寒厚实的肩上,初时的羞怯不安随着他沉稳的步伐渐渐消失,随之而来的是欣喜与踏实的感觉。无论他心里有没有她,无论他是否是她一生的倚靠,现在他都是她名正言顺的夫君。
小时候她去给皇帝请安,正见他把朝阳负在背上。围着雕花的柱子一圈圈转,郑皇后含笑在一旁护着,好一副天伦之乐的画面。空荡荡的大殿里回响着朝阳清脆甜美的笑声,如根根尖刺准确刺入她的心脏,血肉淋漓。
十六年了,她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安心宽厚的肩膀。无论徐寒是真心还是被胁迫,只要片刻的幻象,她便知足了。闭上眼睛,她仿佛回到了童年,母亲、外祖父,所有人都在她的身边,世界温暖而安全。
回到房里,他做了个手势让丫鬟们退下,耸一耸肩,含着几分戏谑低声道:“还不下来?莫非等我拆穿你不成?”
她却不答话,呼吸如常,他余光侧扫:这家伙,居然睡着了!长长的睫毛如展翅的蝴蝶覆上眼睑,唇边挂着浅浅的笑容,像只无辜善良的小梅花鹿。
徐寒心神微荡,弯腰将她放在大床上,待要离开。忽转念一想,蹑手蹑脚在她身边躺下,吹熄了灯。